《和冥主成婚之后》 139
楚半略微點了下頭:“嗯,相過一段時間。”
“他到的詛咒是怎麼回事?”路迎酒說,“那個所謂的回。”
楚半愣了一下。
楚家一直對楚千句的事嚴守口風。他沒想到,路迎酒連詛咒的事都知道了。
但他沒有追問,坦然回答說:“你應該知道了吧,他沒有來生,每一次回壽命都不過二三十年。”
路迎酒又問:“楚家人都知道這事?”
“嗯。”楚半點頭,“都知道,他們也知道楚千句的每一世回,只是對外保而已。”
他笑了笑,眼中卻沒有幾分真實的笑意:“你下個問題,肯定是問為什麼要保。我直接告訴你吧:楚家需要楚千句,是因為他能鎮住失控的孔雀神。”
“孔雀神并非一直沉睡的……又或者說,沉睡的孔雀神對驅鬼師來說才是有利的。”
“在這一點上,楚千句是再好不過的人選了。”
楚半閉了閉眼睛,又想到他第一次見到楚千句的時候。
那是個日熹微的午后,樹葉吹得楚家門口的樹葉嘩啦啦作響。
那個滿臉漠然的男人倚在墻邊。
他的父親牽著他的手,說:“這位是楚千句,半,你好好跟著他學一學驅鬼的本事,尤其是在請神這一塊。”
小的楚半抬頭,和楚千句對視。
那雙眸子中沒有半點緒。
像是吞噬了所有的深淵。
對于這個人,他是聽過不傳聞的,也知道楚千句背負的詛咒。
每次回楚千句都是沒有記憶的,理論上說,他的心理年齡和常人無差。
他只比楚半大了十多歲,連三十都沒有。可是那種漠然、閱遍千帆的漠然,似乎烙印在了靈魂中,生發芽,層層束縛住他的一切。
Advertisement
楚半跟著他學了一段時間,就沒見他笑過,每天冷冰冰得像個假人,而且還高度自律。
唯有請神時,楚半見到了他的緒波。
孔雀神依舊在沉睡中,即便是被舊日的人所召喚,也無法醒來。
但當他降臨在楚千句上時,孔雀的虛影出現在半空,優雅地展翅。
藍綠的尾羽涌如河流,每一金眼斑都在轉,了人心、迷了心智。
它俯瞰世間的一切。
千百年來,孔雀神都是優雅、瀟灑且心高氣傲的。
能夠令他斂起羽翼、溫停駐的,從來只有一人。
請神帶來了反噬,也讓楚千句的瞳孔迅速變了同樣的金綠,像是寶石。
楚半卻從那雙眼中,看到了明亮的笑意。
意識回到現在,他們并肩走在前去楚千句家中的路上。
楚半繼續和路迎酒說:“但是,我剛才沒告訴,楚千句是被孔雀神殺死的。”
路迎酒愣住了。
楚半說:“和楚千句一樣,孔雀神上也有詛咒。他每次沉睡醒來,不久之后,就會陷極其可怕的失控狀態,對楚家、甚至整個人間都造極大的威脅。”
“之所以到今天為止,孔雀都沒真的失控傷人,是因為每次楚千句都鎮住了他。”
“他們的詛咒幾乎是同步的:每一次楚千句回,過個十幾二十年,孔雀便會蘇醒。然后楚千句去見他、阻止他、令他重新陷沉睡——只是付出的代價是生命。”
他閉了閉眼睛:“我不清楚,楚千句對此事的想法是什麼……他應該知道,自己只是被楚家拿來當槍使,但他不在乎。”
按照道理來說,作為“請神”的開創者,楚千句應當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然而一次次的回,一次次對孔雀神的鎮,漸漸磨滅了這一點。
其他人看楚千句,想到的都是“這是個必死的人”。
他們把鎮孔雀當做義務,拋給了楚千句。
他們也知道,永恒的回讓楚千句不會真的死去,這更讓他們對他的犧牲漠然起來。
——詛咒在你們二人上,你去阻攔他也是理所應當。
反正你都會復活,死亡也無足掛齒。
反正你看起來從沒緒,反正永遠還有下輩子……
或許,楚半本來也會抱有同樣的想法。
但他一直記得請神時楚千句眼中的笑意。
再怎麼樣,人心都是的啊,怎麼可能真的全無緒?
只是有些人將它藏得滴水不而已。
楚千句像塊冷漠的石頭。
楚半有幸見過石頭的裂,其中滲出了。
楚半說:“孔雀的羽在暴怒時,會化作利刃那般尖銳和堅,和匕首沒有區別。”
“楚千句的尸上全是貫穿傷。一開始,我們以為這是他與孔雀的打斗留下的,但后來我才意識到,事不是這樣的。”
“這些傷痕,是因為他最后擁抱了孔雀。”
——楚千句同樣是天之驕子,對孔雀了解到極致,這才有了與鬼神一戰的能力。
與孔雀神的那場戰斗到最后,藍綠的華麗羽飛舞,孔雀上滿是鮮,淋漓地順著軀流下——他化作了人,卻又保持了自的一切特征,包括金綠的瞳孔,和鬢角、周的層層羽。
艷紅流過致的鎖骨,垂下修長的手指,在人上野與華麗融,看一眼就能攝人心神。
到最后一刻,發狂的孔雀神也好,滿傷痕的男人也好,都是氣吁吁。
楚千句將手中的刀刃一轉,迎著萬千刺向他的尖利羽,沖了上前。
銀的刀劃過半空,斬斷翠綠,最終濺起一簾猩紅。
它貫穿了孔雀的心臟,狠狠一絞,再果斷地拔出。
鬼神在間無法被真正殺死,但這足夠重創孔雀,讓他回到沉睡了。
而這果決、狠厲的一刀,讓楚千句沒辦法避開又一劍羽。
事實上,他也沒有避開的意思。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已無半分力,等待他的唯有死亡。
他把短刀隨手甩到一邊,刀鏗鏘振,將刃上鮮盡數抖落。
然后他迎著鋪天蓋地而來的、尖端閃著寒芒的羽,邁了半步上前,抱住了孔雀神。
任由對方周的羽翼刺穿了軀。
一切回歸寂靜,滿地狼藉,羽和鮮匯在一起,地面是猙獰的劃痕。
明明彼此相,卻被詛咒所困,只能廝殺至死亡。
理智回歸了孔雀的瞳孔中。
生命的最后幾秒,楚千句過他的面龐,從眼眸一直到鬢角,從下顎一直到脖頸,最后低頭深吻過他的。
這是個帶了腥與烈火氣息的吻,卻溫到了極致。
正如多年前,他抱起荒原上傷的孔雀時,小跑過空濛的細雨,懷抱也是如此溫。
“……晚安,”一吻終了,楚千句在他耳畔說。
“小孔雀,我們來生再見。”
第63章 唯夢閑人
“所以,”路迎酒問,“為什麼那麼久過去了,楚家都沒有試圖解決詛咒?”
楚千句和孔雀神,一個是驅鬼天才,一個是自家結契的鬼神,對于楚家來說都是非比尋常的重要。
如果能破除詛咒,楚家必然得利。
楚半說:“我們一直在想辦法,幾百年來,卻從來沒法解決,甚至連半點曙都沒見到過。這是無解的死局。”
能讓楚半承認一件事“無解”,可不容易。
路迎酒問:“他們上的詛咒究竟從何而來?”
這回,楚半沒有立刻回答他。
他猶豫了幾秒鐘,回頭看去,見其他人都離他倆有段距離,才低聲說:“我待會換個地方再和你說。”
說完他加快腳步:“快走吧,楚千句以前的家就在前頭了。”
路迎酒往前看去,果然看到一間小小的屋子出現在村子的角落。
因為多年無人居住,它破破爛爛的。防盜窗生銹,玻璃被灰塵模糊,木門快要爛掉了。墻上還有一個大大的、紅的【拆】。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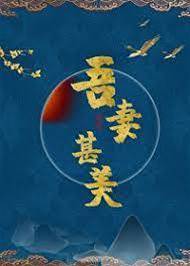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353 章

東宮禁寵
沈江姩在宋煜最落魄之日棄他而去,改嫁為周家婦,一時風光無限。宋煜復寵重坐東宮主位,用潑天的權勢親手查抄沈江姩滿門。為救家族,沈江姩承歡東宮,成了宋煜身下不見天日任他擺布的暖床婢在那個她被他據為己有的夜里,下頜被男人挑起,“周夫人想過孤王有出來的一天麼?”
79.1萬字8.18 13704 -
完結221 章

太子侍妾
【雙潔?謀權?成長】 沁婉被倒賣多次,天生短命,意外成為九皇子侍婢,因為出生不好,一直沒有名份。九皇子金枝玉葉,卻生性薄情,有一日,旁人問起他的侍俾何如。 他說:“她身份低微,不可能給她名份。” 沁婉一直銘記於心。又一日,旁人又問他侍婢何如。 他說:“她伺候得妥當,可以做個通房。” 沁婉依舊銘記於心。再有一日,旁人再問他的通房何如。 他說:“她是我心中所向,我想給她太子妃之位。” 沁婉這次沒記在心裏,因為她不願了。......後來,聽說涼薄寡性,英勇蓋世的九皇子,如今的東宮太子 卻跪在侍婢的腳下苦苦哀求。願用鳳印換取沁婉的疼愛,隻求相守一生。她沁婉哭過,怨過,狠過,嚐過生離死別,生不如死,體驗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是沒醜過!後來,她隻想要寶馬香車,卻有一個人不僅給了她寶馬香車,連人帶著花團錦簇都給了她。
40.6萬字8.18 9261 -
完結503 章

離婚后才知道前夫的白月光竟是我
溫軟和祁宴結婚三年,用盡努力都沒能暖了祁宴的心。她以為那人天生涼薄,無心于情愛,便一心守著豪門太太的身份過日子。直到群里發來祁宴和白月光的合照,溫軟才知道他不是沒有心,只是他的心早就給了別人。 握不住的沙不如揚了它,留不住的男人干脆踹了他,溫軟當晚便收拾好行李,丟下一直離婚協議離開了家。 離婚后,溫軟逛酒吧點男模開直播,把這輩子沒敢做的事全都瀟灑了一遍,怎料意外爆火,還成了全民甜妹,粉絲過億。 就在她下決心泡十個八個小奶狗時,前夫突然找上門,將她堵在墻角,低頭懲罰般的咬住她溫軟的唇,紅著眼睛哄,“狗屁的白月光,老子這輩子只愛過你一人。” “軟軟,玩夠了,我們回家了好不好~”
64.2萬字8 17299 -
完結187 章

甜爆!撿到陰郁大佬閃婚被寵瘋了
宋知暖在自家別墅外撿了個男人,貪圖對方的美色帶回了家,藏在自己的小閣樓上,等男人醒來,兇巴巴的威脅,“我救了你,你要以身相許報答我,報下你的身份證,我要包養你,每月給你這個數!” 霍北梟看著女孩白嫩的手掌,眉梢微挑,“五百萬,我答應了。” 宋知暖炸毛,“一個月五千,多一個子都沒有!” 宋知暖以為的霍北梟,一米八八八塊腹肌無家可歸,四處漂泊,需要自己救濟愛護的小可憐。 實際上的霍北梟,深城霍家太子爺,陰狠暴戾,精神病院三進三出的常客,無人敢招惹的存在,被小姑娘撿回家閃婚后,卻頻頻傳出妻管嚴的謠言,好友不信,遂做局帶太子爺在酒吧泡妹子。 不多時包廂的門被人踹開,闖進來一身穿白色長裙,純粹到極致的姑娘,姑娘只瞧了太子爺一眼,眼圈泛紅,唇瓣微抿,兔子似的。 眾人只見那位太子爺慌亂的摁滅手里的煙,走過去將姑娘圈懷里低頭親。姑娘偏頭躲了下,太子爺輕笑一聲,耐心的哄,“寶寶,罰我我當眾給你跪一個表真心好不好?”眾好友:卒。
35.2萬字8 1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