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冥主成婚之后》 96
路迎酒一愣,然后想起敬閑估計是沒讀過四大名著的,不笑著跟他簡單講了講盤的故事,說那七只蜘蛛怎麼綁架了唐僧,又怎麼在泉水中洗澡。
沒想到敬閑聽完,張地過來又摟上了他的腰。
路迎酒:?
路迎酒問:“你這是干什麼?”
“這不是怕有蜘蛛過來搶你,還拉著你一起洗澡。”敬閑說。
路迎酒:“……”
他算是對敬閑找的借口有了全新認識,把他腰上那手給掰了下來,丟在一邊,自己率先往前走了。
敬閑跟在他后,一臉憾。
這地下通道不見盡頭,越往前走,周圍越是很暗,出沒的蜘蛛越是猖狂。
本來前邊見到的蜘蛛還是很怕人的,走了十分鐘后,已經有蜘蛛敢靠近兩人了,看起來很想下口。
這點蜘蛛沒什麼威脅,路迎酒用符紙的,很輕松就把它們退了。
又走了一段距離,他發現自己好像沒聽到團子的腳步聲了,也久沒聽見敬閑講話。
他一回頭。
這一回頭他差點窒息——
敬閑竟然手中抱著團,正把它往墻上的一只大蜘蛛湊過去!
團子吐著舌頭躍躍試,口水都快滴到地面了,還想出爪子去拉。
路迎酒:?!
眼看團子就要一口咬上去,他趕快制止:“敬閑!”
敬閑被他發現,手上一抖趕帶著團子了回來,一臉無辜地看著他。
路迎酒:“你不要再給它吃奇怪的東西了!”
敬閑:“嗯嗯嗯。”
路迎酒怎麼看怎麼不放心,一把從他手里搶過來團,自己抱著。
團子:“嗷嗷嗚——”表達不滿。
Advertisement
路迎酒就彈它的腦門。
就這樣又走了十幾分鐘。
周圍的蜘蛛網真的快幕布那樣厚了,通道的盡頭終于出現了亮。
不是火,而像是燈泡。
走近后,他們看到在泥土和巖壁之中竟然有一扇鐵門嵌著。鐵門的左右各自亮著一盞白熾燈。
鐵門鎖著。
路迎酒看敬閑,了他。
敬閑得令,當即就把整個鐵門用暴力卸了下來。整張門的金屬幾乎被皺了,委委屈屈地被他丟在一旁。
屋渾濁的空氣撲面而來。
里頭倒是干干凈凈,看不到半點蜘蛛和蜘蛛網,也看不見馮茂的影。
路迎酒邁步進去,看見一張簡單的單人床,一個電視和一臺播放,旁邊的書架上堆滿了黑的錄像帶。
他舉起符紙,湊近去看。
錄像帶一共分了六堆,從第一堆到最后一堆,數量不一,有些堆得很高有些本沒有。
每一堆的上頭都嵌著一個木框,木框中是一塊灰黑的石板,大概是15寸的大小,刻著圖案。
路迎酒先看第一塊石板。
圖案都是很簡單的線條,仿佛原始人留下的什麼文。
畫的是一只巨大的蜘蛛盤踞在山嶺,軀幾乎沒云端。一個人單膝跪在它面前,出左手,去拿它前上的蛛。
他后已經有不人,全都是左手纏著蛛。
這一瞬間路迎酒了然:蜘蛛果然和村里人都是左撇子有關系。
恐怕是在傳說中,祖輩們是用左手接過的蛛,所以他們認為左手是神圣的。
這幅畫的下方,寫了標題《蛛母》
第二塊石板上,畫了一堆小人在圍著火堆跳舞,名字做《祭祀》。
這塊石板底下有不錄像帶,路迎酒隨手拿起一個,打開電視塞進去機里。
一陣閃爍的雪花屏過后,電視上出現了畫面:
篝火燃燒著,一堆村民圍繞著它不斷舞蹈、歌唱。
這本來該是溫馨又熱鬧的場面,但是不論是他們的作還是歌聲,都十足詭異。
歌聲嗚嗚咽咽的,仿佛嬰孩在啼哭,又仿佛是一陣尖銳的風吹過了山谷,發出尖嘯。而他們的舞蹈作僵無比,每一寸關節都在不正常地扭,像是一群牽線木偶……或者說像是在模仿某種節肢,比如說蜘蛛。
路迎酒面無表地快進看完了,又放進去其他的錄像帶。
畫面倒是相同的,都是他們圍著火跳舞唱歌,只是時間和地點不同。看錄像帶的數量,估計是好幾十年的記載了。
快進過程中,路迎酒不時摁下暫停鍵,然后仔細看村民的容貌。
果然被他找出了幾張悉的面孔。
那幾個人,他都是在最近幾天見過的。
這些在十幾年前跳舞的人,如今還以一不變的容貌住在村子里。姑娘依舊貌如花,小伙子依舊年輕俊朗,歲月永遠將他們定格在了一個瞬間,不曾流逝。
路迎酒說:“這村子竟然所有人都有問題……”他沉思片刻,然后有些無奈地笑了笑,“我那些平安符,算是白發給他們了。”
他又繼續看下一塊名為《恩典》的石板。
石板上畫著一個人背上長出了蜘蛛的八足,地上有一大灘嘔吐,仔細一看,全都是臟,肝膽橫流。
他正在把臟拼命吐出來。
吐得越多,他就變得更像蜘蛛。
在他前頭的兩個人——準確來說已經不是人了,兩只蜘蛛正在歡快地爬著。
敬閑的手過石板,說:“那個玩筆仙的主播,做趙梓明對吧。”
“對,”路迎酒閉了閉眼睛,“看來他去洗手間嘔吐,就是把自己的臟全吐出來了。他變了人面蜘蛛。”
然后在好友阿龍不知的況下,被一腳踩死了。
路迎酒見過不悲劇,也聽過不凄慘故事。
他的思緒不會被此影響,但難免還是唏噓,輕輕嘆了口氣。
打開錄像帶,果然播放出的畫面中,都是大口大口吐出臟的人。
有些扶著馬桶嘔吐,有些對著洗手池吐,有些直接就嘔在了地上,淋淋的一團。錄像帶里沒有聲音,但路迎酒幾乎能想象出他們撕心裂肺的聲音。
再然后,背上長出蜘蛛腳,形逐漸萎下去。
他們變了蜘蛛。
第四塊石板名為《轉變》。
沒有錄像帶,石板上畫著村落,和幾十只蜘蛛。
整個村子都變蜘蛛了。
第五塊石板名為《暴雨》。
石板上還是畫著村落,只是這次一只蜘蛛都沒有了,又變了簡陋的火柴人。
火柴人們做出舉手招呼的作,而村子外頭,一輛輛車正在駛來。
路迎酒皺眉,放進去錄像帶。
然后呼吸一滯——
畫面上竟然出現了那些主播的面容!
鏡頭非常搖晃,像是新聞里那種針孔攝像機拍出來的效果。
他飛速瀏覽了每一個錄像帶,看到了悉的紅服、阿龍、趙梓明,甚至還有葉楓和小李的影……他們有些在酒店談,有些在爬山去療養院,有些就是在車里一晃而過。
看角度和時間的話,像是不同的人錄下來的,比如說酒店服務員,比如說村口的村醫們,或者湖邊喂的老大爺。他們耐心地、悄悄地錄下來了外來者的日常。
從第一批主播進村開始,整個村都開始監視他們了!
路迎酒下意識看向最后的石板。
石板上什麼都沒有,像是沒有畫完。
旁邊只有個空的標題:《盛宴》。
已經足夠讓人骨悚然了。
目又回到第一塊石板。
“蛛母……”路迎酒喃喃說,“我沒有聽過這個名字。敬閑,你知道什麼嗎?”
敬閑沉思片刻:“從沒去過鬼界,我也只是聽過一點傳聞,并不知道是否真實存在。如果真的存在,那麼肯定一直待在間。”
他繼續說:“傳說里蛛母是一個巨大如山岳的蜘蛛,會把追隨的人變蜘蛛,永生不死,有時候還能變回人類。”
“當然,如果那些人面蜘蛛想永生和人類相貌,就要不斷把新的人變蜘蛛,給蛛母提供新的追隨者。”
猜你喜歡
-
完結718 章

嬌妃火辣辣
某夜,某人爬牆被逮個正著。 「王妃欲往何處去?」 「那個……南楚世子東陵太子和西炎王又不老實了,我削他們去」 「那個不急,下來,本王急了……」
136.3萬字8 27080 -
完結156 章

穿成侯門寡婦後,誤惹奸臣逃不掉
【雙c 傳統古言】沈窈穿越了,穿成了丈夫剛去世的侯門新鮮小寡婦。丈夫是侯府二郎,身體不好,卻又花心好女色,家裏養著妾侍通房,外麵養著外室花娘。縱欲過度,死在了女人身上……了解了前因後果的沈窈,隻想著等孝期過了後,她求得一紙放妻書,離開侯府。男人都死了,她可不會愚蠢的帶著豐厚的嫁妝,替別人養娃。 ***謝臨淵剛回侯府,便瞧見那身穿孝服擋不住渾身俏麗的小娘子,麵上不熟。但他知道,那是他二弟剛娶過門的妻子。“弟妹,節哀……。”瞧見謝臨淵來,沈窈拿著帕子哭的越發傷心。午夜時分,倩影恍惚,讓人差點失了分寸。 ***一年後,沈窈想著終於可以解放了,她正要去找大伯哥替弟給她放妻書。沒想到的是,她那常年臥病在床的大嫂又去世了。沈窈帶著二房的人去吊唁,看著那身穿孝服的大伯哥。“大伯哥,節哀……。”謝臨淵抬眸看向沈窈,啞聲說道:“放你離開之事,往後延延……。”“不著急。”沈窈沒想到,她一句不著急, 非但沒走成,還被安排管起侯府內務來。後來更是直接將自己也管到了謝老大的房內。大伯哥跟弟妹,這關係不太正經。她想跑。謝臨淵看著沈窈,嗓音沙啞:這輩子別想逃,你肚子裏出的孩子,隻能是我的。
31.5萬字8.18 9189 -
完結1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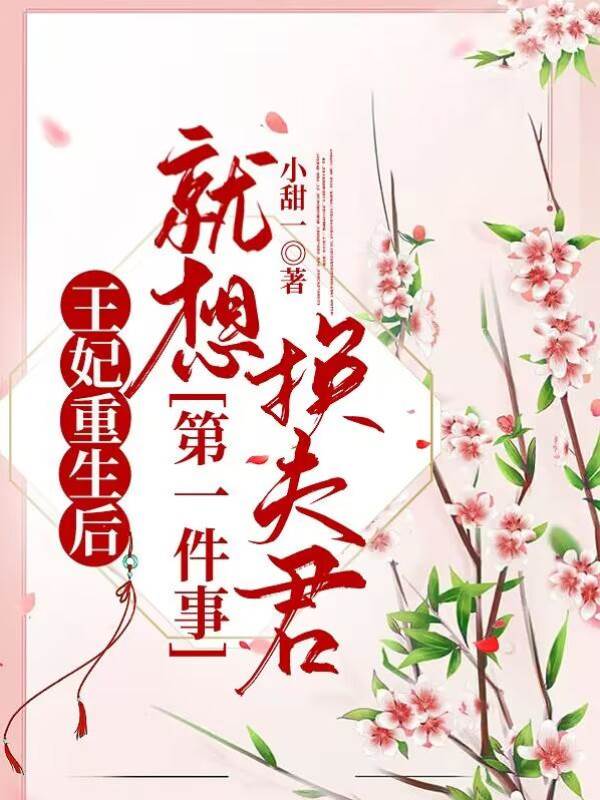
王妃重生後,第一件事就想換夫君
上輩子盛年死於肺癆的昭王妃蘇妧重生了。回想自己前一世,溫婉賢惠,端方持家,一心想把那個冰塊一樣的夫君的心捂熱,結果可想而知;非但沒把冰塊捂化了,反而累的自己年紀輕輕一身毛病,最後還英年早逝;重生一世,蘇妧仔細謹慎的考慮了很久,覺得前世的自己有點矯情,明明有錢有權有娃,還要什麼男人?她剛動了那麼一丟丟想換人的心思,沒成想前世的那個冤家居然也重生了!PS:①日常種田文,②寫男女主,也有男女主的兄弟姐妹③微宅鬥,不虐,就是讓兩個前世沒長嘴的家夥這輩子好好談戀愛好好在一起!(雷者慎入)④雙方都沒有原則性問題!
34.3萬字8 20883 -
完結279 章

嫁給兄長的竹馬
寧姒10歲時遇見了16歲的姜煜,少年眉目如畫,溫柔清雅,生有一雙愛笑桃花眼,和她逗比親哥形成了慘烈的對比。 那少年郎待她溫柔親暱,閒來逗耍,一口一個“妹妹”。 寧姒既享受又酸澀,同時小心藏好不合時宜的心思。 待她出落成少女之姿,打算永遠敬他如兄長,姜煜卻勾起脣角笑得風流,“姒兒妹妹,怎麼不叫阿煜哥哥了?” 【小劇場】 寧姒十歲時—— 寧澈對姜煜說,“別教她喝酒,喝醉了你照顧,別賴我。”嫌棄得恨不得寧姒是姜煜的妹妹。 姜煜微醺,“我照顧。” 寧姒十六歲—— 寧澈親眼看到寧姒勾着姜煜的脖子,兩人姿態親密。 姜煜低頭在寧姒臉頰上親了一口,然後對寧澈笑,“阿澈,要揍便揍,別打臉。”
42.9萬字8.18 11084 -
完結309 章

釣餌
周宴京電話打來時,陳桑剛把他白月光的弟弟釣到手。周宴京:“陳桑,離了我,你對別的男人有感覺?”弟弟雙手掐著陳桑的腰,視線往下滑:“好像……感覺還不少。”……“在我貧瘠的土地上,你是最後的玫瑰。”【飲食男女 男二上位 人間清醒釣係美人VS偏執腹黑瘋批大佬】
53.4萬字8.18 6024 -
完結123 章

傻妃配殘王
最近京城可出了個人人皆知的大笑話,將軍府中的傻公子被太子殿下退貨轉手給了殘王,傻子配殘王,天生一對。 世人卻不知這被人人嘲笑的某人和某王正各自私地下打著小算盤呢。 “報,王爺,外面有人欺負王妃殿下。” 某人聞言,眉頭一挑:“將本王四十米的刀拿來,分分鐘砍死他,活得不耐煩了!!” “報,王爺………………,”某士兵支支吾吾的看著心情不錯的某人。 “怎麼了,誰又欺負王妃殿下了?” “王爺,這次并不是,王妃殿下他去了春香閣……………………” 砰的一聲,某人身下的輪椅碎成了幾塊:“給本王帶兵將春香閣拆了!” 歡脫1V1有副cp
15.5萬字8 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