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冥主成婚之后》 35
陳言言的手抖了一下。
路迎酒的子微微前傾,繼續講:“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沒有向陳家求助的意思——或許是你死都不想和他們聯系,或許是你沒意識到況嚴重,不管怎麼樣,我的提議是這樣的:我幫你驅散這只鬼,你告訴我當年的細節。我沒有揭人傷疤的好,除了案件本,絕對不會多問一句。”
陳言言下意識說:“找其他厲害的驅鬼師,也是一樣的,不一定非要你啊。”
“你可以去試。”路迎酒笑了,“但是你敢賭嗎?”
賭贏了,就守住了當年的,賭輸了,那可是要賠上命的。
陳言言看了眼自己的左手,止疼藥的藥效過去了,傷口正微微發疼。再閉上眼睛,那輛呼嘯著向沖來的卡車,好像還在眼前。的單車被撞得變了形,人飛出去五六米,重重落地時,嚨中泛起濃烈的腥味,模糊視線中,只能看到單車的子朝著空中緩緩地轉。周圍的嘈雜聲很遙遠,像是隔著深水,有人在喊:“出事了——!”
那一瞬間,真的以為自己已經死了。
確實和醫生所說的那樣,這次是命大。
路迎酒的名字,是聽過很多次的,找他驅鬼可是別人求都求不來的機會。
咬了咬:“……但是,”飛速地看了眼敬閑,猶豫了半天才開口,聲如細,“我也、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兇手啊……萬一你是壞人怎麼辦……”
路迎酒說:“我要是兇手,還犯得著大費周章來找你問細節嗎?最清楚案的,就該是我自己了。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時候,甚至都沒有認出我,當年,我本不是什麼正兒八經的嫌疑人,這點你不是最清楚的嗎?”
Advertisement
他的聲音有種讓人信服的力量。
只要稍微打聽過他的人,都知道他當首席時口碑極佳,可謂是驅鬼界的良心:承諾了保護委托者,那麼委托者就絕不會出事;承諾了找到厲鬼,那麼厲鬼的一家大小都會被連揪出來。加上那養眼到親和力拉滿的長相和沉靜的氣質,再怎麼看,都和“心不正”不沾邊。
陳言言沉默了很長時間。
看不出在做什麼心理斗爭,但看向路迎酒的表逐漸和。
許久后,深呼吸了一口氣,說:“好,我告訴你。其實,我上這個鬼,就是當年害死我家人的鬼……”
路迎酒和敬閑對視了一眼。
陳言言攥了手:“當時我和同學說要一起玩試膽游戲,就找了個廢棄的建筑,‘四屠宰場’,玩四角游戲。規則你應該是知道的。”
路迎酒點頭。
他低頭搜了一下,四屠宰場在鷺江市和源臺市中間,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也不知道那幾個小屁孩怎麼過去的。
陳言言繼續說:“玩著玩著,我們就發現不對勁了,我們之中好像真的多了一個人。我們很害怕,馬上離開了。接著,我就打車去了KTV陪我弟過生日。沒想到、沒想到……”閉了閉眼睛,“我把那只鬼一起帶過去了。后面的事你們也知道了。我才是害死他們的兇手……現在終于到我了。”
路迎酒說:“這不是任何人的錯,理清疑點,查明真相,才是你對他們最好的藉。”
陳言言閉著眼睛點了點頭,長吁一口氣,繼續說:“玩游戲的四個人,分別是我,我的閨范馨,還有我倆的男朋友。范馨……范馨在那不久后,也因為意外離世了,肯定是這個鬼害的。至于那兩個男生,我后來沒聯系了。”
回憶起了過去。
6年前的那個下午,男們在車上,離開明的校園,一起去了森的屠宰場。那老舊的建筑沉默在云下,像是一頭龐然大,他們翻過生銹的鐵門,踩著齊膝雜草,笑鬧著走進去,互相打趣。
頭上烏云一卷,傾盆大雨從天而降,閃電撕裂了蒼穹,狂風吹起年人的衫。沒有任何人能想到,這是一條不歸路。
路迎酒記下了這三個名字,發給了陳笑泠。
如果陳言言遇到了危險,說不定,那兩個男生也是這樣。
“所以,”陳言言看著他,“你能殺死它嗎?”
的目又掃過敬閑——那俊朗的男人就站在路迎酒后,和認真聆聽的路迎酒不同,他的神是滿不在乎的,像是對的故事不興趣,甚至不屑于流虛偽的關心。他又去裝了一杯水,拿在手里慢慢喝,從始至終目都在路迎酒上。
路迎酒思考了幾秒鐘:“因為靈異游戲請來的鬼,最好是能夠回到當時的地點,再進行驅散。為了穩妥起見,我們要去四屠宰場。”
陳言言的臉蒼白了幾分:“要回去?”
“嗯。”路迎酒點頭,“事有疑點。你去到KTV是傍晚,玩游戲的時間是在下午。靈異游戲是很難真的招來厲鬼的,在白天玩的話,概率就更是低。何況這個鬼很厲害,簡直是兇殘得過分了……就我個人來看,這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陳言言慘淡一笑:“那是因為,我們在玩游戲前還了些符紙去請鬼。我當時膽子大,想請來的鬼,是最可怕的那一位。如果是他,做到這些是輕而易舉的吧。”
“有名諱嗎?”
“沒有,只有位。說出來你可能會嘲笑我吧。”
“不會的。”路迎酒說,“這是很關鍵的線索。”
陳言言的手抓了被子。
是真的很害怕,抖著,老半天后才小聲說:“我請來的,是鬼王。”
“咳咳咳——!”敬閑猛地嗆了一口水,直接笑得不行了。
……
兩分鐘后,路迎酒和敬閑站在病房外。
他們是被憤怒的陳言言趕出來的。
兩人看著面前人來人往,一時無言。
隔了一陣,路迎酒開口說:“雖然我也知道那不可能,但是你干嘛嘲笑別人呢……”
敬閑:“……一下子沒忍住。”
他是真的覺得離譜,又笑了聲——那青燈會說路迎酒是嫌疑犯,那陳言言說他就是殺人無數的厲鬼,這滅門案還是他們夫夫倆合伙犯罪搞出來的。
那小姑娘也是真的敢說,這世界上,哪有能請來他的人?
此前,他就來過這世間一次。
就是路迎酒冥婚那天。
敬閑說:“我真的錯了,你別生氣。”
路迎酒看他,那張勝過模特、被雕細琢出來的帥臉上滿是真誠——路迎酒心想,要是剛才他對陳言言有這萬分之一的誠懇,事也不至于這樣。
路迎酒:“……生氣不至于,就是,你還是要尊重一下別人的。”
敬閑保證道:“下次一定!”
他又想著,路迎酒雖然上說著不生氣,但是黑白無常告訴過他,搞對象的時候,對方是會口是心非的。
說不生氣,很有可能就是在生氣。
說沒關系,很有可能就是有關系。
于是路迎酒剛試圖理清思路,就看見敬閑又誠懇地說了句:“你別生氣。”
路迎酒:“……?”
路迎酒說:“我真沒有……唔……”
敬閑靠近半步,把他懟在了門上死死抱著。那力氣還是一如既往地大,路迎酒在他懷中撲騰了幾下,仿佛一只被大型犬住的貓,完全沒啥水花,反而惹了一。
路迎酒:“你這又是在做什麼??”
“我錯了!”敬閑說,說完抱得更了。
一個路過的老大爺盯著他們倆,眼神分外復雜,滿臉寫著“你們玩得真大”,又仿佛在看什麼“保衛戰”的現場:一個悔恨不已的渣男試圖追回漂亮的舊,而舊……漂亮的舊路迎酒仰頭,無聲地罵了句臟話。
好不容易從敬閑的懷中掙扎出來,路迎酒扶額道:“你這道歉方式也太獨特了。”
猜你喜歡
-
連載722 章

閃婚誤惹:天價大佬狂寵她
沈安安目睹渣男和同父異母的姐姐背叛后,她轉頭撩上了渣男的小舅舅,陰差陽錯下兩人直接結婚了。。正當她暗暗自喜,要坐穩小舅媽的位置時,豬隊友訕訕告訴她撩錯人了。。沈安安:???我娃都有了你和我說這?。她看著眼前帥氣的男人,覺得自己也不虧,算了,…
71.4萬字8 74314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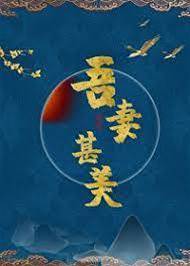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132 章

他又野又烈
【破鏡重圓 久別重逢 雙向奔赴 雙向救贖 青春甜寵】高中時溫書緲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最後卻以最狼狽的方式收場。六年後再遇,他是紋身店老板,她變成了他的員工。他表情冷漠的如同一個陌生人。直到謝勁看見溫書緲提著行李箱時他終於忍不住失控的把人推到牆角:“還來是吧。”“六年前的事情你還要再來一次是吧!”“溫書緲。”他一字一頓的叫她的名字,低頭在她鎖骨上狠狠咬了一口。溫熱又兇狠。*沒有人知道,他的鎖骨上紋了一個女人的唇印和名字,那是溫書緲咬他的痕跡。他把這個痕跡做了永久的定格。她離開的那些天,謝勁給她發信息:“溫書緲,你最好永遠都不要出現在我麵前,永遠。”*他愛她愛進了骨髓。她說畫畫是她的另一雙翅膀,他就拚了命的愛護她的翅膀,卻沒想到後來有一天,她的翅膀斷了,他差點瘋了。*謝勁:“我從未放棄過愛你,隻是從濃烈變得悄無聲息。”溫書緲:“無需命運袒護我,我隻要謝勁。”——【痞帥野壞賽車手X要乖不乖小畫手】
24.2萬字8.18 8273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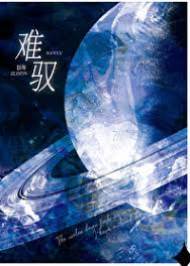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57 11698 -
完結179 章

世子寵妻錄
林紈前世的夫君顧粲,是她少時愛慕之人,顧粲雖待她極好,卻不愛她。 上一世,顧家生變,顧粲從矜貴世子淪爲階下囚。林紈耗其所能,保下顧粲之命,自己卻落得個香消玉殞的下場。 雪地被鮮血暈染一片,顧粲抱着沒了氣息的她雙目泛紅:“我並非無心,若有來生,我定要重娶你爲妻。” 重生後,林紈身爲平遠軍侯最寵愛的嫡長孫女,又是及榮華於一身的當朝翁主,爲自己定下了兩個目標—— 一是:再不要把一手好牌打爛。 二是:不要與前世之夫顧粲有任何牽扯。 卻沒成想,在帝都一衆貴女心中,容止若神祇的鎮北世子顧粲,竟又成了她的枕邊人,要用一生護她安穩無虞。 * 前世不屑沾染權術,不願涉入朝堂紛爭的顧粲,卻成了帝都人人怖畏的玉面閻羅。 年紀尚輕便成了當朝最有權勢的重臣,又是曾權傾朝野的鎮北王的唯一嫡子。 帝都諸人皆知的是,這位狠辣鐵面的鎮北世子,其實是個愛妻如命的情種。 小劇場: 大婚之夜,嬿婉及良時,那個陰鬱淡漠到有些面癱的男人將林紈擁入了懷中。 林紈覺出那人醉的不輕,正欲掙脫其懷時,顧粲卻突然輕聲低喃:“紈紈,爲夫該怎樣愛你?”
28.6萬字8 16229 -
完結166 章

盛小姐一身反骨,就愛給黑子添堵
[任務失敗,三天后死亡]盛棠愛上了攻略人物,導致任務失敗。 她利用這三天時間將整個娛樂圈攪得翻天覆地,看著渣男賤女名聲被毀的樣子終于可以放心去死,但一睜眼,她居然沒死! 一年后,盛棠帶著獎項強勢回歸! 黑粉:不是大姐,你在頒獎臺上低頭找什麼呢?笑死我 盛棠:我找廁所,你也姓廁? 黑子:地球居然還有你這種極品,真是惡心! 盛棠:讓你家主子給你單整個地球拴著,怎麼總跑出來亂咬人呢。 吃瓜群眾:好美的精神狀態一女的! 就在大家看盛棠發癲的時候,居然看到盛棠參加戀綜了?! 不但盛棠參加戀綜了,就連清冷影帝傅宴安也來了?! 看著在綜藝上找各種理由借口和盛棠貼貼的傅影帝,粉絲們無力吐槽。 最后,傅宴安理直氣壯地點頭:“擔心我家小孩受欺負,來看看。”
35.8萬字5 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