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縛龍為后》 35
“阿鳶?”
“阿鳶?……”
寧枝玉喚了燕鳶好幾聲,燕鳶方才回神,扭頭看寧枝玉:“……嗯?”
寧枝玉坐起子,擔憂道:“你在想什麼呢。”
“這幾日?你與我在一起時總是走神,可是國事上遇到了什麼難題?”
燕鳶笑了笑:“沒有。”
寧枝玉定定著他俊側容,心中浮起難以言喻的悲傷,總覺得這人雖在自己邊坐著,心卻離他越來越遠了。
今日燕鳶本是沒打算帶寧枝玉出來的,寧枝玉求他了許久,說想同普通夫妻那般在街上逛廟會,看花燈,寧枝玉有想要什麼的時候,燕鳶不忍心拒絕,見他這幾日服了龍鱗后神好了許多,便答應了。
然而,從玄龍離開那日起,心便從未停止過想念。
燕鳶知道自己這樣不對,可他本控制不住自己,當初只是癡迷于玄龍的,稍微靠近些便想與他歡好,如今玄龍不見了,他的心就跟著空缺了一塊,雖不會死,但腦中裝著那龍的面容揮之不去,吃飯的時候想,睡覺的時候想,理朝政的時候想,就連與寧枝玉在一起時都忍不住頻頻想起。
明知道陷得越深,便是對寧枝玉的背叛越深,然而,人若能輕易掌控自己的,哪里還會有那麼多癡男怨為殉。
難道……他真的喜歡上那龍了麼。
那阿玉呢,阿玉怎麼辦……燕鳶想到此,心臟就狠狠揪,恰逢此時,側寧枝玉忽得咳嗽了起來。
燕鳶心中一驚,從袖中掏出手帕遞到寧枝玉邊,寧枝玉抬手接過,燕鳶輕輕順著他單薄的后背:“難得厲害麼?”
Advertisement
寧枝玉搖頭,用手帕捂著咳個不停,馬車壁簾被風拂起,窗外的月映得他面容慘白,眼底猩紅。
燕鳶心痛不已,命令外頭駕車的侍衛快馬加鞭。
寧枝玉許久才漸漸安靜下來,白帕子從邊挪開,被滲紅了半塊。
燕鳶拿過他手中帕子折起,用干凈的地方去寧枝玉邊殘留的污,啞道:“朕就不該帶你出來,原還好好的,定是因為今夜吹了風,現在又咳了。”
寧枝玉知他心疼自己,便笑起來,抬手了燕鳶溫熱的面頰,安道:“這子本就是時好時壞,無事的,阿鳶莫要擔心。”
燕鳶哪里舍得再說重話,沉默地將寧枝玉攬懷中,寧枝玉靠在他肩頭,久久無言。
“……阿鳶。”
馬車進皇城時,寧枝玉喚他。
燕鳶低頭:“嗯?”
“今夜我很歡喜。”寧枝玉輕聲道。
燕鳶笑起來,眼底:“朕亦很歡喜。”
“阿鳶。”寧枝玉又喚他。
“嗯?”燕鳶耐心地回。
“若有一日……你上了別人,莫要告訴我。”
燕鳶形微僵:“說什麼呢。”
“沒有。”
寧枝玉角揚著淺淺的弧度,就如在聊今夜吃了什麼般輕松。他的眸漆黑如夜,里頭燃著不算熱烈的火,許是因置于黑暗,那簇火顯得格外富有生命力,卻又好似隨時會熄滅。
“我只是想,活在世上最后的日子,能快樂些。”
“你若上了別人,莫要告訴我,賜我一杯鶴頂紅,安安靜靜送我走吧。”
“最好是由你親手喂我喝下的,能死在你懷中……我亦覺得歡喜。”
燕鳶見了寧枝玉面上的笑容,覺得刺目,也覺得心慌,收手臂將人抱在懷中,干啞道:“你真是病得太久了,連腦子都不甚清醒了,總這般胡言語。”
“但朕不會嫌棄你,你是朕的皇后,不論你變什麼模樣,朕都會繼續你。”
“賜毒酒這話都說得出來,你是存心要朕不痛快,讓朕難過麼。”
寧枝玉攥他襟,紅了眼眶:“沒有……”
他哪里舍得燕鳶難過。
只是無法接世上唯一待他好的人離他而去,若真有那麼一天,比起做個雙目明亮的瞎子,他寧愿做個頭腦清醒的傻子。
死于他而言有何畏懼,比死更可怕的是眼睜睜看著心的人與他背道而馳,人若沒了盼頭,死就是件很輕松的事了。
燕鳶一下一下著寧枝玉后背,溫聲道:“朕知你心思敏,病得久了,容易胡思想。”
“朕不怪你。”
“若累了,便睡吧,有朕在呢。”
寧枝玉不住生出想哭的沖,這人明明待他如此溫,他怎麼就懷疑燕鳶變心了呢,也許真是自己病糊涂了,胡思想,傷了自己,也傷了他的阿鳶。
“嗯。”寧枝玉摟燕鳶的腰,靠著他肩膀,合上雙眼,眼角出淚。
馬車在鸞宮外停下,燕鳶抱著寧枝玉下了車,了殿寧枝玉便醒了,燕鳶將人輕手輕腳地放到床榻上,拉著寧枝玉手說了會兒話,將人哄睡了,方才離去,去理今日堆積的政務。
燕鳶已幾日未回乾坤宮了,夜里不是留宿鸞殿,便是在書房的小榻上湊合一夜,只要回到與玄龍生活過的地方,就覺得心里空虛落寞,難以眠。
他沒想到,區區一頭妖能在自己心中留下如此重的痕跡,大抵就如劍過墻壁留下的刮印,再深刻的痕跡都能被能工巧匠修補得完無缺,但曾經存在過的東西,是不會隨著表面的風平浪靜被永遠抹去的。
書房,燕鳶坐在桌案后,看著桌上的奏章,手中狼毫將落未落,筆尖的墨滴落在奏章上,將上頭的字糊了一團。
燕鳶猛然回神,放眼去,偌大書房空空,唯他一人,暗夜獨有的孤寂與安靜將他徹底淹沒,忽得就想起那笨拙的龍。
那龍笨雖笨,但待他是真的好,會在他生氣時努力哄他,不會說什麼漂亮話,只會用行來證明他的真心。
燕鳶原以為自己是不稀罕玄龍的真心的,他得人是阿玉,要玄龍的真心做什麼,他之前還覺得多余,如今卻……如今,其實仍舊是累贅。
他不能背棄與阿玉的承諾……
燕鳶放下手中狼毫,從口掏出鳶尾玉墜,正是他送給玄龍作定信的那塊,玄龍離開的時候沒有帶走,將它留在了乾坤宮偏殿的桌上。
說來好笑,挑選這塊玉佩的時候,燕鳶未曾用過什麼心,隨便太監去國庫挑來的,自己就是隨手取了一塊送他,告訴玄龍說是心挑選的,便哄得他那般開心,連逆鱗都拔了送給他。
如今那龍走了,燕鳶反而將這塊毫無意義的玉佩好好地收在懷中,時不時便要拿出來看看。
他看著這塊玉佩的時候,便總是想,玄龍曾擁有這塊玉佩的時候,是否也同他這般,指尖細細挲過上頭的紋路,借此思念他。
再多困,已無人回應他。
那龍已離開了。
天高海闊,他會去哪兒呢,是會回到千年古潭,還是重新尋一無人知曉的地方,安安靜靜地躲著,他無法尋到。
燕鳶心底涌起莫名的悲傷,他抬起手,想將手中玉墜擲碎在地上,斷了自己那不該有的念頭,可又覺得不舍。
逆鱗被他作藥引給寧枝玉服了,他與玄龍唯一的,僅存的聯系,便是這塊玉墜,對他來說其實意義不大,但這玉墜裝載著兩人曾有過的意。
即使那意其實在任何人看來都很可笑。
最終,燕鳶還是將手收了回來,可不知怎的,他的手沒能握,玉墜極快地從手中落,砸在堅的桌案上。
玉碎。
燕鳶慌忙將玉佩拾起,想將那指蓋大小的碎玉片拼湊回去,可怎麼都做不到,他心中不安,高聲喚道。
“陳巖!”
“陳巖!”
陳巖進來,見他面焦急,小心湊過去問道:“皇上,怎麼了?”
“你看這玉墜,能恢復原樣嗎?”燕鳶急聲道。
陳巖看了片刻,如實道:“皇上,這玉碎了,怕是恢復不了了,即便修復了,也會留痕的。”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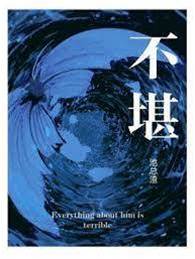
不堪
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三觀不正,狗血淋頭,閱讀需謹慎。】 每個雨天來時,季衷寒都會疼。 疼源是八年前形如瘋魔,暴怒的封戚所留下的。 封戚給他留下了痕跡和烙印,也給他傷痛和折磨。 自那以后,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高人氣囂張模特攻x長發美人攝影受 瘋狗x美人 封戚x季衷寒 標簽:HE 狗血 虐戀
20.2萬字8 6022 -
完結178 章

浮京一夢
蘭燭見到江昱成的那天,她被她父親帶到他面前,父親卑躬屈膝地討笑着,叫着對方江二爺。 江昱成隨意翻着戲摺子,頭也不擡,“會唱《白蛇》?” 蘭燭吊着嗓子,聲音青澀的發抖。 江二爺幫着蘭家度過難關,父親走了,留下蘭燭,住在江家槐京富人圈的四合院閣樓裏。 蘭燭從那高樓竹窗裏,見到江昱成帶回名伶優角,歌聲嫋嫋,酒色瀰漫。 衆人皆知槐京手腕凌厲的江家二爺,最愛聽梨園那些咿呀婉轉的花旦曲調, 不料一天,江家二爺自己卻帶了個青澀的女子,不似他從前喜歡的那種花旦俏皮活潑。 蘭燭淡漠寡言,眉眼卻如秋水。 一登臺,水袖曼妙,唱腔哀而不傷。 江昱成坐在珠簾後面,菸灰燙到手了也沒發現,他悵然想起不知誰說過,“青衣是夢,是每個男人的夢。” 他捧蘭燭,一捧就是三年。 蘭燭離開江家四合院閣樓的那天,把全副身家和身上所有的錢財裝進江昱成知她心頭好特地給她打造的沉香木匣子裏。 這一世從他身上受的苦太多,父親欠的債她已經還完了,各自兩清,永不相見。 江昱成斂了斂目,看了一眼她留下的東西,“倒是很有骨氣,可惜太嫩,這圈子可不是人人都能混的。” 他隨她出走,等到她撞破羽翼就會乖乖回來。 誰知蘭燭說話算話,把和他的關係撇的乾乾淨淨。 江昱成夜夜難安,尋的就是那翻轉的雲手,水袖的輕顫。 他鬼使神差地買了名動槐京蘭青衣的票場子,誰知蘭燭卻不顧這千人看客,最終沒有上場。 江昱成忍着脾氣走到後臺化妝間,看到了許久的不見的人, 幾乎是咬着牙問到:“蘭燭,爲什麼不上場” 蘭燭對鏡描着自己細長的眉,淡漠地說:“我說過,不復相見。” “江二爺,這白蛇,實在是不能再爲你唱了。”
28.1萬字8 1560 -
完結161 章

離婚那天,傅少跪在她裙邊求原諒
結婚五年,她以為自己可以焐熱傅宴禮的心,等來的卻是他的一紙離婚協議,他前女友的回歸更是成了壓垮她們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姜瑤看著朋友圈老公為前女友慶生的照片徹底的心灰意冷,主動簽下離婚協議成全他。傅宴禮不愛姜瑤,這是一個圈子里皆知的秘密,當年傅宴禮是被逼婚娶了姜瑤,所有人都為他鳴不平,等著姜瑤被休下堂,傅公子可以迎娶心上人幸福一生。 然而,真到了這一天,一向尊貴無雙的傅公子卻固執的拉住她的手,紅著眼卑微祈求,“瑤瑤,我知道錯了,咱們不離婚行不行?”
30.2萬字5 125 -
完結93 章

晚一點愛上你
穿著自己媳婦兒設計的西裝完成婚禮,季則正覺得自己計劃周全,盡在掌握。自從遇見她,記住她,他開始步步為營,為她畫地為牢。 帶著傷痛的她,驕傲的她、動人的她,都只是他心中的陸檀雅。 這一回陸檀雅不會再害怕,因為冥冥之中上天早有安排,錯的人總會離開,對的人方能共度余生。 “遇見你似乎晚了一點,但好像也剛剛好。”
26.4萬字8 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