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魚陷落》 342
一陣冷風吹來,拂走了地面上的熱氣,國際監獄外站崗的獄警揚起頭,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按捺不住滿心狂喜:“是要下雨了?”
監獄大門慢慢敞開,穿制服裝備的保鏢整齊有序列隊而出,參與談判的組織領導人在保鏢簇擁下走了出來,軍隊的異形雷達車緩緩跟隨,隨時預防周圍出現危險實驗干擾談判。
言逸走在最前面,李妄陪同在側。
獄警押著戴上純黑頭套的艾蓮走到言逸側,言逸轉掀開頭套,指尖扶上臉頰邊緣檢查是否有面痕跡,毫不遮掩地當眾確認了一遍人質份。
短短一年間,艾蓮像老了十歲,狠狠抬起松弛的眼皮,冷笑道:“公報私仇,我以為你是什麼正人君子。”
“私仇?”言逸蓋上了的頭套,背手站立等待,“私仇指什麼?是在保衛城市中負重傷和壯烈犧牲的IOA特工和學員嗎?”
接近正午十二點,天空風云變幻,固化的海面封層逐漸開裂,裂紋蜿蜒擴大,爬滿了封印的海面。
突然,一激流沖破海面,形高聳云的海龍卷,烏云中電流轉,藍閃電不斷爬下天空劈裂海面,海浪翻涌,逐漸由水化鋼鑄造王座。
一條通藍,明能觀見骨骼的巨大蝠鲼沖出水面,張開近十米的雙翼,從空中劃出一道震撼藍。
明蝠鲼化為人形,坐上王座,支著頭垂眼睥睨眾生。
一頭珠母貝隨之躍出水面,落在水化鋼珊瑚支架上,張開巨,出里面圓盤大小的圓潤珍珠,然后猛然閉合,鎖住,保護著里的圓珠。
盡管被珍珠質厚實包裹,但塞壬鱗片的輝依舊不可遮蔽,淡淡廓從珍珠部出藍來。
Advertisement
蘭波擔心自己離開加勒比海后會有人對小白不利,只能隨帶著才稍微安心,但珍珠的大小已經生長到無法拿在手上的地步,只能存放在珠母貝中。
“我來了。我要的人帶來了嗎?”蘭波的聲音低沉有力,帶著些許鯨鳴回音。
言逸向前邁了一步,示意艾蓮就在自己邊,但沒有立刻把人推過去:“請您解封所有海域吧。”
蘭波用尖長食指卷了卷金發:“你有什麼底氣和我談條件?”
蘭波微抬眼皮,魚尾化修長雙,踩著水化鋼階梯一步一步走下王座。
他分開洶涌海浪,每落一步,腳下都會展開一面藍電流轉的水化鋼平面。
蘭波與言逸肩而過,走到艾蓮面前,掀開的頭套,用覆蓋冰涼鱗片的手爪抬起下端詳,當著所有談判者的面擺弄他要的獵,黑的尖銳指甲在艾蓮臉上劃出一道痕,低頭嗅的氣味。
“我不會立刻殺死你的。”蘭波輕艾蓮耳側,隨后將人一把奪了過來,推海中,水化鋼牢籠將艾蓮閉合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灌有空氣的明長方塊中,并緩緩沒深海。
被無盡深淵吞噬的恐懼讓艾蓮本能地敲打外壁求救,但也無濟于事,不久就完全消失了蹤跡。
“我們已經把人出來了,您兌現承諾解封海域吧。”
“如果我不呢?”蘭波挑眉淡笑,“看你們的狼狽樣子我發自心高興。”
“但海陸割裂遭殃的不僅我們,如果真的發海陸戰爭,兩敗俱傷的局面不會是您想要的。陸地上生存的不僅人類一種生,您要趕盡殺絕嗎?坐在王位上,這樣是否失職呢?”
蘭波緩步走回海中,冰冷海水沒過了他的小。
“抱歉。”言逸真誠道,“事發展到如今這樣的局面,是我們的錯,我們會盡力挽回的。”
蘭波沉默下來,不再回答,這時,雙眼瞳仁忽然亮起金紋路,伴生能力錦鯉賜福應到時機自釋放,一個不知道哪來的布包從水中飄了過來,撞到了蘭波的。
蘭波出輕蔑諷刺的眼神,卻嗅到了蛛包裹上悉的氣味。
他怔了怔,蹲下來打開包裹,里面裝滿了著標簽的小禮,蛛網兜、手工牛軋糖、幾包酸溜溜和一沓在蚜蟲島上拍的照片,還有一部套著兔子手機殼的手機,似乎因為漂泊時間太久,手機早就沒電關機了。
蘭波輕照片上站在自己邊的小白,眼瞼慢慢泛起紅。
他已經快要接小白變玻璃珠陪伴在自己邊的事實了,可是看見照片上小白鮮活的模樣,他又清晰地到細的疼痛依然在他口久久沉積著,從未釋懷。
正在他出神時,裝甲車上的異形雷達突然報警,警示音反復播放:“惡化期實驗正在靠近!”
所有保鏢立即舉槍戒備,人們屏息凝神不敢妄,突然,一道詛咒金線纏繞到了珠母貝上,強行撬開貝殼,纏繞在其口中含的大珍珠上。
監獄最高的尖頂上不知何時悄然出現一個實驗,厄里斯坐在高臺邊緣晃雙,扯起角做了個鬼臉。
言逸和蘭波同時應到氣息異常,朝珠母貝飛奔過去。
蘭波躍海中,雙恢復魚尾,從海浪中穿梭回援,言逸飛一躍,從空中幾次瞬移,近珠母貝保護里面的白玻璃珠。
“不要打碎它——!”
但噩運降臨的氣息突然籠罩下來,珍珠從言逸指尖墜落,蘭波不顧一切將它接進懷里,后脊卻狠狠砸在了海面上,高空墜落時海水與地面一樣堅,巨大的沖擊力讓蘭波眼前一黑。
雖然接住了珍珠,但珍珠表面爬上了裂紋,裂紋越爬越多,突然碎裂開來。
蘭波躺在水化鋼浮冰上,顧不上骨骼震裂的劇痛,艱難爬起來將散落的珍珠碎片攏進懷里。
塞壬鱗片從玻璃球部了出來,失去載后,閃爍藍的鱗片自回到了蘭波上。
他慌張地想要把珍珠碎片拼回原樣,卻發現本做不到。
“不要,不要忘了,randi,別讓我忘了你。”蘭波狠狠攥住一塊碎片,掌心滲出來,讓疼痛迫自己不要忘小白。
眼淚斷了線般墜進海里,蘭波跪坐在漂浮的水化鋼上,仰頭痛哭。他所端著的王的威嚴在這一刻徹底崩塌,復仇的喜悅在巨大的悲傷面前不值一提。
“蘭波,別哭。”言逸在他邊說。
蘭波快要失去理智時,突然到有什麼溫熱的小東西在了自己手背上。
他含著眼淚低下頭,看見了一只白絨的小爪子搭在自己手背上,很小很小。
言逸忍不住彎起眼睛,單膝蹲在水化鋼浮冰上,用指尖了白絨里還著的小獅子崽的頭。
“小白?”
小獅崽剛剛睜眼,只會嚶嚶。
——
躲在監獄高臺尖頂上故意挑起紛爭的厄里斯也愣了,一下子站起來:“什麼?那是我大哥?我去把它踩死。”
人偶師見蘭波并沒忘記一切的跡象,捂住厄里斯的帶他跳下高臺:“別出聲,撤。”
今天6000+!
第255章
確定小獅崽沒事,兩人的目同時轉向了監獄尖頂,冷厲搜尋那一縷淡淡的歐石楠信息素氣味。
言逸直接追了上去,影從原地消失,再從數十米之外懸空出現,凌空再次瞬移,不過兩個呼吸間便踏上了監獄最高的尖頂天臺。
頂上旗幟隨風獵獵作響,厄里斯和人偶師正用詛咒金線向更遠的平臺去,一縷金線末梢不經意拂過言逸臉頰。
“想走?”言逸一把抓住即將消逝的詛咒金線,快速纏繞在自己小臂上,用力一扽。
厄里斯腰間驀然一,他只來得及用力把人偶師推上對面高臺,自己卻被言逸狠狠拽了回來。
以厄里斯惡化期的實力,至有力量與言逸一戰,但言逸吸取了與永生亡靈戰斗的經驗,并不近厄里斯的,而是突然松開手中的詛咒金線,讓厄里斯重重撞擊在平臺下的墻壁上。
厄里斯單手掛在了高臺邊緣,整個都懸在高空中,下意識了一下印有蜘蛛標記的后腰有沒有被打碎。
他仰言逸,臉上的十字紋線隨著他出悚人笑容而變得扭曲:
“我只是做了人人都想做的事,如果他碎了,人類得償所愿,誰會謝我?你們可真虛偽。”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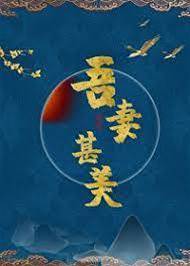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353 章

東宮禁寵
沈江姩在宋煜最落魄之日棄他而去,改嫁為周家婦,一時風光無限。宋煜復寵重坐東宮主位,用潑天的權勢親手查抄沈江姩滿門。為救家族,沈江姩承歡東宮,成了宋煜身下不見天日任他擺布的暖床婢在那個她被他據為己有的夜里,下頜被男人挑起,“周夫人想過孤王有出來的一天麼?”
79.1萬字8.18 13704 -
完結221 章

太子侍妾
【雙潔?謀權?成長】 沁婉被倒賣多次,天生短命,意外成為九皇子侍婢,因為出生不好,一直沒有名份。九皇子金枝玉葉,卻生性薄情,有一日,旁人問起他的侍俾何如。 他說:“她身份低微,不可能給她名份。” 沁婉一直銘記於心。又一日,旁人又問他侍婢何如。 他說:“她伺候得妥當,可以做個通房。” 沁婉依舊銘記於心。再有一日,旁人再問他的通房何如。 他說:“她是我心中所向,我想給她太子妃之位。” 沁婉這次沒記在心裏,因為她不願了。......後來,聽說涼薄寡性,英勇蓋世的九皇子,如今的東宮太子 卻跪在侍婢的腳下苦苦哀求。願用鳳印換取沁婉的疼愛,隻求相守一生。她沁婉哭過,怨過,狠過,嚐過生離死別,生不如死,體驗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是沒醜過!後來,她隻想要寶馬香車,卻有一個人不僅給了她寶馬香車,連人帶著花團錦簇都給了她。
40.6萬字8.18 9261 -
完結503 章

離婚后才知道前夫的白月光竟是我
溫軟和祁宴結婚三年,用盡努力都沒能暖了祁宴的心。她以為那人天生涼薄,無心于情愛,便一心守著豪門太太的身份過日子。直到群里發來祁宴和白月光的合照,溫軟才知道他不是沒有心,只是他的心早就給了別人。 握不住的沙不如揚了它,留不住的男人干脆踹了他,溫軟當晚便收拾好行李,丟下一直離婚協議離開了家。 離婚后,溫軟逛酒吧點男模開直播,把這輩子沒敢做的事全都瀟灑了一遍,怎料意外爆火,還成了全民甜妹,粉絲過億。 就在她下決心泡十個八個小奶狗時,前夫突然找上門,將她堵在墻角,低頭懲罰般的咬住她溫軟的唇,紅著眼睛哄,“狗屁的白月光,老子這輩子只愛過你一人。” “軟軟,玩夠了,我們回家了好不好~”
64.2萬字8 17299 -
完結187 章

甜爆!撿到陰郁大佬閃婚被寵瘋了
宋知暖在自家別墅外撿了個男人,貪圖對方的美色帶回了家,藏在自己的小閣樓上,等男人醒來,兇巴巴的威脅,“我救了你,你要以身相許報答我,報下你的身份證,我要包養你,每月給你這個數!” 霍北梟看著女孩白嫩的手掌,眉梢微挑,“五百萬,我答應了。” 宋知暖炸毛,“一個月五千,多一個子都沒有!” 宋知暖以為的霍北梟,一米八八八塊腹肌無家可歸,四處漂泊,需要自己救濟愛護的小可憐。 實際上的霍北梟,深城霍家太子爺,陰狠暴戾,精神病院三進三出的常客,無人敢招惹的存在,被小姑娘撿回家閃婚后,卻頻頻傳出妻管嚴的謠言,好友不信,遂做局帶太子爺在酒吧泡妹子。 不多時包廂的門被人踹開,闖進來一身穿白色長裙,純粹到極致的姑娘,姑娘只瞧了太子爺一眼,眼圈泛紅,唇瓣微抿,兔子似的。 眾人只見那位太子爺慌亂的摁滅手里的煙,走過去將姑娘圈懷里低頭親。姑娘偏頭躲了下,太子爺輕笑一聲,耐心的哄,“寶寶,罰我我當眾給你跪一個表真心好不好?”眾好友:卒。
35.2萬字8 1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