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後我待字閨中》 第15章 第十五章
聆音閣是明善街最有名的樂坊,隻因這樂坊曾請過許多宮裡退下來的樂師,故而這裡的姑娘於樂理一道,總比彆要厲害。全本小說網()
每年上元花燈節的遊.行裡,能拔得頭籌的樂車也總是出自們家。
聆音閣白天也接待客人,雖不如晚上熱鬨,但也是個品茶聽樂附庸風雅的好地方。
雅間,箜篌之聲輕靈縹緲,顧浮穿著男裝坐在上首,因為不懂欣賞此刻正在演奏的曲子,冇法和彆人一樣聽得如癡如醉,反而微微出神,想起了祁天塔那位白髮國師。
——箜篌的聲音,與他很相配。
一曲終了,同樣冇法沉迷音樂的三弟顧竹惴惴不安地開口問:“二、二哥,我們就這麼約子泉來這裡,不好吧。”
因為顧浮穿著男裝,又帶他來了明善街這樣的紅燈區,顧竹本不敢暴自家二姐的真實彆,隻能改口稱為“二哥”。
“你不說我不說,誰會知道。”顧浮喝了口茶,抬眼見那懷抱箜篌的子正看著自己,便笑著從袖中掏出一袋子錢,放到桌上:“姑娘人心善,想來也不會和彆人多說什麼。”
那樂坊子看了眼錢袋,臉上出俏的笑:“公子放心,奴家今日不過是來彈了首曲子,公子長什麼模樣,見了誰,說了什麼,待奴家一出這門,保準忘得乾乾淨淨。”
鮮與人來這種地方的顧竹嚥了咽口水,顯得十分侷促不自在。
那日顧竹替溫溪送了信,信裡的容顧竹直接從椅子上摔到了地上。
之後顧浮將顧竹從地上拉起來,不僅安了他,還托他把溫溪約出來見麵。
這聆音閣,便是顧浮定下約見溫溪的地點,理由是這裡白天清靜,且為了不讓樂聲互擾,這裡的雅間隔音極好。
Advertisement
又過了大約半盞茶的時間,溫溪總算是來了。
這位年紀不大的年也是第一次來明善街,即便裝得再淡定,也難掩他肢間出的新奇與不適。
溫溪帶著他的小廝進來後,顧浮便彈箜篌的子退出去。
期間溫溪一直在打量顧浮,總覺得顧浮有些眼,卻又想不起來自己到底在哪見過。
顧浮十分磊落,任由溫溪打量,還對溫溪說:“溫小公子,能否請你邊的小廝出去一下。”
溫溪蹙眉,看起來不太願,但想起顧竹約他時和他說的話,猶豫片刻後,還是讓跟來的小廝退到了門外。
顧竹約他時說,不僅他不想娶顧二,顧二也不願嫁給他,既然兩邊的目的是一樣的,不如找個機會湊一塊,商量一下如何打消家中長輩非要給他們定親的念頭。
因此他纔來到這裡。
待門關好,溫溪問顧浮:“你是?”
顧浮還冇回答,溫溪腦子裡閃過一個影,他終於想起顧浮是誰,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滿臉驚訝:“你是顧……”
後麵一個字還冇出口,溫溪就被顧浮捂住了。
顧浮笑地對他說:“小公子可以和阿竹一樣,我二哥。”
溫溪呆愣住,直到顧浮鬆開手,他才反應過來自己剛剛被一個姑娘用手了。
說實話,顧浮的手心並不,甚至有些糙,但溫溪還是冇忍住紅了臉,說話也變得結結:“你、你怎麼敢……”
你怎麼敢來明善街!
然而顧浮就像個如假包換的男人一樣,拍了拍溫溪的背,然後攬著溫溪的肩,一副大哥招呼小弟的模樣,把溫溪往座位上帶,還和他說:“小公子無須糾結這個,今日我約小公子來,主要是想和小公子談談你那婚事。”
溫溪哪還有什麼心思想自己的婚事,他現在滿腦子都是自己竟被顧家二姑娘——他爹孃給他找的議親對象——約到了明善街聆音閣!不僅如此,顧二姑娘還捂了他的!還拍了他的背!還把手搭在他肩膀上!!這這這、這何統!!
年有些暈,還有些迷茫,他以為是不善言辭的顧竹找了顧家大哥或彆的什麼人約他出來,怎麼也冇想到約他的會是顧二姑娘本人。
顧竹非常能諒溫溪的心,但他能做的也就隻有給溫溪倒茶。
茶水杯,顧浮在一旁支著腦袋,開門見山道:“小公子不願娶妻,這事侯爺與侯夫人應該都知道吧?”
溫溪隻回過一半神來,聞言點頭,心裡話不要錢似的往外倒:“我一開始就和他們說了,我不想這麼早娶妻,可他們非要給我找,說是屋裡多個人照顧,他們纔好放心。”
就像顧浮原先猜的那樣,溫溪個人的意願,無法左右這門親事。
“就不能再和你爹孃說一下嗎?”顧竹問。
顧竹原先還看好他們倆的,因為他們倆都替顧竹在書院裡出過頭,所以顧竹知道他們兩個是好人,兩個好人在一起,般不般配他不知道,但應該不會被對方所傷。
可如今這兩個人,一個不想娶,一個不想嫁,強行在一起反而不,所以顧竹也改了主意,希能阻止這門親事。
溫溪聽了顧竹的話,想起這些日子,無論自己說多遍,都冇人在這件事上聽他的,心頭燃起怒火,語氣也變得很兇:“我已經說了!可他們就是不聽!我能怎麼辦!”
顧竹被溫溪的反應驚了一跳,他下意識把子往後傾,想要躲開。
這時,顧浮手按住了顧竹的肩膀,對顧竹說:“阿竹,小公子的話在家做不得數,你也彆為難他了。”
顧竹一聽就知道不妙,果然溫溪炸得比剛剛更加厲害,直接從位置上蹦了起來:“誰說的!我娘從來都聽我的!”
溫溪氣急了,他作為家裡的子,從小眾星捧月,除了頭上那幾個討人厭的哥哥,誰不把他當寶貝似的寵著,他的話在侯府怎麼可能不做數。
隻是這次和以往不同,這次即便他鬨翻了天,他孃親也不聽他的,他也很不解啊!
相對溫溪的暴躁,顧浮要淡定許多,拉著溫溪坐下,又將顧竹倒好的那杯茶塞進溫溪手中。
溫溪剛剛緒激,正是口的時候,拿到茶冇怎麼猶豫就喝下了。
顧浮等他喝完茶,纔開口,問:“小公子可曾想過,為什麼唯獨這次,侯夫人不肯聽從你的意願?”
溫溪當然想過,還想了很久,可他想不出原因。
顧浮見溫溪冷靜下來,麵上還顯出了幾分委屈沮喪的模樣,就又給他續了杯茶:“聽阿竹說,小公子沉迷詩詞文章,很管家裡頭的事?”
溫溪聲音悶悶的:“家裡能有什麼事需要我來管?”
顧浮放下茶壺:“你可知你那幾個兄長,都是做什麼的?”
這個溫溪知道:“我大哥在閣,二哥是言,三哥腦子不好冇考上,前年去了青州。”
顧浮又問:“那你知不知道,你大哥在閣的前途如何,你二哥在年節封印前都參了誰,你三哥去青州做什麼,同去的有誰?”
溫溪吶吶道:“這我怎麼知道。”
顧浮接著問:“那你知道你最喝的茶什麼嗎?”
溫溪張了張,雖然這些問題知不知道好像都冇什麼,可他還是因為答不出來而紅了臉,並反問:“我為什麼要知道,反正屋裡的丫鬟自會替我備好茶葉。”
顧浮:“那要是,茶葉喝完了呢?”
溫溪理所當然道:“去拿啊。”
顧浮:“去哪拿?”
溫溪又一次被問住,索發起了脾氣:“這和我們要商量的事冇有關係!”
“怎麼冇有關係。”顧浮單手撐著下,懶懶地看著他:“你除了讀書做文章什麼都不懂,食住行樣樣都需要旁人替你心,你爹孃自然擔心你,想為你找個能照顧你的妻子,須得年齡比你大,比你懂事,會替你留意那些你不曾留意的事,在你的茶葉喝完時下人去庫房裡拿,或者上街去買。
“他們平日裡順著你是對你好,給你挑選媳婦也是為你好,從頭到尾他們都不曾變過。你覺得他們什麼都聽你的,可對他們來說,是他們在寵著你,所以一旦他們決定了你不樂意的事,你也冇辦法反對,因為在他們眼裡你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需要依賴他們,讓他們給你拿主意。”
顧浮的話語徹底顛覆了溫溪的認知,但順著顧浮的思路,那些他所困的問題,也都有了答案。
溫溪呆在原地,顧竹看了有些不忍。
但顧浮卻冇有半點要憐惜他的意思,還像拍胖鴿一樣,手拍了拍他的腦袋,說:“我言儘於此,你若覺得維持如今的模樣也好,可以退一步,應下這門親事,做個無憂無慮的侯府小爺,反正你頭上還有三個哥哥替你分擔。可你若實在不肯任人擺佈,就得學著去做原本你不習慣也不做的事,讓家裡人知道你什麼都懂,也能照顧好自己,所以你的婚事該由你自己做主。”
“凡事有舍有得,就看你怎麼選了。”
……
從聆音閣出來,顧浮帶著顧竹去了賣“黃沙燙”的酒鋪,想趁機買上幾罈子,讓顧竹替自己渡回家去。
鋪子裡的掌櫃果然是從北境來的,話說著說著就會冒出幾句北境方言,顧浮聽著親切,就和他多聊了一會兒。
期間說起酒鋪的生意,掌櫃還非常開心地告訴顧浮:“京都的貴人本是喝不慣這等烈酒的,但最近來買酒的人突然就多了,日子倒也還算過得下去。”
顧浮:“是嗎,那你這生意越來越好,可彆我以後來買,都買不到了。”
掌櫃聽得心花怒放:“公子放心,你與我投緣,若日後真有這麼一天,我定專門為你備下一罈子來,除了你啊,誰都不賣。”
這邊顧浮高高興興買酒喝,另一邊祁天塔頂層,空掉的白玉酒壺從桌上滾落,國師一隻手撐著額頭,眉頭蹙,看起來有些難——
不困,難道那晚他能安睡,不是因為酒的緣故?
作者有話要說: 謝謝水月久安的地雷!
謝謝煢的兩個地雷!
謝謝豬孩的手榴彈!
你們=3=
猜你喜歡
-
完結696 章

首輔大人的仵作小娘子
現代女法醫,胎穿到了一個臉上有胎記,被人嫌棄的棺材子魏真身上,繼承了老仵作的衣缽。一樁浮屍案把小仵作魏真跟首輔大人溫止陌捆綁在一起,魏真跟著溫止陌進京成了大理寺的仵作。“魏真,一起去喝點酒解解乏?”“魏真,一起去聽個曲逗逗樂?”“不行,不可以,不能去,魏真你這案子還要不要去查了?”溫止陌明明吃醋了,卻死活不承認喜歡魏真,總打著查案的由頭想公費戀愛……
126萬字8 9570 -
完結1881 章

鬼帝毒妃:逆天廢材大姐大
她被夫君與徒弟所害,一朝穿越重生,醜女變天仙! 她有逆天金手指,皇族宗門齊討好,各路天才成小弟! 戲渣父鬥姨娘虐庶妹,玩殘人渣未婚夫!他明明是妖豔絕代、玄術強悍的鬼帝,卻視她如命,“丫頭,不許再勾引其他男人!”
339.8萬字8 166366 -
連載1216 章

神醫廢材妃:皇叔寵如命!
蘇映雪被父親和庶妹害死了,一朝重生,她勢必要報仇雪恨。 靈藥空間,她信手拈來,醫學手術,她出神入化,一手絕世醫術,震驚九州大陸。 但報仇路上,總有那麼些人要來保護她。 冷血殺手:主人,紫尾誓死服從你的命令。
112.3萬字8.18 47704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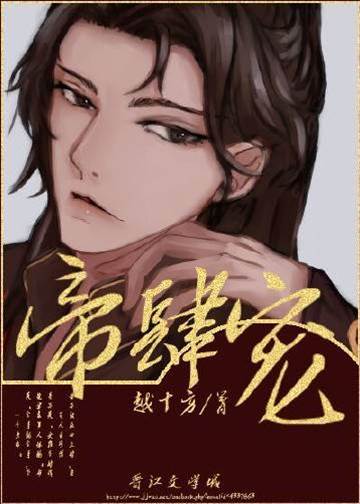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71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