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卿卿不放松》 第6章 求娶
鄭沛氣噎,狠狠瞪了鄭濯一眼,卻惱不得元賜嫻不給面子。畢竟人家的確喊了“殿下”,是他慢答一步。
鄭濯眼底出幾分無奈笑意。
這個瀾滄縣主倒機靈,方才與他對了眼,顯然是意與他共舟的意思,卻偏要他來做這惡人,好獨善其。
元賜嫻毫不心虛地點點頭:“這主意有趣。便令擲得奇數者一舟,偶數者一舟,如何?”
如此一來,豈非得憑天意?鄭沛氣得都快犯病了,正要拒絕,卻見說完這句,忽然偏頭對他笑了笑。
這素齒丹,燦然一笑震得他沒說上話來,半晌才恍然驚覺,此笑非笑,那輕盈檀口分明是向他比了個型:奇。
原非人不依,而是怯了,這才拐著彎來!
他心中釋然,春風得意道:“好,就使這法子!”
很快有婢送上了四顆骰子,四人各執一顆,在一面木盤上依次拋擲。
鄭沛當先擲了個奇數,喜滋滋地瞧著余下幾人,見鄭濯接著擲出個偶數,渾都暢快起來。
元賜嫻倒沒這想擲什麼就擲什麼的本事,見狀,掂了掂手中骰子,看一眼鄭濯,一臉“就靠你了”的神。
鄭濯淡笑一下,示意放心。
得了暗示,一把將骰子擲出,一瞧,果真是個偶數。
鄭沛登時傻眼。
難不是他自作多會錯了意,方才元賜嫻的一笑,單單只是一笑而已?
陸時卿覷一眼著塊磁石,在木盤底下小作不斷的鄭濯,隨手擲了個奇數,在鄭沛還不著頭腦時便往獨木舟走去,停在岸邊回頭道:“九殿下,您先請?”
……
元賜嫻如愿與鄭濯上了一條船,當先離岸而去。
鄭沛愁白了臉,呆了半晌才踩上木舟。不知是因日頭曬人,或者心氣惱,他坐下時子一晃,險些一頭栽進水里去。
Advertisement
陸時卿往后退避幾分,像生怕他將病氣過給自己,坐在對頭不咸不淡道:“殿下如有不適,下可隨您一道回岸上去。”
眼見元賜嫻和鄭濯的木舟漸漸行遠,他咬咬牙:“不必。”又吩咐艄公,“趕跟上!”
湖面寬闊,水芙蓉裊裊亭亭,碧葉紅花鋪了大半池,木舟在其間須得緩行。好在撐篙的艄公功夫嫻,輕輕巧巧幾避幾繞,便船悠悠往前駛了去。
只是對鄭沛而言,這幾番晃就不大輕巧了。不一會兒,他便因接連彎繞腦袋發暈,胃腹翻騰,一酸氣漸漸上涌到了嚨口。
他竭力按捺,不料前頭又逢一大片水芙蓉。艄公的長篙一撐,木舟一晃,他便再憋不住,“哇”地一口,眼看就要吐出來。
對頭陸時卿臉大變,慌忙起退開,因木舟狹窄,避無可避,急之下,只得“噗通”一聲躍下了水。
與此同時,鄭沛嘔出了一大灘臟污。恰逢風過,飛濺一船。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
元賜嫻和鄭濯聞聲驀然回首,雙雙錯愕。
見心上人過來,滿污穢的鄭沛恨不能昏死過去,偏吐完了一舒暢,想暈還暈不了。
艄公大驚,慌忙拋下長篙,向他請罪。
陸時卿也不比鄭沛好幾分。他人在池中,渾,滿面泥漬,鬢角還往下淌著水珠子,一只手如攥救命稻草般,攥著桿碧綠的蓮枝,周團簇了一圈紅艷的水芙蓉。
這場面,真當得起香艷二字。
一片死寂里,響起個脆生生的笑聲。
他一聽便知是誰,回頭狠狠剜了元賜嫻一眼,不料這下剜在帷帽垂落的白紗上,倒不疼也不。
岸上仆役已朝這向趕來。鄭濯也吩咐艄公往回撐去。
等到了陸時卿跟前,元賜嫻起白紗,低頭著他解釋:“陸侍郎莫怪,方才失笑,實是為您出淤泥而不染的風華所折。”
陸時卿渾一抖。
他已是兩害相較取其輕,這丫頭何必提醒他,池子里滿是淤泥,實則也不比鄭沛的穢好上多!
鄭濯失笑,吩咐岸上人去照管鄭沛,隨即起手向陸時卿道:“來。”
元賜嫻見狀,趕拾翠走去船頭穩穩,以免兩人靜太大這不靠譜的木舟翻了,卻見鄭濯一把拉起了陸時卿,而腳下的船依舊十分穩當,幾乎連晃都沒晃。
看了眼他發力的胳膊。
能如此輕松拽起一名與自己板差不離的男子,必是底子深厚的練家子。鄭濯此人,興許的確并非面上瞧來這般文氣。
陸時卿抖得渾上下每一骨節都在打架,剛著手腳在船尾坐下,泥水便從頭到腳緩緩淋淌了下來。
元賜嫻忍笑遞去一方錦帕:“陸侍郎,您?”見他面嫌惡,補充道,“想來這帕子比眼下的您干凈一點。”說完,笑著拿指頭比了個“一點”的手勢。
陸時卿咬牙,死盯著不。
鄭濯朗聲大笑,吩咐了艄公回岸去,見元賜嫻還著手,便接過的帕子塞進陸時卿手心,替他收了,道:“回頭我替你收拾九弟,你且回府好生沐浴歇息,今日就莫去教十三弟學問了。”
陸時卿終于“嗯”了一聲。
元賜嫻聞言笑意微滯,問:“陸侍郎平日都教十三殿下做學問嗎?”
鄭濯見他約莫吐不出話來,替他答了句“是”。
三人一道上了岸。
鄭沛面盡失,早已落荒而逃。陸時卿這般模樣,自然也被仆役送回了府。岸上只剩了元賜嫻和鄭濯。
兩人本是心照不宣,預備趁泛舟獨說話的,這下倒得來全不費功夫了。
鄭濯開門見山地問:“縣主方才何故與我共舟?”
元賜嫻示意拾翠退遠一些,莫旁人靠近,完了答:“殿下,咱們明人不說暗話。您大費周章與家兄串通,輾轉來見我,應是有話與我說。而我與您共舟,自然是想聽聽您的話。”
元鈺那個蹩腳的演技可謂百出,元賜嫻早便猜到了究竟。想來是鄭濯與兄長商量好了見一面,然后蹭了個鄭沛的方便。
語出直接,鄭濯眼底微訝異,道:“縣主直爽,我也不兜圈子。我此番前來,是想求娶縣主。”
元賜嫻覺得,這一句求娶,就像在說“要不今兒個午膳吃餛飩”一樣。
他面無波無瀾,便也聽得平靜,微微仰首注視他道:“殿下想娶我,何不與家兄、家父商議,或請圣人賜婚?拿這事問我,且不說是否有悖禮數,恐怕也是毫無意義。我若應了,您一樣還得回頭請長輩做主,我若不應,您便拋卻這念頭了?”
鄭濯答:“縣主與旁家娘子不同。我若不先過問縣主心意,盲目請旨,因此惹惱了滇南王,恐將難以收場。我亦知此番失禮,故而借了九弟的名頭前來。當然,所謂父母之命,妁之言,如縣主應我,該走的禮數,必然補齊了一樣不。”
這話聽來勉強算得上誠懇。有南詔太子那樁事在前,估著鄭濯也清楚滇南王多疼兒,想來詢問他老人家多半一場空,怎樣抉擇,還得聽元賜嫻的,不如直接點。
元賜嫻點點頭:“那麼殿下為何想娶我?”
鄭濯微微一滯。
笑了笑:“殿下不問我便罷,既說意聽我心意,至也該給我個應了您的理由不是?若真我抉擇,想娶我的人不,何必非得是您?”
鄭濯起先并無窘迫之,聽到后來卻目微,似乎被問住了。
繼續笑:“倘使此刻站在這里的是九殿下,興許還能理直氣壯說一句,他想娶我是因我長得好看。您呢?”見他仍不開口,牽了下角,“殿下誠意,我已看得分明,告辭。”
轉就走,鄭濯下意識腳步一移:“等等。”
元賜嫻回頭,見他猶豫了一下說:“今日是我唐突,然此時此地不宜言事,如縣主不厭棄,三日后,我將派人登門與令兄詳議。”
靜靜他半晌,道:“如此,三日后,我再決定是否考慮殿下的提議。”
小劇場:
陸時卿:導演,劇組是不是發錯劇本了?這場落水戲真是給男主的?
顧導(霸道總裁臉):你現在是在質疑我的專業嗎?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9018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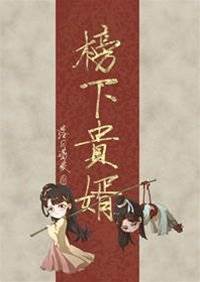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765 -
完結899 章
權寵天下:紈絝惡妃要虐渣
她不學無術,輕佻無狀,他背負國讎家恨,滿身血腥的國師,所有人都說他暴戾無情,身患斷袖,為擺脫進宮成為玩物的命運,她跳上他的馬車,從此以後人生簡直是開了掛,虐渣父,打白蓮,帝王寶庫也敢翻一翻,越發囂張跋扈,惹了禍,她只管窩在他懷裏,「要抱抱」 只是抱著抱著,怎麼就有了崽子?「國師大人,你不是斷袖嗎......」 他眉頭皺的能夾死蒼蠅,等崽子落了地,他一定要讓她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斷袖!
76.9萬字8 202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