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寧》 第001章 晴陽覆雪
“很小的時候,婉娘告訴我,這天下最尊貴的人是皇後,皇後居住的宮殿就做‘坤寧宮’。我就問婉娘,坤寧宮是什麼樣。”
“婉娘說,也不知道。
“我坐在鄉間雨的屋簷下,便想,如果能變作那天上飛過的鴻雁,能飛去繁華的京師,飛到那紫城裡,看一看坤寧宮是什麼樣,該有多好?”
宮門幽閉,僅左側一扇窗虛開。
天空沉,線昏暗。
往日熱鬧的坤寧宮裡,此刻一個宮人也看不見了。
隻剩下薑雪寧長跪坐於案前,用白皙纖細的手指執了香箸,在案上那端端擺著的錯金博山爐裡輕輕撥弄,縷般的煙氣自孔隙中悠悠上浮,織金銹的袂長長地鋪展在後,繁復的雲紋在幽暗中約遊著點點輝。
“後來,我果然到了京師。老天爺跟我開了個大玩笑,給了我一顆不該有的妄心,卻讓我在鄉野田間長大,沒養出那一京中名媛、世家淑的氣度,還偏把我放到這繁華地、爭鬥場,僅施捨予我一副好皮囊……”
薑雪寧的容貌是極明艷的,灼若芙蕖。
蛾眉婉轉,眼尾微挑,檀點朱,自是一渾然天的嫵,又因著這些年來執掌印、在高位,養出了三分難得的雍容端莊。
低眉斂目間,便能人怦然心。
尤芳在側後方靜立良久,聽著那渺似塵煙的聲音,想起在世人眼中機關算盡、爭名逐利的一生,忽然便有些恍惚起來。
竟有一種悲哀從心頭生起。
們都知道,已經逃不過了。
薑雪寧忽然就笑了一下“芳,這段時間,我總是在想,我果真錯了嗎?”
小時候,被婉娘養大,不知自己世,在莊子外的田園山水裡撒野,是一隻誰也管不住的鳥兒,隻有婉孃的胭脂水能讓回家。
Advertisement
婉娘出瘦馬,是人中的人。
說,天下是男人的天下,隻有男人能征服;而人,隻需征服男人,便也征服了天下。
輾轉回京後,認識了勇毅侯府的小侯爺燕臨,他帶扮男裝,在京城裡肆意玩鬧,連爹孃也不敢管教太多,頗有幾分竹馬青梅之意。
後來勇毅侯府牽連進平南王謀反案。
燕臨一家被流放千裡。
那尚未及冠的年在夜裡,翻了薑府的高墻來找,沙啞著嗓音,用力地攥著的手“寧寧,等我,我一定會回來娶你。”
薑雪寧卻對他說“我要嫁給沈玠,我想當皇後。”
猶記得,那年時的燕臨,用一種錐心的目著,像是一頭掙紮的困,紅了眼眶,咬了牙關。
那一晚年褪去了所有的青,放開了的手,轉遁黑暗。
五年後,已是沈玠的皇後。
登上後位的路並沒有那麼順利,所以在短暫的生命裡,像燕臨這樣的人還有不。
比如吏部侍郎蕭定非。
比如錦衛都指揮使周寅之。
甚至,是後來殞夷狄的樂長公主沈芷……
隻是,誰也沒想到,昔日年會有捲土重來的一日。在邊關立下戰功後,燕臨投了謝危,打著“清君側”的旗號,披甲歸來,率軍圍了京城,控製了整座紫城,也將。
沈玠被人下了毒,纏綿病榻,不理朝政。
他便堂而皇之地出宮廷,每每來時屏退宮人。
朝堂外,無人敢言。
人人都知道,他是謝危的左膀右臂。
謝危屠了半座皇宮的時候,是他帶兵守住了各宮門,防止有人逃走;謝危抄斬蕭氏九族的時候,是他率人撞開了閉的府門,把男老抓出……
如今,他便與那一位昔日的帝師謝危,站在宮門外。
沈玠已經駕崩,留下詔書命垂簾聽政。
然而從宗室過繼來的儲君,尚未扶立登基,便在趕來京師的途中,被起義的天教黨割下頭顱,懸在城門。
現在,到了。
薑雪寧輕輕眨了眨眼,濃長卷翹的眼睫在眼瞼下投落一片淡淡的影,讓此刻的神帶上了幾分世事變幻難測的蒼涼。
尤芳有些悵然地著。
卻已擱下了香箸,蓋上香爐,取過了案上那四四方方的大錦盒,開啟來。裡麵端端地放著傳國玉璽,和一封一個時辰前寫好也蓋了印的懿旨。
懿旨裡寫,自願為先帝殉葬,請太子太傅謝危匡扶社稷,輔佐朝政,擢選賢君繼位。
薑雪寧忽然抬首向窗外看了一眼。
不知什麼時候,下了一夜的雪已經停了。
耀眼的從沉的雲裡出來,照進這慘宮廷的窗,投下一束明亮的線。
呢喃了一聲“若早知是今日結局,何苦一番汲汲營營?還不如去行萬裡路,看那萬裡河山,當我自由自在的鳥兒去。這輩子,終不過是誤宮墻,繁華作繭……”
尤芳默然無言。
薑雪寧便問“芳,若給你一個選擇的機會,你還會來嗎?”
尤芳是薑雪寧認識過的所有人裡,最奇怪的那一個。
本是個伯府庶,笨拙可憐,一朝跌進水裡竟然大變了,從此拋頭麵、經商致富,開票號、立商會,短短幾年間便了江寧府首屈一指的大商人。
“尤半城”也不為過。
隻是運氣不好,在這一場宮廷朝堂的爭鬥中,先站錯了隊,後來雖也投誠了謝危,可這些日子以來也被防著,在這宮中。
兩人慘到一塊兒,倒了無話不說的知己。
薑雪寧聽講白手起家的經歷,好多都是新奇的話兒,還聽抱怨經商時去過的海外夷國,連蒸汽機都沒出現。
蒸汽機是什麼,薑雪寧不知道。
但尤芳總說自己並不是這兒的人,而是來自一個很遠的、已經回不去的地方。
還說,前朝有一個巨大的,如果知道了它,但凡有點腦子的人都不會在這一場爭鬥中行差踏錯。
隻是可惜,知道得晚了。
尤芳幽幽地嘆了口氣,苦笑“這鳥不拉屎還凈氣的時代,誰穿誰穿去!”
薑雪寧好久沒聽過這麼鄙的話了,恍惚了一下,卻想起時辰來,隻忽然揚聲喊道“謝大人!”
朱紅的宮墻上,覆蓋著皚皚的白雪。
宮門外黑一片人。
燕臨按劍在側。
為首之人長而立,聞言卻並不回答。
薑雪寧知道他能聽到。
這是整個大乾朝心機最深重的人。
聖人皮囊,魔鬼心腸。
兩朝帝師,太子太傅,多人敬他、重他、仰慕他?卻不知,這一副疏風朗月似的高潔外表下,藏著的是一顆戾氣橫生、覆滿殺戮的心天子所賜的尚方劍下,沾滿了皇族的鮮,殺得護城河水飄了紅;琴執筆的一雙手裡,扣著蕭氏滿門的命,牽連者的堆疊如山。
這是唯一一個窮盡渾解數也無法討好的人。
“您殺皇族,誅蕭氏,滅天教,是手握權柄、也手握我命之人,按理說,我沒有資格與您講條件。”薑雪寧眼底,突地墜下一滴淚來,烙在手背上,“我這一生,利用過很多人,可仔細算來,我負燕臨,燕臨亦報復了我;我用蕭定非、周寅之,他們亦借我上位;我算計沈玠,如今也要為他殉葬,共赴黃泉。我不欠他們……”
一生飄搖跌宕的命跡,便這般劃過。
匕首便在袖中。
輕輕將其拔i出,寒閃爍的刃麵,倒映著的眼和鬢邊那一支華的金步搖。
薑雪寧的抖起來,聲音也抖起來,眼底蓄滿了淚,可也沒資格去哭,隻一字一句,泣般道“可唯獨有一人,一生清正,本嚴明治律,是我脅之迫之,害他誤歧途,汙他半世清譽。他是個好,誠謝大人顧念在當年上京途中,雪寧對您喂之恩,以我一命,換他一命,放他一條生路……”
誰能料得到,薄冷彷彿沒有心的皇後孃娘,如今會有一日,以己之命,換區區一刑部侍郎?
究竟是沒心,還是旁人沒能將這一顆心焐熱呢?
宮門外那人久立未。
過了好久,才聽得平淡的一字“可。”
真是好聽的聲音。
還像很久以前。
薑雪寧釋然一笑,決絕抬手——
“噗嗤。”
鋒銳的匕首,劃破纖細脖頸上的脈時,竟是裂紙一般的聲音,伴隨而起的,似乎還有宮門外誰人長劍墜地的當啷聲響。
也倒下去了。
緻的金步搖砸在地上,上頭鑲嵌著的深紅寶石碎了又飛濺出去。溫熱的鮮,順著臺階,在冰冷的地麵上慢慢浸開,像極了年時常腳踩著玩的那條淺淺的溪水。
誤宮墻,繁華作繭。
這坤寧宮,終了吞骨、葬命的墳墓。
窗外晴出來,照在雪上,一點一點,到底慢慢化了……
好長的一夢,夢裡一世因果全都混沌,唯有刃鋒過頸時的覺,清晰至極。
真疼。
薑雪寧想,早知道,該選個不疼的方式去死。
“咳。”
夢裡好像有什麼著口,讓不過氣來,於是咳嗽了一聲,終於費力地睜開了眼。
然而這一看卻嚇著了。
躺在一張淩的榻上,更確切地說,是躺在兩個男人中間。近在咫尺,是一張雋秀儒雅的青年的臉,幾乎與氣息相,甚至還抬了一隻手來大大咧咧地攬住了。
薑雪寧簡直頭皮一炸。
這場景,不得不讓想到當初燕臨返朝後,將,總是悄無聲息踏宮中,讓連覺都睡不安穩……
一下把這人的手甩開,翻從榻上站了起來。
那青年醉夢中掀開眼簾,倒奇怪這般舉,隻半坐起來,還要手去拉“唔,薑兄我們繼續睡——”
“放肆!”
好歹是當過皇後甚至號令過百的人,薑雪寧聽他出言不遜,還見他舉止放浪,完全下意識地一掌朝他臉上甩去!
“啪!”
這一聲響亮得很,終於驚了榻另一頭枕著劍酣睡的玄袍年。
他睜開眼,是長眉鼻薄,自有一銳氣。一看這場景,有一剎的茫然,可接著就瞥見了華服青年那淩的袍和右側臉頰上五道微紅的手指印,以及薑雪寧那一張又驚又怒的臉。
“錚”地一聲,年反應過來,瞬間步擋在薑雪寧前,拔劍出鞘,劍尖在了青年脖頸!
尚存一分青的麵容上覆滿冰霜。
他寒聲質問“你對做了什麼?!”
青年一則驚訝於他竟這般沖敢拔劍向自己,二則又委屈又無辜,不由捂住了自己的臉頰“能做什麼?本王又不斷袖!”
年眉峰皺起,看他的眼神十分懷疑。
本王……
薑雪寧忽然愣住了。
直到這時候,才後知後覺地聞見自己一酒氣,發現自己穿的是銀線繡竹紋的青袍,作年打扮,剛纔打人的手掌上也傳來火辣辣的疼。
扮男裝。
不是在夢中。
而那被劍指著的青年的臉,和這擋在前的年的影,終於漸漸從記憶中浮了上來一個是後來當了皇帝的臨淄王沈玠,一個是後來當了臣的小侯爺燕臨!
這就是尤芳常唸叨的“重生”嗎?
前世小心謹慎,哄得男人們團團轉,這一世剛開始就甩了未來皇帝一掌……
現在跪下來謝罪,來得及嗎?
坤寧
坤寧
猜你喜歡
-
完結232 章
腹黑郡王妃
一覺睡醒,狡詐,腹黑的沈璃雪莫名其妙魂穿成相府千金.嫡女?不受寵?無妨,她向來隨遇而安.可週圍的親人居然個個心狠手辣,時時暗算她. 她向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別人自動送上門來討打,休怪她手下不留人:姨娘狠毒刁難,送她去逛黃泉.繼母心狠手辣,讓她腦袋開花.庶妹設計陷害,讓她沒臉見人.嫡妹要搶未婚夫,妙計讓她成怨婦.這廂處理著敵人,那廂又冒出事情煩心.昔日的花花公子對天許諾,願捨棄大片森林,溺水三千,只取她這一瓢飲.往日的敵人表白,他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心,她纔是他最愛的人…
155.2萬字5 59507 -
完結752 章

盛世凰歌
擁有精神力異能的末世神醫鳳青梧,一朝穿越亂葬崗。 開局一根針,存活全靠拼。 欺她癡傻要她命,孩子喂狗薄席裹屍?鳳青梧雙眸微瞇,左手金針右手異能,勢要將這天踏破! 風華絕代、步步生蓮,曾經的傻子一朝翻身,天下都要為她而傾倒。 從棺材里鑽出來的男人懷抱乖巧奶娃,倚牆邪魅一笑:「王妃救人我遞針,王妃坑人我挖坑,王妃殺人我埋屍」 「你要什麼?」 「我要你」
132.9萬字8 10928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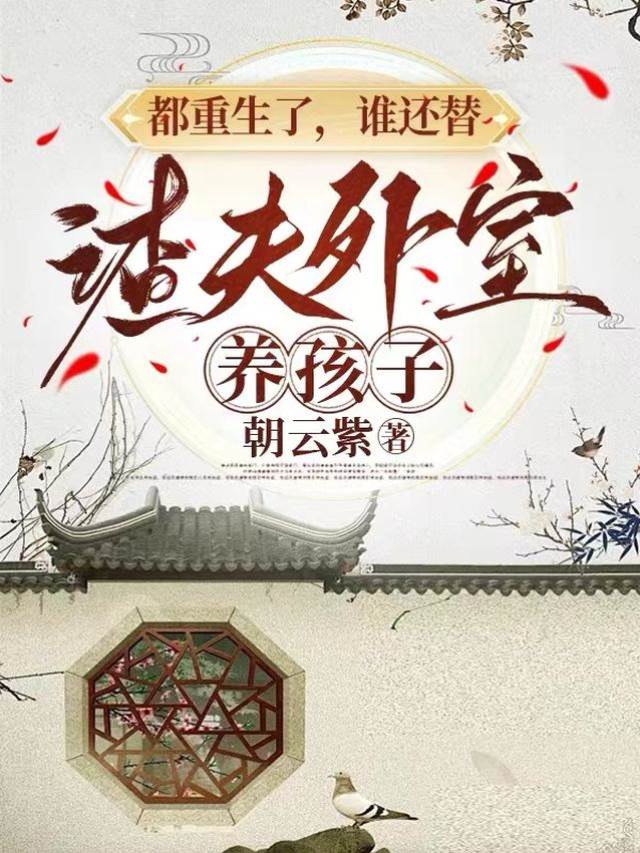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