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情》 027、好壞的馬老師
這是一段真實的故事,當事人的我如今已近而立之年,十幾年的那一幕至今曆曆在目,我不知道是否值得回憶,但每每想起,總有回味無窮的覺。初三快畢業時,馬老師接手了我們班的語文教學。是這樣一位年輕的婦,麗如姣月,修長的段出一青春的氣息。的到來使我們班男生的語文績普遍提高,更是我們這些於青春期的男生手時所幻想的對象。
我出生於農家,學有所是我的唯一出路。對如我這樣的學生,馬老師都比較重。中考結束,準備回鄉下,但連日來的豪雨沖斷了我回家的路,我只好等在空的宿舍裡。眼看學生食堂就要關門了,我正在為就餐著急,馬老師來了,對我說:“這樣吧,你上我家吃住一段時間”馬老師新婚不久的家在頂樓,的老公到深圳開發經濟窗口去了,長時間不能回來,二室一廳的居室裡清靜而優雅。我那時剛過十五歲,與自己的老師獨一室顯得極不自然,不過的麗讓我新奇而激。瓢注般的大雨似乎預示著要發生什麼。
半夜裡我被一只手弄醒了。窗外是刷刷的雨聲,四周黑沉沉的,我嚇得一不,更不敢睜開眼睛。我仰面朝天地躺著,馬老師的一只手在蠕!那纖細的手指輕輕挑起我的三角,停了一下,看看我沒醒,就很小心地把我的ji勾出來。我心裡好激,卻因為旁是我的老師,我只有裝睡。那時的我才發育兩年,只有很稀疏的,但由於長期的鍛煉,我的很健康,ji雖然不是很,但起來足足有12cm長。
馬老師用暖乎乎的手輕輕的弄它,我無論如何抗拒不了這種激,ji很快起來。我閉著眼,覺老師的另一直手在自己的大,整個的人在輕輕的抖,然後就聽到了一聲輕微的歎息抑或是氣。
早晨醒來,我一不睜開眼,看到自己的老師穿著睡袍躺在邊,它那雪白的和呈現在我的眼前,一條輕微的卷曲著,幾彎彎曲曲的探頭探腦地從雪白的三角邊了出來,薄薄的三角勾勒出xiao的凹凸,還有一塊粘結後留下的斑痕。我突起心,想老師的,我裝著睡覺翻的樣子,迅速地把一只手扣在老師的上,但因為心裡太激,什麼覺也沒有。過一會兒,老師起床走了,我裝做什麼也不知道似的又睡了半小時。
第二天老師問我:“睡得好嗎?”
我說:“好極了,一覺到天亮”第二天晚上,故伎重演,只是老師的手比頭天晚上更大膽。第三天晚上,老師對我說:“你今天晚上到我房間睡吧,我怕打雷”晚上老師問了我許多的問題,我以為只是等我睡著後地我的ji,那知在了我一會後,捉取我的一只手放到的房上,驅使我的ji迅速地脹起來。馬老師的一只手地抓著我的ji,來回急速地圈套,裡輕輕地著:“你人這麼小,東西卻這麼大。”
我什麼都不懂,只覺得自己要窒息。
老師下的睡袍,出兩個堅雪白的nai子,然後一把把我翻到的上,接到溫潤如脂的,只覺得呼吸急促。“做一回我的丈夫吧。”
馬老師起屁,下小小的三角,把我的手牽引到的大部,我像木頭人,手指是一堆忽忽的東西。馬老師分開大,用手抓著我的ji在的桃園小山包上來回,我的ji所覺到的是一個熱乎乎、漉漉的的。
馬老師的一只手在自己的上索著翻開大yin,然後把我的ji放到的yin道口,我的gui頭就像被一個潤的小咬著。“快,快,快用力……”
老師邊說邊用雙手推我的部。我一用力,ji“刺溜”一下像進了一個深淵,熱乎乎、漉漉、繃繃,還不時收,與此同時,老師輕輕哼了一聲,見我不,老師道:“快”我那時不知道是來回,只是使勁用力往下自己的ji,老師的yin道猛然一收,我只到一陣漩渦向我襲來,堅的ji在老師的yin道裡跳,jing狂不已。老師“啊……啊……”
大兩聲,猛然抬起自己的屁,同時雙手死死地摳住我的部。
過了好久,我才清醒地覺到老師的手在我的頭發,我的ji還被老師的小地夾著,我張得要命,從的上一躍而起,“啊”地大一聲:“你怕嗎?”
我點點頭。“別怕,來,我吧。”
這時的馬老師,整個的青春赤地暴在我的眼前。
長長的秀發下麗的臉龐有一抹青春的紅暈在遊,nai子渾圓而堅,老師的nai子並不大,是極的1/3球的那種,兩個嘟嘟的頭微微翹起,四周是圓圓的暈,清晰得就像用紅的彩筆圈畫上去似的。纖細的柳腰下是凝脂般而平坦的小腹,大雪白而修長。
老師的xiao在小腹下微微的隆起像一個小饅頭,是稀疏黑黑而卷曲的那種,兩片雪白的大yin地地粘合在一起,粘合形一條裂,裂的兩邊是淡淡的茸。看到老師的部,一強烈的沖使我想去探過究竟:“老師,我想看看您……您的……”
老師笑了:“想看什麼哇?”
然後對著我的耳朵說:“那,你想看老師的,你就看吧”說著把兩條修長的大分開樹放在床上。
我倒轉過子,用手開兩片雪白的大yin,老師那紅的xiao立即呈現在我的眼前,小yin微微地揚著小腦袋,紅的小yin因為充和的滋潤而向兩邊驕傲地張開著,yin道小口因為剛被我的ji過而潤。看到如此可的xiao,我忍不住親上一口,多年後,當我過各各人種的後,才知道老師的是最的。
我這一親,老師整個人抖了一下,“啊……”
地了一聲,好奇驅使我去翻弄老師的xiao,又忍不住不斷地親、,“哎喲……哎喲……啊……嗯……”
老師的在扭曲,一條明而油亮的從老師的yin道口流出,我一口把吸進裡,老師的微鹹而潤。這時的老師完全不能自持,一口把我還沒有完全起的ji吸到的裡,用舌頭來回攪,那熱乎乎、溫的覺使我的ji一下子脹到極限。“我……我不行了,我要你我,來……老師教你幾招……”
說著,馬老師一把把我推倒床上,我看到自己的ji直地豎著,老師迅速地騎到我的上,屁很練地擺兩下,我的ji就被的套住,然後一用力,剛才還直的ji轉眼間就被老師的齊吞下,它上下急促地聳著自己的屁,我只看到自己的ji在的黑黑的間來回出沒。此時的老師閉著眼,屁上下聳,裡高:“啊……嗯……哎喲……xiao好舒服……”
我的ji被老師的來回急速地套著,只覺到發脹發痛,但由於剛完,卻始終堅如鐵。老師每次抬起的屁,我就看到ji上粘著白的漿。
老師就這樣不停地套了十幾分鐘,然後就撕心裂肺地“啊……啊……”
大幾聲,整個人一下子在我的上,抖,yin道一陣又一陣的在收,順著我的ji流了我一,老師達到了高。
這激的浪讓我一躍而起,一把把還在氣的老師推倒在床上,起堅如鐵的ji再次老師微紅的xiao。我以十五歲年不經世事的狂熱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用自己的ji狂自己老師的xiao。
老師喊著,頭來回擺,子不斷地扭曲,兩只手一會兒抓床單、一會兒又拿起枕頭塞住因為而大張的,一會兒又來抓我的背部,兩條高高地分樹在天空,腳趾因為痙攣而地彎曲在一起。看到這一切,征服的噴張在我的心頭,ji更加賣力地狂不已,我再次聽到老師撕心裂肺的喊,老師的再次收不已,的不斷噴出讓我的ji覺到一陣陣地發燙。
十五歲的年於花季,那沖勁似一個發的火車頭,我不知道自己一刻不停地上下了多長時間,只知道自己的汗珠像雨點般落下,子底下的老師兩個頭豎,手在抓,呼吸急促,眼淚直流。狂的ji從老師那玫瑰的小裡帶出來許多白的漿,粘在老師的和雪白的床單上。
急速的不知過了多久,一熱浪向我襲來,一陣目眩後,脹痛的ji在老師乎乎的不斷收的rou裡狂跳不已,我一下子癱倒在老師溫的上,任由ji把滾燙的jing老師的xiao,老師的兩條轟然放下,兩手死死地摳住我,嚨裡撕裂般地發出一聲長長的呼:“啊……”
然後就氣若遊般地癱在床上,只有在急速地起伏。我們很快地睡著了,老師本來就窄窄的因為高後的收而把我的ji地夾住,起來時看老師的因為一夜的瘋狂已是被得通紅,床單上除了大片的粘痕外還有斑斑的跡,我的背部也被老師抓下幾條痕。
整個暑假,我就與老師呆在一塊的樂趣,老師教會了我各種姿勢和技巧,由於我們每天都上三次以上,每次我的ji都是被夾在老師窄窄的裡用泡著而睡去,我現在長著一18cm長的ji,老師說:“那是我的長時間滋養的結果”馬老師是這樣記述我們在一起所過的暑假生活,夜來雨注傾盆,紅綃帳中聞師聲,年未ji,抓不出門。妙妙妙,高中三年,馬老師教了我三年語文,我了三年。
為我主持的十八歲年禮就是在那一天裡我們閉家門,擺上各種姿勢,用兩手翻開自己的讓我,並且為我做了記錄:高:176cm,重:65kg,ji:16x3·8cm。
這一天,要我十八次,以紀念這特殊的日子,最後老師的部腫得像個紅桃子,大小yin外翻好幾天才恢複原狀,我的ji也是用熱巾捂了好幾天才有知覺。後來我上了大學,寒暑假裡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在一起魚水之歡,在大學四年裡,我了多同校和外校的生,我也記不得了,有些值得回憶的,我將在《大學的瘋狂》裡告訴諸君。
就即使我進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到後來去瑞士、紐約和莫斯科工作,我還偶爾回國與老師分床第的歡樂。最近與老師相會,依然是如此的麗,床上的功夫勝過當年,為了這短暫的相會,要求我的ji一直放在的裡。
老師已近四十,我也將屆而立,在我瘋狂地了讓幾次如癡如醉的高之後,老師溫地躺在我的脯上:“你了,ji又長又,這麼惹人喜,真有男子漢的魅力”“這是老師培養的結果,當我妻子香奈子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都嚇哭了”“是啊,我是看著你的ji長大的,它是不是了很多?”
“是的,我將有一些回憶的文字,記述這些年來我的風流,除了《大學的瘋狂》外,還有《一城一妾》《歐雜記》《風流莫斯科》等,不過,在我所的中,老師的是最的,因為小巧、細白、鮮而紅。我真的好喜歡老師您的。”
“你隨時都可以來,老師的將永遠為你的大ji準備著,老師將隨時張開雙迎接你的到來。”
猜你喜歡
-
連載322 章

情欲青春
一位八零後男青年,從青春期走向性成熟期間的情欲往事。從花季少年到三十而立,林青的人生之路,情欲洶湧,百花盛開,春色無邊。一個個的女孩、熟女、少婦,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回憶。女人是男人最好的大學——謹以此文紀念那逝去的青春歲月。
59.7萬字7.59 312539 -
完結80 章
龍神是個騙炮狂
修煉成型的第一天,夏天決定找個男人,通過“采陽補陰”提升修為。然而,她卻不知道,自己的采陽對象,竟然是從三界消失了萬年之久的龍神墨離。墨離告訴她,因為她的修為太渣,她采陽不成,反被別人采了。三魂七魄丟了一魄,她只剩下三年陽壽。想要拿回魂魄,兩人雲雨一次,可以延壽三天。夏天算了算,要拿回原本五百年的壽命,她需要向墨離獻身:六萬零八百三十四次……毛都要被他做禿了啊……P.S.1.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虐身,不會變態血腥。2.我也不知道算甜寵文,還是追妻火葬場。3.嬌軟傻白甜女主 x 高冷白切黑男主4.1v1,SC,劇情肉,盡量不會為肉而肉。5.作者是個老沙雕,會忍不住寫沙雕梗。6.完結之後,H章開始收費了。一個吃女孩子不吐皮的故事。已完成:《離朱》點擊直達正在寫:《大理寺.卿》點擊直達
15.7萬字8.33 68215 -
完結105 章
蘇桃的性福生活
蘇桃本是京城商戶之女,年方十六,為了求得一個好姻緣隨娘親去音源寺廟上香,不想被個色和尚盯上破了身。 失貞女子如何能嫁人,不想男人一個接一個的來了。
19.2萬字8.09 251507 -
完結326 章

洞仙歌
微博:化作滿河星他喜歡殺人,她喜歡吃飯。他嫌這小道士既寒酸又笨舌,小道士本人覺得挺冤。她下面沒那二兩貨,不得低調點嗎?愛殺人、會殺人並且想殺人的小王爺因為同命結不僅殺不了 還被迫和鹹魚小道士綁一塊除妖 一起做春夢的故事。前期互相嫌得像狗,後來彼此纏得似蜜,橫批:真香玉面閻羅小王爺×腹誹貪吃小道士女扮男裝,全是爛梗,男主不是好人,多壞還不確定。進度慢,劇情向。封面我寫的,我超棒
59.4萬字8 113324 -
完結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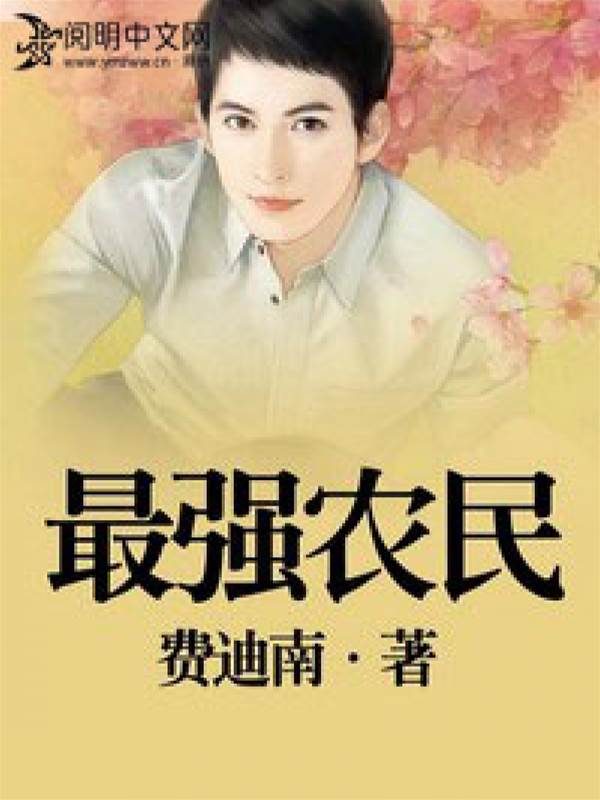
最強農民
作為世界上最牛逼的農民,他發誓,要征服天下所有美女!
14.3萬字8.18 126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