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嫤語書年》 第21章 淮陽
賊衆被裴潛帶來的軍士打退,激戰一場,衆人在路旁就地休整。
府兵傷了幾個,所幸無人喪命,有人正給他們包紮。馬車被賊人使了絆馬索,拉扯的兩匹馬都摔傷了,車廂也壞了。
魏安方纔被府兵護衛著,毫髮未傷,此時又鎮定地坐在牛車上擺弄他的木件,不時擡頭瞥瞥這邊。
我坐在路旁的大石上,面前,裴潛一直站著,上的青袍修長。
許久不見,他的形壯實了許多,不再是當年那個臨風詠賦的單薄年。他的腰間懸著劍,眉宇也寬了些,儒雅依舊,卻多了幾分殺伐之氣。
我曾設想過我和裴潛再見面會是什麼樣子。
他娶新婦的時候,我覺得我會對他又抓又撓罵他負心,然後沒出息地求他娶我;我嫁去萊的時候,我覺得我會撲上去痛哭一場,然後沒出息地求他娶我;而五年之後,當現實與時磨滅了所有幻想,我已經不再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就像現在,我面對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有人正向裴潛稟報賊衆傷亡,裴潛聽著他說話,好看的雙眉微微蹙起。他沒有轉也沒有走開,時不時問些話,聲音清澈,正如長久在夢裡徘徊的那樣悉。
說完了話,那人走開,裴潛再度轉過頭來。
“飲些水麼?”他問我。
我搖搖頭。
“用食麼?”
我搖搖頭。
“還害怕?”
我沒有表示。
裴潛微微彎腰,看著我,片刻,輕聲道:“阿嫤,說話。”
我著那雙眼睛,仍然不開口。
裴潛低低地嘆了口氣,直起,回頭對一名軍士道:“收拾車駕馬匹,回淮。”
那軍士應下,轉傳令。
Advertisement
我吃了一驚,看他們的架勢,是要帶上我們一起走。
“我……我不去淮!”我心急之下口而出,聲音的。
裴潛看向我,苦笑:“我以爲你再也不出聲了。”
我咬咬脣,心知被他破了功,有些懊惱。
“我不去淮。”我重新說一遍。
“不去?”裴潛臉平和,“你看看護衛你的兵卒,有幾個不帶傷,此去雍都最快也要八九日,他們走得了麼?若再遇上些匪徒,又當如何?”
我被他問住,一時語塞。我想堅持,卻不得不承認裴潛的話沒有錯。心狐疑不定,臉也跟著晴莫辯。
“還有什麼話要問麼?”裴潛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道。
我猶豫一下,瞅著他:“你怎會在此?”
魏傕伐譚熙,兵力只有對方的一半。天下割據,各路豪強之間虎視眈眈,魏傕一方面顧忌寡不敵衆,一方面有顧忌後方無人,於是,東南的吳璋就了魏傕的結盟首選。魏傕與吳璋約定,吳璋出兵五萬,與魏傕共同伐譚,事之後,淮水流域盡歸吳璋。
吳璋在淮擁兵二十萬,倚仗山澤天塹,本是一塊難嚥的骨頭。這五萬兵馬,對於魏傕來說其實只能算個零頭,但是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把背後的包袱給吳璋,讓他牽制荊楚蠢蠢的樑充。
於是,魏吳界的淮南了兩軍共守之。
而裴潛,是吳璋駐在淮南的主將。
他對我說這些的時候很耐心,毫無保留,就像我從前問他問題的時候一樣,他說完了,就看著我,用眼神詢問我聽懂沒有。
若在從前,我會想七想八,拿些全不著邊際的念頭來煩他。可是現在,我聽完以後,默默地點點頭,不再說話。
馬匹換上了好的,車廂壞了半邊,但還能走。
我就坐在這樣的馬車上,滿腹心事,顛顛簸簸地去了淮。
淮是淮南郡的郡府所在,也是我在淮南看到的唯一還像個樣子的城池。因爲戰事的關係,這裡除了民人,街上到能見到拿著武的軍士,見到人馬來到,紛紛讓開道路。
穿街走巷,裴潛把我安置在城中一安靜的宅院裡。
“前面挨著的就是我的府衙,你且歇息,我去去就來。”他對我說。
我頷首,沒看他的臉。
裴潛沒再說什麼,轉走開了。他的腳步聲消失在門外,卻在我的耳畔延續了很久。
“夫人……”阿元看著我,滿臉擔憂。自從見到裴潛,和我一樣心緒不定,在路上的時候就言又止。
我知道想說什麼。裴潛怎麼會突然出現,我們到了這裡之後又該如何?可我現下的心思也一樣渾渾噩噩,要想的東西太多,反而不知從何說起。
轉眼,我看到魏安立在庭院裡,手裡拿著他的木件。
我開始後悔帶他出來。剛纔遇襲,要是魏安有個三長兩短,我就真的不用回去了。
“長嫂,我們要留在此地麼?”見我走過來,他問。
我點頭:“許多府兵了傷,馬車毀壞,暫且上不得路。”我看他神,溫言道,“四叔莫怕,淮也有朝廷兵馬,回程時只消多派人手,必不會再有遇襲之事。”
魏安搖頭:“我不怕。”
我當他是年逞強,笑了笑。
魏安著我:“真的,那些賊打不過兄長的軍士,別看我們這邊傷了幾個,可他們被斬殺了十餘人。”
這我倒沒仔細看,想來當時被突然出現的裴潛震傻了。
“哦?”我看著魏安認真的樣子,忽然來了興致,“你怎知他們是賊?他們可有箭有刀呢。”
“箭都是製的,有的箭頭還是石塊;刀大多是鄉人的柴刀,打不過兵刀。”他皺皺眉,“長嫂,兄長的軍士真的很強,即便無人來救,我等也不會有閃失。”
我正尋思著該怎麼給這個小叔子解釋裴潛,他提起這茬,倒是正好開口。
“四叔,”我說:“方纔來救的那位將軍……”
“是季淵公子。”魏安道。
我沒想到他一下說了出來,愣住:“你認得他?”
“認得。”魏安的表淡淡:“我在長安時,他曾到家中邀兄長騎馬。”
我驚詫不已。
裴潛竟與魏郯相識,我怎麼不知道?
“他們……”我頓了一下,覺得要說得再清楚些,“我說的是夫君與裴將軍,很好麼?”
“不知,”魏安道,“我只在宅中見過兩三回。”
我看他眼神閃爍,片刻,問:“四叔還知道什麼?”
“季淵公子是長嫂以前的未婚夫。”
我的額角又開始發脹。
在這個小叔眼裡,我已經沒有什麼了,甚好。
裴潛走開以後,許久也沒有再出現。
他給我安排的宅院不錯,雖不大,卻乾淨舒適。府兵們被安置去了別,裴潛另派了軍士守在宅院外,人影綽綽。
我的屋子,進門可見一案一榻。
案上有壺有杯,壺裡的水還是熱的。我開了壺蓋來看,裡面泡的是槐花,還有蜂的味道。
榻上有幾本書,我翻了翻,都是些志怪的小經。
許多年過去,我喜歡什麼,裴潛仍然記得清楚。
我到有些累,走到室,在臥榻上躺了下來。
榻上的褥子很。奇怪的是,當我閉上眼睛,頭腦昏昏沉沉,有件事卻格外清醒。
魏安說,魏郯和裴潛在長安的時候就認得了。
魏吳結盟,裴潛在淮南的事,魏郯不可能不知道。
那麼……
щшш◆ тt kān◆ ¢ ○
“……夫人亦知曉,我與夫人婚姻,乃出於權宜……”魏郯的話驀地迴響在心頭。
當時聽到的時候我覺得驚詫,現在卻越來越覺得耐人尋味。
魏郯是故意的麼?他知道裴潛在這裡,所以讓我來淮南?
那裴潛呢?他今天出現的時候,掀開車幃就喊“阿嫤”……
許是力耗費太多,這一覺我睡得很沉。當我醒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屋裡很暗,我的上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層薄被。
我拉開被子,起下榻。待我推門出去,只見庭院裡燈火寥寥,阿元他們不知道去了哪裡。
“醒了?”一個聲音從廊下傳來,我去,卻見裴潛正坐在階上,那姿勢,似乎待了很久。
“嗯。”我答道。有一瞬,我仍然以爲自己在做夢,可是到涼涼的晚風和燈籠下裴潛疲憊的神,我覺得這是真的。
“了麼?我帶你去用膳。”見我不說話,裴潛又道。
我沒答話,卻走過,隔著廊柱看他。
“裴潛。”
這聲音出來的時候,我能覺到他明顯怔了一下。
我幾乎從未稱過他的全名。張口的時候,我有些猶豫,可還是了出來。這般勢,我刻意地想同他拉開些距離。
“嗯?何事?”他沒有異,仰頭看著我。
我咬咬脣,道:“白天的時候,我曾問你怎會在此。”
裴潛笑笑:“我不是答過了麼,魏吳結盟……”
“不單是此意,”我打斷,看著他,“你去救我,並非過路。你早就知道我會來,對麼?”
作者有話要說:告訴大家一個不好的消息,存稿用完了……
風在耳邊輕拂,夏蟲低鳴。
我等著裴潛說話,他卻只看著我,好一會,浮起無奈的笑:“我正愁如何說起,你倒提了起來。”
心像被什麼了一下,我盯著他。
“坐著聽還是立著聽?這話說起來不短。”裴潛拍拍旁的石階,過了會,從上下裼鋪在石階上。
我皺眉:“不用你的服墊……”
裴潛斜眼一睨,我邊的話突然嚥了回去。
當我在那墊著裼的臺階坐下的時候,心裡不是不鬱悶的,過去多年了,怎麼還會這樣習慣地被他一個眼神堵住話頭。
“今日我是特地去追你的。”裴潛一點彎也不繞,道,“孟靖上月就曾來信,說你會來淮南。我不知你何時來,一直等候。月初我有事去了揚州,幾日前才得知你已經在路上,急忙返來。”說著,他舒一口氣,雙目中浮起溫潤的神采,“幸不曾耽誤。”
他沒有否認他與魏郯相識,可等他把事一五一十的說出來,我的心已經不能用驚訝來形容了。
裴潛自習劍,雖然以文采名,卻一直對武事興趣高昂。
這我是知道的,不過,我不知道先帝在宦子弟中拔擢年羽林郎的時候,裴潛也曾經報名。
這事他不僅瞞著我,也瞞著家人。教場比試那日,他特地在臉上畫了眉了假胡,教人認不出來。
比試的前幾場,裴潛很順利,可就在要過關的最後一場,他輸了。
打輸他的人,就是魏郯。
這一戰打得激烈,裴潛雖敗,卻因此結識了魏郯。二人雖見面不多,卻相互欣賞,常常比試劍法。
後來,天下罹,魏郯追隨父親征戰,而裴潛祖籍揚州,舉家避回到故土。
二人再見的時候已經是魏郯定都雍州以後。魏郯出於形勢的考慮,一向與吳璋和好,一次,裴潛命去雍州見魏傕,與魏郯見了一面。他說我在萊,求魏郯把我帶出來。
魏郯一口答應。後來,他也真的做到了,他用的方法,就是娶我。
“他一直想尋空隙送你出來,可一直出征在外,我這邊又因事拖延,故而只得暫將你留在雍都。直至夏初,孟靖來書與我商議,方纔將此事敲定。”裴潛看著我的神,說,“阿嫤,此事牽扯要,孟靖不與你說,也有他的考慮。”
我坐在階上一不,也沒有說話。
腦子裡回想起許多東西。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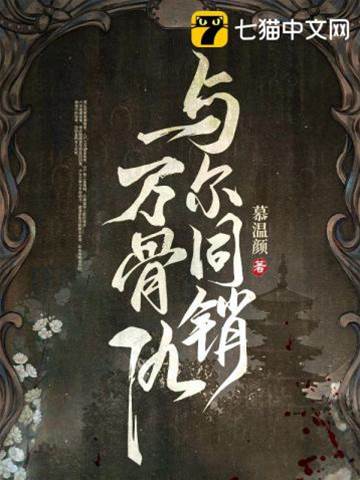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