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迷津渡》 第9章 第 9 章 自己脫還是我幫你。
第9章 第 9 章 自己還是我幫你。
9.
男朋友……
竟然喊他男朋友?
不似之前那般的戲弄,而是親昵、溫地他男朋友。
可不是說,做男朋友的前提是永遠不記得以前的事嗎?
是不介意他會恢複記憶,還是一時興起?
沒事,就算那樣也沒事,他安自己。
這樣的轉變,已足夠令他靈魂栗。
他願意被踩在腳下玩弄,哪怕明天就被拋棄。
至今晚,天使用潔白的擺掃過惡魔漆黑的面龐。
周景儀見他半天沒靜,轉頭催促:“快點兒啊!我還得出去呢。”
他忘了回應,只覺得生氣的模樣都可。
“謝津渡!”周景儀耐心耗盡,想發火。
他猛地回神。
昏暗的燈下,孩如瀑的長發鋪撒在後背,泛著盈盈的澤。
想要扣紐扣,得穿過這些蓬松的發。
手指剛上去,一陣暖融的香氣便撲至鼻尖——
橙花和海鹽餅幹混合的味道。
他咽了咽嗓子,好想把鼻尖上去輕輕地嗅,慢慢地吻……
撲通——
撲通——
他的心鼓脹、跳,像一尾離水蹦跶的魚。
周景儀也覺得頭發礙事,一歪腦袋將長發捋至一邊。
綢緞質地的發從他手心流淌過,冰冰涼涼。期間,的手指短暫地到了他的手背,又小鹿般跳走了。
沒有了發的遮蔽,潔白漂亮的後背//在空氣中,那對纖細漂亮的蝴蝶骨讓看上去更像天使了。
他不敢多看,覺得那是對聖潔的。
手指小心翼翼避開的背部皮,往下尋找紐扣。
周景儀邊等他扣扣子,邊碎碎念:“一會兒,我一定要讓那個髒辮小鬼喊我一聲姑,竟然敢說我是日本人,真的要把我氣死了……”
Advertisement
謝津渡不是故意不搭話,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那兩粒紐扣霸占了。
因為過度張,他指尖在發抖,手心在出汗。
周景儀沒在說話,忽明忽暗的燈在後背上跳。
好漂亮,好想……
他被心底的惡魔驅使著,又被那跳的蠱,指尖一點點靠近……
一下,只一下,他對自己說。
指腹在脊柱上短暫地輕點過後,迅速移開。
周景儀也覺到了,熱的,一即離,像是某種的吸盤,引得一陣栗。
他應該是不小心到的吧,想。
“弄好了。”謝津渡把手從後背上移開。
“服幫我拿著,我一會兒還要穿。”周景儀沖後囑咐完,快步出了盥洗間。
四周奇靜無比,頭頂的燈一閃一閃地跳著,他抱過那堆換下來的服,呆愣愣地立在那裏。
這些東西上沾滿了的溫和氣息,是那種讓他陶醉到暈厥的味道。
他萌生出某種錯覺,仿佛懷中抱著的是……
胳膊不自覺地收,鼻尖上去細嗅,想將這些記錄進。
人群突然尖起來——
比剛剛更吵。
他想起周景儀還在外面,忙抱著服追出去。
他的天使已經站到了聚燈下,肩薄腰細,發飛揚發著,沒有刻意的濃妝豔抹,但就是很鎮得住場子。
有人送了把吉他上去,道了聲謝,抱進懷裏,幾下調好了音。
周景儀是今天晚上唯一一個上去板挑戰的孩,又是亞洲面孔,雖不明實力,但勇氣可佳,加上臉蛋兒漂亮,引來無數人加油打氣。
臨時主持進來說話:“比賽共三局決勝負,我們有三種不同的比賽方式,由你們自由選擇順序。”
髒辮男朝做了個請的手勢:“士優先,你來選第一局。”
周景儀輕蔑一笑,朝他擡了擡下,用流暢的英文說:“還是你先選吧,弱者優先。”
髒辮男覺得不過是在虛張聲勢。
這種人他見得多了,最後都是他的手下敗將。
他選了最拿手的對戰方式——倒放複刻。
主持人稍作解釋,觀衆席隨機找人倒放一首曲子,誰先用吉他複刻出原聲,誰就贏。
周景儀點點頭,表示已經清楚規則。
吵鬧的人群安靜下來。
音響裏叮叮當當響起一段旋律,倒放開始了。
周景儀閉眼聽了不到5秒鐘,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腳趾打著節拍,原地起調,指尖在琴弦上由慢到快撥,在周跳、搖曳。
悉的前奏響過一陣後,選曲人跳起來起來大喊:“天啊,難以置信,就是它,就是它。”
接著,人群興地起來——
周景儀對比毫無波瀾。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指尖撥彈,和吉他的旋律融為一,被照亮,或者就是本。
所有人都被那曲子裏的憂傷緒染到,目齊刷刷聚焦在上。
濃烈的緒直至高戛然而止——
的手指短暫地離開吉他,朝臺下卷手示意。
霎時間,所有人跟著旋律一起高唱起來:“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alright. Baby, you're harder to see than most…”
謝津渡的目被牢牢吸引,磁石一般追著跑。
周景儀注意到了他,卻沒有給予任何回應。
直到那句,“How do I love,how do I love againHow do I trust,how do I trust again”時,朝隔著人群他投來一瞥。
謝津渡鼻頭泛酸,眼眶驟然變得熱,直至哽咽。
好在,沒再看他。
最後一個音符彈完,周景儀輕拍吉他,利落收音。
鼓掌、歡笑聲、哄鬧聲織在一起。
這一刻,酒吧裏的熱鬧氣氛到達了頂峰。
唯一覺不妙的是髒辮男。
迄今為止,他沒有在這個項目上輸過。
“第二局我們比即興原創複刻吧。”他說。
觀衆席裏有人站出來噓他:“現在到這位士選比賽方式了。”
髒辮男扭頭,故意激將周景儀:“你要是不敢比這個,我們就換別的。”
不敢比?呵,笑話,從三歲開始玩吉他 ,還從沒怕過。
周景儀有些煩躁,撥了撥長發,看向他的眼神有點冷:“就比這個,你即興,我複刻,這樣更快。”
即興原創複刻,為一方即興演奏,另一方現場複刻,複刻方原封不地再現演奏就算贏。
由于演奏方的曲目是現場臨時創作,複刻方不僅要擁有絕對音準,還要有超強的記憶力。
髒辮男手一揮,讓人送來了電子琴。
周景儀從鼻子逸出一聲輕笑,這家夥還聰明,知道用電子琴來增加難度。
一個樂隊不可能集齊所有的樂手,電子琴可以據需要切換不同的樂聲,恰到好地彌補了這種缺陷。
厲害的鍵盤手,甚至可以做到一個人就是一支樂隊。
髒辮男調音過後,人群自安靜下來。
吉他起調後不久,他一會兒吉他,一會鍵盤,來回切換演奏,行雲流水。
這麽流暢的作,本不像是即興發揮,更像是提前寫好的譜。
有行人聽完,搖搖頭嘆:“這麽難的調子,就是對著譜子,也得要一個晚上才能記住。”
謝津渡有些擔憂地向周景儀——
聚燈下的孩坐在椅子上,遠比他想象的從容,抱著吉他,目沉靜,姿態放松,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打著節拍。
幾分鐘後,髒辮男結束了演奏
周景儀不不慢地走到電子琴前。
有人下意識屏住了呼吸。
同樣的吉他起調,同樣的一會兒吉他,一會兒鍵盤,作練,沒有毫猶豫,跟著節拍輕輕搖擺。全程不像是在和人對戰,倒是像在音樂本。
更加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竟然一個音也沒彈錯!
髒辮男的臉,由白轉紅再轉青,輸贏已定局。
周景儀把借來的吉他還回去,信步走到髒辮男面前。
“抱歉,你的獎金就歸我了。記住,下次別再把中國人認日本人。”
髒辮男下頜繃,臉部劇烈扭曲,鼻孔張大一掀一掀地往外吐著氣,眼睛憎惡地看向。還沒有人敢搶這麽搶的錢,那是他的錢!
“去死吧,臭人!”他舉起手裏的吉他狠狠砸過來——
謝津渡是第一個察覺到不對勁的。
他本能沖上前,一把將周景儀護在懷裏。
沖著腦袋擊打過來的吉他,落到了他後背上。
砰——
很重的聲響,電吉他霎時間分離斷了兩節。
滿座嘩然。
髒辮男見沒打到,還二次行兇,謝津渡微側過,握住對方手臂,用力往回一扭——
咔咔兩聲,仿佛有什麽清脆地斷裂了。
髒辮男抱著胳膊,撕心裂肺地哀嚎。
謝津渡將周景儀摟至一邊,抖開手裏的外套將包裹進去,了的額頭,溫聲征詢:“不玩了,回去好嗎?”
嚇得不輕,靠在他口,小啄米似的點著頭。
他不再管酒吧裏的事,抱起,大步往外走。
有人追上來問:“獎金你們不要了嗎?”
那可是七萬多英鎊,折合人民幣七十多萬,多人今晚來這裏都是為了錢。
謝津渡略停下腳步,朝後說:“留著請大家喝酒吧。”
周景儀的司機一早便在樓下候著了,見二人出來,忙把車開了過來。
後座車門打開,亮著一道暖橙的。
雨停了,風很烈,馬路上亮著無數金的小水窪。
謝津渡作輕地將放到座椅裏,扭走——
周景儀一把拽住他的手腕,聲音滴滴的:“你就這麽走啦?不送我嗎?”
他當然想送,可是……
“不許走,你得送我回去才行。”命令道。
“好。”
去酒店的路上,酒勁兒上頭,在他懷裏找了個姿勢靠著假寐。
他們一塊兒長大,賴他懷裏睡覺的次數,沒有五百回也有三百回。
謝津渡還是會張,手指僵地蜷在一起,好想抱……
聖誕節快到了,倫敦街頭的燈飾裝扮煥然一新,霓虹燈洩進來,眼皮掀開一道,瞥見他收未收的手臂。
“想抱就抱!”看穿了他的心思,直白提醒。
“我沒……”
謝津渡話說一半卡住了——
周景儀拉過他的手環上來,“這樣抱,我教你。”
僵手臂下來,他輕輕環住的肩膀,沒敢再。
“你後背怎麽樣?”問。
“不疼。”他答。
不信,坐起來,眼睛瞇一條線,目攫住他,問:“真不疼?”
他不想讓擔心,故意避重就輕,轉移話題:“你沒穿冷不冷?”
“當然冷啊,”噘著,不忘調戲他,“你再摟點兒。”
“……”
謝津渡越是藏著掖著,就越想一探究竟。剛剛髒辮男砸他的那一下,吉他都斷了,他背上傷得肯定不輕。
既然問了不肯說,那就只能直接看了。
可是天生的行派!
到了酒店門口,二人下車,周景儀親昵的環住他的胳膊,說:“走吧,跟我去樓上。”
“太晚了,還是……還是……”
“難道你要穿這樣回去?”指了指他大的領口,那裏沒有遮蔽,線條清晰可見。
“……”
“你這也太暴了。”
“……”
“萬一遇上變態怎麽辦?”
“……”
周景儀沒給他拒絕的機會,一把將他拉進了電梯間。
兩分鐘後,合上房門,踢掉高跟鞋,朝他擡了擡下說:“好啦,現在沒人了,把服掉吧。”
謝津渡沒。
走近幾步,將他摁坐在床上,居高臨下地著他,“自己還是我幫你?”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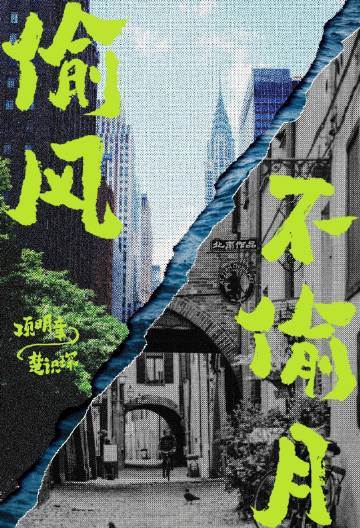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170 章

離婚后,秦少夜夜誘哄求復合
薄棠有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她暗戀了秦硯初八年。得知自己能嫁給他時,薄棠還以為自己會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直到,他的情人發來一張照片秦硯初出軌了。 薄棠再也無法欺騙自己,秦硯初不愛她。 他身邊有小情人,心底有不可觸碰的白月光,而她們統統都比她珍貴。 恍然醒悟的薄棠懷著身孕,決然丟下一封離婚協議書。 “秦硯初,恭喜你自由了,以后你想愛就愛誰,恕我不再奉陪!” 男人卻開始對她死纏爛打,深情挽留,“棠棠,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她給了,下場是她差點在雪地里流產身亡,秦硯初卻抱著白月光轉身離開。 薄棠的心終于死了,死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天。
30.6萬字8 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