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離婚!換親后,八零糙漢夜夜寵》 第24章 小桃
夏冬沐搭上最后一班車抵達鎮上。
找了戶人家,拿東西給人家抵押換得一支手電筒。
就這麼舉著微末的亮往村里去。
黃泥大路走完就是一段窄小的路段。
是從鎮上進村的必經之路,周圍黑漆漆,還有蟬鳴聲。
著布包寬帶,腳步加快了些。
忽然,一陣窸窸窣窣。
沒管,正要往前,一個黑影驀然跳出來。
手電筒下意識照過去,是陳。
夏冬沐在村里沒遇見他,每次撞見,他都用一副晦又惡心的眼神盯著瞧。
他怎麼知道還沒回去?
“夏同志,從城里回來?”
夏冬沐不聲的暗暗后退,上應付著,往一旁準備繞過去。
“嗯,陳大叔,你去哪?”
“我?”陳像是看戲似的盯著夏冬沐慢慢的往旁挪。
“我當然是在等你。”
話落,他一撲,將夏冬沐撲倒在地。
聲聲迫不及待的惡笑從陳的里發出。
“夏同志,你不知道我好想你,你給我當媳婦吧,我保證我比蕭管理更對你好!”
“放開我!”
陳迫不及待的撕扯夏冬沐的長。
夏天布料,很快的的領口就被拉扯下來,出圓潤的肩頭。
陳呼吸加,俯首在上面弄。
夏冬沐胃里的惡心一陣陣往上涌。
仿佛又回到了福利院,同樣是黑漆漆的環境,同樣的氣息。
Advertisement
年的怎能反抗人的力量,當時得空就尖,不停地尖加掙扎。
夏冬沐瞪著雙眼,死命大吼:“就命啊!就命啊!”
雙手不停地撲騰,陳要限制的手不是,捂的也不是。
氣惱下,啪——
一掌重重扇在夏冬沐的側臉。
掙扎的作微頓,就這個間隙,陳把的往下撕。
雪白的在夜里發。
陳看的心臟狂跳。
意識到夏冬沐的安靜,他開心的俯首品嘗味。
然而,他剛彎腰,一道重擊砸在他的頭顱頂。
陳愣了。
夏冬沐猛地推開他,丟下手中的石頭,來不及整理,轉就往坡上跑。
陳的腦袋有點暈,他站起來,眼前冒火星,他頭再拿開,有點黏糊糊。
著跑遠的影,陳抬腳想追,然而卻往后踉蹌好幾步。
砰——倒地。
夏冬沐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只能不停地奔跑,奔跑,再奔跑。
等筋疲力盡,環顧四周,好像是來到山林里。
腳一,撐著樹干緩緩坐在地面。
凌不堪的子被忽視。
驀地,還沒休息兩分鐘,前方傳來快速的腳步聲。
撐著樹干忙站起來,影越來越近,下意識的躲在樹干后。
影錯跑了三步卻停住。
夏冬沐的呼吸提高,警惕的盯著前方。
影往回走,夏冬沐暗暗的往后退,月下,一切顯得那麼寂靜。
“lunar!”這是驚喜的聲音。
夏冬沐愣然,“小,小……”
話沒說完,頭重腳輕的暈過去。
……
蕭折勛十點回村,把三車停放在養豬廠后就返回。
陳立業和他一起,兩人走到村尾遇到陳珍珍。
陳立業皺眉,“珍珍?你怎麼還在這,這麼晚了。”
陳珍珍下意識的看向蕭折勛,小聲的說:“我等你。”
“等我干什麼,我又不是不識路。”陳立業嘟囔。
蕭折勛沒管他們兄妹倆,直接大步走在前。
等他推開院門,發現周圍黑漆漆。
應該睡了吧,他想。
他沒打擾房間里的人,自顧去淋浴室洗漱,卻發現里面很干,不像使用過的模樣。
夏冬沐的他了解,每晚回來肯定要洗漱。
想到什麼,蕭折勛大步去敲門,然后里面沒有靜。
恰這時,江萬起夜出來,“勛哥,你回來了。”
“江萬,你有看到冬沐回來嗎?”
提起這事,江萬清醒了兩分,“沒有啊,從養豬廠回來后,沒看到你家有人。”
蕭折勛的眉眼一沉,大力踢開木門,打開燈。
一切空!
馬不停蹄的,他去村委辦事房間打電話,他沒打到機廠里,而是打到呂建國的住。
“夏同志?我走的時候讓子安那小子送回去了呀。”
蕭折勛的下頜微繃,“呂叔,麻煩你幫我找一下周子安,就現在,此刻!”
他覺心里有點慌,但不知這慌從哪來。
“好好。”呂建國忙下床。
這麼晚了,希夏冬沐不要出什麼事!
大概三分鐘,蕭折勛和周子安通上電話,得知夏冬沐離開時是七點,蕭折勛啪的一聲掛了電話。
他返回養豬廠,開著三車沖向鎮上。
江萬見他風風火火,沒來得及出聲,就著他離去。
三車的燈比較亮,路過那小截路段,悉的布包映蕭折勛的眼底。
他下車大步過去,眼眸一掃。
皺的布包、亮著微弱線的手電筒、躺著不省人事的陳……
蕭折勛的眼神越發黑邃。
**
夏冬沐醒來的時候,周圍的很陌生。
靜靜的等待著,等待腦海里的記憶回歸平靜。
以為自己又穿越了。
“lunar,你醒來了,來,喝點米粥。”
歪頭一看,是梳著兩個麻花辮的圓潤娃娃臉,皮白皙,服時髦,一點不像這個時代的人。
“小桃?”
“看到我很驚訝吧,我為了找你跑不地方。”
夏冬沐支起,小桃忙過來攙著。
“你是怎麼來的?”
“你喝點米粥,我慢慢告訴你。”
小桃也姓夏,是后世跟夏冬沐說也是孤兒,不如讓跟著姓夏。
這種事沒什麼大不了,夏冬沐就答應了。
兩人還上了同一個戶口本
夏冬沐在后世莫名穿了后,小桃端茶進辦公室發現怎麼都不醒。
轉出去人,卻半路撞到桌角往地上一摔,再醒來就是不同的時代。
初來的地方是在山腳下的山村道路上,不知道怎麼辦,就邊問路,邊走到鎮上。
后來,憑著后世的本領在鎮上找了一份工作,也沒放棄尋找夏冬沐的消息。
說沒緣吧,抵達的鎮上就是夏冬沐經常去的鎮上。
說有緣吧,們一次也沒見,小桃也沒在鎮上打聽到夏冬沐的消息。
偏偏這次,下工回去的晚,到夏冬沐借手電筒那戶人家的兒子在讀夏冬沐寫給他們的保證紙條。
剛好讓聽到對方說:“借款人:夏冬沐。”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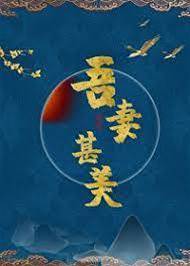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353 章

東宮禁寵
沈江姩在宋煜最落魄之日棄他而去,改嫁為周家婦,一時風光無限。宋煜復寵重坐東宮主位,用潑天的權勢親手查抄沈江姩滿門。為救家族,沈江姩承歡東宮,成了宋煜身下不見天日任他擺布的暖床婢在那個她被他據為己有的夜里,下頜被男人挑起,“周夫人想過孤王有出來的一天麼?”
79.1萬字8.18 13704 -
完結221 章

太子侍妾
【雙潔?謀權?成長】 沁婉被倒賣多次,天生短命,意外成為九皇子侍婢,因為出生不好,一直沒有名份。九皇子金枝玉葉,卻生性薄情,有一日,旁人問起他的侍俾何如。 他說:“她身份低微,不可能給她名份。” 沁婉一直銘記於心。又一日,旁人又問他侍婢何如。 他說:“她伺候得妥當,可以做個通房。” 沁婉依舊銘記於心。再有一日,旁人再問他的通房何如。 他說:“她是我心中所向,我想給她太子妃之位。” 沁婉這次沒記在心裏,因為她不願了。......後來,聽說涼薄寡性,英勇蓋世的九皇子,如今的東宮太子 卻跪在侍婢的腳下苦苦哀求。願用鳳印換取沁婉的疼愛,隻求相守一生。她沁婉哭過,怨過,狠過,嚐過生離死別,生不如死,體驗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是沒醜過!後來,她隻想要寶馬香車,卻有一個人不僅給了她寶馬香車,連人帶著花團錦簇都給了她。
40.6萬字8.18 9261 -
完結503 章

離婚后才知道前夫的白月光竟是我
溫軟和祁宴結婚三年,用盡努力都沒能暖了祁宴的心。她以為那人天生涼薄,無心于情愛,便一心守著豪門太太的身份過日子。直到群里發來祁宴和白月光的合照,溫軟才知道他不是沒有心,只是他的心早就給了別人。 握不住的沙不如揚了它,留不住的男人干脆踹了他,溫軟當晚便收拾好行李,丟下一直離婚協議離開了家。 離婚后,溫軟逛酒吧點男模開直播,把這輩子沒敢做的事全都瀟灑了一遍,怎料意外爆火,還成了全民甜妹,粉絲過億。 就在她下決心泡十個八個小奶狗時,前夫突然找上門,將她堵在墻角,低頭懲罰般的咬住她溫軟的唇,紅著眼睛哄,“狗屁的白月光,老子這輩子只愛過你一人。” “軟軟,玩夠了,我們回家了好不好~”
64.2萬字8 17299 -
完結187 章

甜爆!撿到陰郁大佬閃婚被寵瘋了
宋知暖在自家別墅外撿了個男人,貪圖對方的美色帶回了家,藏在自己的小閣樓上,等男人醒來,兇巴巴的威脅,“我救了你,你要以身相許報答我,報下你的身份證,我要包養你,每月給你這個數!” 霍北梟看著女孩白嫩的手掌,眉梢微挑,“五百萬,我答應了。” 宋知暖炸毛,“一個月五千,多一個子都沒有!” 宋知暖以為的霍北梟,一米八八八塊腹肌無家可歸,四處漂泊,需要自己救濟愛護的小可憐。 實際上的霍北梟,深城霍家太子爺,陰狠暴戾,精神病院三進三出的常客,無人敢招惹的存在,被小姑娘撿回家閃婚后,卻頻頻傳出妻管嚴的謠言,好友不信,遂做局帶太子爺在酒吧泡妹子。 不多時包廂的門被人踹開,闖進來一身穿白色長裙,純粹到極致的姑娘,姑娘只瞧了太子爺一眼,眼圈泛紅,唇瓣微抿,兔子似的。 眾人只見那位太子爺慌亂的摁滅手里的煙,走過去將姑娘圈懷里低頭親。姑娘偏頭躲了下,太子爺輕笑一聲,耐心的哄,“寶寶,罰我我當眾給你跪一個表真心好不好?”眾好友:卒。
35.2萬字8 1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