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萬福》 第11章 瘋婦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趙晢很早便教過。
想到趙晢,抿了抿的瓣,說來也可笑,口口聲聲不用趙晢管了,可今日用的這些法子,竟無一不是從他那學來的。
“姑娘,這才初春,夜里冷著呢。”糖糕小心翼翼的勸道“人既然在府里,姑娘實在不必急于一時……”
“姑娘,金瓜子只有這麼多了。”糖果捧著黑漆的壇子,將里頭的一小捧金瓜子盡數倒在了桌上,看向“要不然,等明日天亮了奴婢去二夫人那取吧?
左右,姑娘要去菩提寺,要用金子也尋常。”
李璨聞言,角微微挑了挑,眸之中滿是可笑與譏諷。
娘給留下的嫁妝,可不只有幾庫房的死,還有二十幾家鋪子,日日都在盈利。
這其中,以南門朱雀大街和東市子大街的兩家大當鋪生意尤勝,每日生意如火如荼,說是日進斗金也不為過。
自落地,便不曾為錢財犯過愁,逛集市自來是想買什麼便買什麼,賞賜下人也都是一把一把的金瓜子,帝京城許多店家都暗地里稱為“散財”。
賀氏在錢財上是不曾苛待過的。
眼下想來,都是的銀子,賀氏不過是拿的錢財充大方罷了,又何必小氣?
Advertisement
賀氏掌管著娘留給的那些鋪子,同的兩一兒四人的吃穿用度樣樣都是的。
若是換是賀氏,也會對自己好的,裝模作樣便能換得無數錢財,誰會不愿意裝?
怪只怪這些年眼盲心瞎,賀氏這母子四人哄的團團轉。
如今,要用錢財,竟還須得同賀氏開口,賀氏可真會反客為主。
這些年,要用金銀,賀氏雖從未回絕過,卻也在其中得了不激與戴。
想起過往,恨不能即刻便奪了賀氏的掌家之權,好他們母子四人再撈不到半分好。
“姑娘,不如奴婢先去看看是哪個小廝吧?”糖糕提議。
兩個婢都憂心忡忡的著。
“好。”李璨點頭了。
糖糕打著氣死風燈去了。
小半個時辰后,哈著寒氣回來了。
“如何?”李璨著問。
“是一個康子的,他有個妹妹,在咱們院子做灑掃,我已經同他說了。”糖糕哈著手回。
這一趟算是沒有白跑。
“走。”李璨沒有毫猶豫。
客院門前,材瘦小的小廝康子裹著被褥,蜷在門邊,凍的瑟瑟發抖。
頭頂上懸著一盞燈籠隨風晃,門環上穿著鐵鏈子,握在他手中。
他是賀氏院子跑的小廝,因著是后來才去的嘉禾院,旁的下人都排他,只能做這些苦哈哈的差事。
遠遠地,瞧見一行三人來了,他忙丟掉被褥,起行禮“見過七姑娘。”
李璨微微頷首。
“開門吧。”糖糕吩咐。
“是。”康子扯開了鐵鏈子,推開了門。
妹妹在鹿鳴院,他不能得罪七姑娘。
再說,里面那一位也不見得能說出什麼來。
糖果在門口守著,李璨帶著糖糕進了客院。
廊下,掛著一盞昏黃的燈籠,隨風輕輕搖晃,勉強照亮四周。
午夜靜悄悄的,屋子里一片黑暗,毫無聲息。
李璨甚至有一瞬間懷疑,這是不是賀氏給設的圈套。
“姑娘,你在這等著,奴婢去瞧瞧。”糖糕舉起手中的氣死風燈,行到門前,小聲
詢問“有人嗎?”
靜等了片刻,并無人回應。
“我推門進來了。”打了聲招呼,手中使力,門“吱呀”一聲開了。
“別殺我!別殺我,求求你們,不,不死……”
屋里傳出驚恐的聲,半夜聽來,尤為驚悚。
糖糕吃了一驚,連退數步。
李璨卻越過,進門去。
“姑娘,等奴婢先進去。”糖糕知道自家姑娘的子,勸是勸不住的了,絕不能姑娘以犯險。
李璨站住腳,安靜的等在原地。
糖糕將手中的氣死風燈遠遠的打在前面照亮,壯著膽子進門,點燃了屋里桌上大燭臺的蠟燭。
“嘿嘿嘿……”
墻角,怪異的笑聲傳來。
兩人齊齊向那。
一個蓬頭垢面衫襤褸的人蜷在墻角,正朝們咧笑著,臉上的污垢人瞧不清的長相,若不是口微微鼓起,甚至分不清是男是。
“嘿嘿嘿……死了……都死了……”
又一次笑了,缺了一顆門牙,使得說話也不甚清晰。
李璨端詳了片刻,抬步朝行了過去。
“姑娘,別去,這是個瘋子,會傷人的!”糖糕也下意識護在李璨跟前,警惕的著那個瘋婦。
“無妨。”李璨推開,緩步行了過去。
這只有一人,想來,這是娘邊留下來的唯一證人了。
賀氏如此謹慎,不信這婦人是真的瘋了。
“別殺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不要殺……不……不……”
那瘋婦害怕極了,在墻角瑟瑟發抖,眼淚將面上的灰塵沖出兩道淺淺的壑,看著可怖又可憐
。
“你別怕,你認得我嗎?”李璨蹲下看“我是白月的兒,我李璨。”
“別……別過來……”
那瘋婦兩手半擋在面前,一臉驚恐。
“你是我娘的婢對不對?你能告訴我娘當初到底是怎麼死的嗎?”李璨又問。
“不死……不能死……不死,不死……”那瘋婦更害怕,拼命往墻角。
“我想知道我娘的死因,你能告訴我嗎……”李璨又問了一句,漆黑的眸子中滿是失,這婦人看著不像是裝瘋賣傻,如此,到手的線索卻又斷了,這該從何查起?
心中又焦急又無措,不落下淚來。
“姑娘,走吧。”糖糕不忍心,上前扶起,也跟著抹了一把眼淚。
李璨不甘的回頭瞧了瞧,糖糕扶著,正要踏出門檻去。
“姑娘……”
便在此時,后那瘋婦忽然口齒清晰的喚了一聲。
李璨猛地轉過小腦袋,心中一陣激,三步并作兩步跑了回去,蹲到那婦人跟前,小臉上滿是急切與忐忑,小嗓音都有些抖了“你,你是裝的對不對?”
那婦人不說話,只用一雙略微渾濁的眼打量著。
李璨眸中藏著急切,卻蹲著不敢,也不敢再開口詢問,生怕再嚇著,到時候什麼也問不出。
打量了半晌,那婦人才再次開口“姑娘可否給我看看后背?”
“大膽!”糖果下意識的呵斥。
李璨推開糖果,問那婦人“你是想看我后背的痣嗎?”
那顆痣,其實并不算是在背上。
而是在的后脖頸之下,脊柱骨的最上端正中央,是一顆朱砂痣。
這痣生下來便有,這些年隨著長大而慢慢長大了些。
猜你喜歡
-
完結847 章

穿書後,我嬌養了反派攝政王
(章節內容嚴重缺失,請觀看另一本同名書籍)————————————————————————————————————————————————————————————————————————————————————————————————————棠鯉穿書了,穿成了炮灰女配,千金大小姐的身份被人頂替,還被賣給個山裏漢做媳婦,成了三個拖油瓶的後娘!卻不曾想,那山裏漢居然是書里心狠手辣的大反派!而那三個拖油瓶,也是未來的三個狠辣小反派,最終被凌遲處死、五馬分屍,下場一個賽一個凄慘!結局凄慘的三個小反派,此時還是三個小萌娃,三觀還沒歪,三聲「娘親」一下讓棠鯉心軟了。棠鯉想要改變反派們的命運。於是,相夫養娃,做生意掙錢,棠鯉帶着反派們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後來,三個小反派長大了。一個是位高權重當朝首輔,一個是富可敵國的大奸商,一個是威風凜凜的女將軍,三個都護她護得緊!當朝首輔:敢欺負我娘?關進大牢!女將軍:大哥,剁掉簡單點!大奸商:三妹,給你遞刀!某個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則直接把媳婦摟進懷。「老子媳婦老子護著,小崽子們都靠邊去!」
145.2萬字8.33 120041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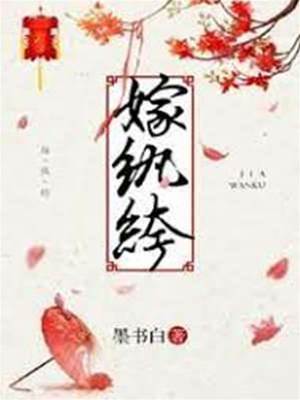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012 章

戰神王爺是妻奴
一朝穿成被人迫害的相府癡傻四小姐。 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隨身攜帶醫藥實驗室和武器庫。 對于極品渣渣她不屑的冷哼一聲,迂腐的老古董,宅斗,宮斗算什麼? 任你詭計多端,打上一針還不得乖乖躺平! 絕世神功算什麼?再牛叉還不是一槍倒! 他,功高蓋世,威震天下的戰神王爺。 “嫁給本王,本王罩著你,這天下借你八條腿橫著走。” “你說話要講良心,到底是你罩我,還是我罩你呀?” “愛妃所言極是,求罩本王。” 眾人絕倒,王爺你的臉呢?
362.3萬字8 38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