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吻》 第9章 第九章
車廂霎時間靜了下來,意識到陸遇安心非常一般,陳凈揚不敢造次。
但他想了想,自己除了讓他去警局給自己簽字之外,也沒干什麼特別過分的事吧。他不是第一次去警局接自己,不可能是因為這個事而心不好。
琢磨半晌,陳凈揚想到了原因。
“哥。”他扭頭瞅著陸遇安,“你不會是在吃醋吧?”
車駛地下停車場,線由昏暗到明亮過度。
聽到陳凈揚的話,陸遇安臉上沒一變化,甚至連個眼神都沒給他。
陳凈揚看他聲不的模樣,對自己的直覺產生了丁點懷疑。
他猜錯了?
不應該啊,他這方面的直覺很出錯。
車停好,陸遇安才掀起眼皮看他,“下車。”
陳凈揚:“……哦。”
跟著陸遇安進了屋,陳凈揚按捺不住,繼續剛剛的話題,“你不是吃醋的話,你干嗎讓我閉?”
陸遇安沒理他,轉進了廚房。
陳凈揚跟進去,不停,“還是說你討厭阮螢姐?”沒等陸遇安吭聲,他又自言自語,“這更不應該,你要是討厭一個人,你連個眼神都不會給人家,怎麼可能還和一起吃宵夜。”
這麼多年,陳凈揚自認還算了解他這個表哥。
他比陸遇安小九歲,因為父母生意忙的緣故,小學初中大多時間,都住陸遇安家里。
陸遇安高中以前不孩子歡迎,陳凈揚不清楚,他那會太小。但陸遇安上高中之后,他常常能在小區,陸遇安學校見向他表白,送禮,請吃飯的孩。
在他記憶中,陸遇安好像從來都是拒絕。
他皮相雖好,卻和異絕緣。
為此,陳凈揚的姑姑頭疼過很多回。常常和陳凈揚念叨,擔心陸遇安這輩子都沒人要。
Advertisement
陳凈揚想著,注意到陸遇安在倒水。
他口干舌燥,眼疾手快把他倒好的水搶走,咕嚕咕嚕喝下。
“……”
陸遇安沒和他計較,重新拿了個杯子。
這回,陳凈揚沒敢再搶。
等陸遇安喝完水,他才再次出聲,“哥,你說句話唄。”
“說什麼?”陸遇安明知故問。
陳凈揚無語,“你剛剛為什麼讓我安靜點。”
“你太吵。”陸遇安實話實說。
這個回答,讓陳凈揚無力反駁。
他默了默,“除了這個原因,就沒別的了?”
陸遇安瞥他,“你還想要什麼別的?”
“你是不是——”話說一半,陳凈揚頓住,他覺得自己要是問陸遇安是不是對阮螢有意思,他肯定不會告訴自己,甚至不會搭理他。思及此,他換了個問話,“阮螢姐是不是對你有意思?”
晚上在燒烤攤他雖沒覺出兩人對對方有太明顯的意思,但一起聊天的時候,他覺得他們的氣場過分契合。
讓他不得不多想。
聽到陳凈揚這話,陸遇安靜默一會,“陳凈揚。”
陳凈揚激應聲,期待他的回答。
陸遇安抬腳往外走,走到書房門口,他偏頭他,“再吵,今晚回你自己家睡。”
“?”
陳凈揚一愣,還沒反應過來,陸遇安把門甩上,把他隔絕在外。
對著閉的門好一會,陳凈揚在要個答案和被趕出門之間衡量須臾,選擇了后者。
他很清楚的知道,陸遇安是個說到做到的人。
-
另一邊,阮螢到家后不久,接到了崔治電話。
他剛出完任務回局里,看到阮螢留給自己的蛋糕和字條。要不是阮螢帶蛋糕過去,他都忘了今天是自己生日。
阮螢沉默了會,輕聲道:“崔叔叔,生日快樂,您多注意。”
崔治笑笑,“好,今天太忙了。等崔叔叔過幾天休息,你也有空,崔叔叔請你吃飯。”
阮螢說好。
崔治又叮囑幾句,讓也注意,有什麼事給他打電話,到警局找他都行。
他大多數時間,都在局里。
掛了電話,阮螢在沙發上呆坐許久,才慢吞吞起去浴室洗漱。
不確定是不是崔治那通電話的緣故,這一晚的阮螢做了很多個夢。七八糟的,讓一夜沒睡好。
-
周一上午,阮螢早早出現在醫院。
和預想的差不太多,星期一的醫院,比其他幾天工作日人多很多。
檢查結束后,阮螢去醫院門口逛了一圈,買了點東西,才折返去住院部看琪琪。
明天就回電臺上班,想趁著最后一天假期,多陪陪。
和門診那邊差不多,工作日的住院部,也很忙很忙。
看到出現,悉的幾位護士和打了聲招呼,告訴琪琪在房間,便火急火燎忙去了。
阮螢到的時候,琪琪在吊水。
還沒出聲,就驚喜地抬起頭,準確無誤地對準站的位置,“阮姐姐,是你來了嗎?”
阮螢驚訝不已,“你怎麼知道是我?”
今天過來,沒有提前跟琪琪說。
琪琪粲然一笑,等坐下后才說,“你上有好聞的味道,我分得出。”
阮螢忍俊不,“我們琪琪的鼻子怎麼這麼靈。”
被一夸,琪琪還有點小驕傲,“陸哥哥也說我鼻子靈,他每次一進病房,我就知道是他。”
阮螢揚了揚眉,“那你能不能跟姐姐說說,我們倆上味道的區別。”
琪琪點頭,歪著頭思考了好一會,“陸哥哥上是糖果的味道,酸酸甜甜的。”
阮螢被的形容逗笑,大概懂了形容和陸遇安上味道的依據在哪。
“那姐姐呢?”追問。
琪琪沉默許久,臉朝著阮螢這邊說,“是溫暖,有點像以前媽媽上的味道。”
阮螢愣住。
原本以為,琪琪會像形容陸遇安一樣,用買過的蛋糕,亦或者是上次過來送給的巧克力來形容。
完全沒有想到,會把溫暖這個帶著意的詞,送給自己。
察覺到阮螢的默然,琪琪有點著急,“阮姐姐,你怎麼不說話了?是不是琪琪說錯了?”
“……不是。”阮螢回神,握著沒有扎針的那只手,“姐姐就是有點意外,琪琪形容我們形容的太好了,這幾天是不是有好好聽書?”
上回來就知道,陸遇安送了一個聽書機給,里面有很多適合這個年齡小孩聽的書,很有趣。
琪琪點頭,“有的,前天陸哥哥還給我念了故事書。”
聞聲,阮螢腦海里浮現出畫面。
陸遇安穿著白大褂,英姿筆坐在病床旁,捧著一本彩富的故事書給琪琪講的畫面。
他平時說話聲線音調就很好聽,講起故事,有代,應該會更特別,更有味道。
一時間,阮螢有些羨慕琪琪。
也想聽陸遇安講故事,想聽他的聲音。不知道他下回給琪琪講故事的時候,能不能來“蹭堂課”。
陪琪琪聊了會天,阮螢也依葫蘆畫瓢,翻開陸遇安念過的故事書,給念了另一篇話故事。
在醫院待了好幾個小時,阮螢也沒見著陸遇安。
估著陸遇安應該是在手室。
正打算走,阮螢到能口氣休息的于惜玉,“于護士。”
于惜玉看,笑盈盈模樣:“阮小姐,要走了嗎?”
阮螢點頭,忽然想起來,“于護士,我想問你個事。”
于惜玉:“你說。”
阮螢出院的時候,于惜玉不在上班時間。把香薰給其他護士,讓對方幫忙還給后,就一直忘了問香薰在哪買的。
今天巧合適,阮螢便直接問了,“上次我失眠,你借給我安神助眠的香薰在哪買的?方便給我個鏈接或地址嗎?”
于惜玉一愣,“什麼香薰?”
阮螢眨眼,“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小瓷罐,我出院前一天晚上你給我的。”
于惜玉回憶,“陸醫生回來的那天?”
阮螢:“對。”
“那不是我的。”于惜玉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跟阮螢解釋,“那個東西是陸醫生的。”
告訴阮螢,那天送回病房后,陸遇安就向于惜玉了解了阮螢況。
知道一直失眠后,就從辦公室拿了那罐香薰出來,讓放阮螢床頭幫助安神眠。
說完,于惜玉看,“你需要的話,可以問問陸醫生。”
阮螢緩慢眨了下眼,朝確認,“那罐香薰,是陸醫生讓你給我的?”
于惜玉:“對呀。”
阮螢怔了怔,朝目疑的于惜玉彎了下,“好,我知道了,謝謝你于護士。”
于惜玉莞爾,“阮小姐客氣啦。”
和于惜玉聊了兩句,阮螢離開醫院。
-
周一手排的比較多,有一臺比較復雜。
等陸遇安忙完有空對付一下胃時,畢凱旋湊了過來。
“陸醫生。”
陸遇安看他,“今晚替你值班?”
“不是。”畢凱旋一哽,“我是這種人?”
陸遇安挑了下眉,看破不說破。
畢凱旋訕訕,自覺道:“短時間,我應該是不需要你幫我值班了。”
這話過于悉,陸遇安淡然道,“又失了?”
又這個字的微妙之,就在于,它是“又”。
畢凱旋是眼科部的達人,談的朋友沒有十個也有八個。可惜的是,每一個都好景不長。
不過他并沒有因為失過于頻繁而氣餒,在這條路上,畢凱旋抱著和他名字一樣的信念,期待“凱旋而歸”。
安靜了會,畢凱旋嘀咕,“你說人心,海底針是不是?我不過就是在夸那家人均三千的餐廳廚師刀工好時,人均價值的時候說了句我刀工比那廚師更好,就罵我惡心,說我吃飯聊讓反胃的事。”
他很是不明白,“我刀工好,怎麼就是一件讓反胃的事了?”
陸遇安:“……”
畢凱旋覷著他,“你怎麼不說話?”
陸遇安:“無話可說。”
畢凱旋睇他一眼,“算了,反正我就是告訴你我又失了,你最近有值班可以給我。”
頃,陸遇安吃的差不多,“你今天是不是有病人復查?”
“有啊。”畢凱旋說,“怎麼?”
陸遇安:“恢復的怎麼樣?”
畢凱旋正想回答,忽而眼珠子一轉,故意問:“誰恢復的怎麼樣?我今天有好幾個病人來復查。”
陸遇安抬眼,神自若,“我問阮螢。”
他這麼坦,畢凱旋反倒不知道說點什麼了。他哽了哽,把阮螢況托盤而出,“好的,手后還有點痕跡,我讓去拿支藥膏,涂完痕跡應該能消的差不多。”
說話間,他灼灼注視陸遇安,“你和什麼關系?”
陸遇安吃完飯,淡淡掃他一眼,“沒什麼關系。”
畢凱旋:“……沒什麼關系你特意問我。”他吐槽,“我才不信。”
陸遇安起準備回辦公室,語氣寡淡,“不信還問。”
畢凱旋:“???”
回到辦公室,陸遇安準備休息會,畢凱旋對著他桌上憑空出來的果籃驚訝,“這誰送給你的,不怕你被醫院抓典型?”
陸遇安抬眸去看,還沒來得及開口,畢凱旋拿起果籃里附上的一張卡片打開,看到一個悉的名字。
“阮螢?”他詫異,“阮螢為什麼給你送果籃?”
畢凱旋茫然,“是不是送錯人了,我是的主刀醫生,這果籃應該送給我的才對。”
于惜玉恰好進來有事,聞聲說,“沒送錯,阮小姐說送給陸醫生。”
畢凱旋噎了噎,耍賴道,“那我不管,我要一起吃。”
“可以。”陸遇安把卡片從他手中走,低眼去看,字是阮螢自己寫的,依舊娟秀有力,溫淡雅。
看了會,陸遇安從手機翻出半個月前撥出的那個號碼,再次撥通。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狙擊蝴蝶
李霧高考結束后,岑矜去他寢室幫忙收拾行李。 如果不是無意打開他抽屜,她都不知道自己曾丟失過一張兩寸照片。 - 所謂狙擊,就是埋伏在隱蔽處伺機襲擊。 ——在擁有與她共同醒來的清晨前,他曾忍受過隱秘而漫長的午夜。 破繭成蝶離異女與成長型窮少年的故事 男主是女主資助的貧困生/姐弟戀,年齡差大
27.7萬字8 8157 -
完結521 章

錯惹惡魔總裁
洞房對象竟不是新郎,這屈辱的新婚夜,還被拍成視頻上了頭條?!那男人,費盡心思讓她不堪……更甚,強拿她當個長期私寵,享受她的哀哭求饒!難道她這愛戀要注定以血收場?NO,NO!單憑那次窺視,她足以將這惡魔馴成隻溫順的綿羊。
141.7萬字8 14730 -
完結169 章

盛寵之權少放過我
她千不該萬不該就是楚秦的未婚妻,才會招惹到那個令人躲避不及的榮璟。從而引發一系列打擊報復到最后被她吃的死死的故事。
45.5萬字8 11480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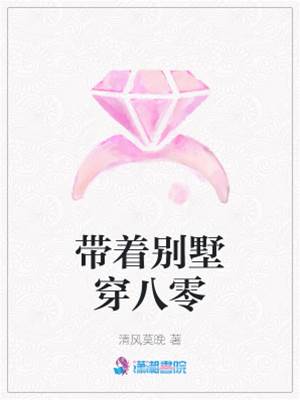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94 章

千億前妻帶崽歸來,馬甲藏不住了
江司妤和薄時宴協議結婚,做夠99次就離婚。 在最后一次情到深處的時候,江司妤想給男人生個孩子,不料男人記著次數,直接拿出離婚協議書。 江司妤愣住,回想結婚這三年,她對他百依百順,卻還是融化不了他這顆寒冰。 好,反正也享受過了,離就離。 男人上了年紀身體可就不行了,留給白月光也不是不行! 江司妤選擇凈身出戶,直接消失不見。 五年后,她帶崽霸氣歸來,馬甲掉了一地,男人將人堵在床上,“薄家十代單傳,謝謝老婆贈與我的龍鳳胎..”江司好不太理解,薄總這是幾個意思呢?
72.4萬字8 5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