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成流放反派他元配》 第5章 第五章
“什麼你的?這是我的裳!”張春芬頓時跟被踩了尾的耗子似的跳起來,“葉嘉你莫不是窮瘋了?周家的日子就那麼苦,你見著什麼好東西就都是你的?”
張春芬可不是個好相與的。能干得出寄居在葉家還使喚人家姑娘的事兒,哪有什麼廉恥?
兩手往口一擋,扭頭就想進屋。
葉嘉攔到跟前,手將那裳往面前一扯,似笑非笑。其實,哪里曉得原主有哪些裳?本不過隨口一詐,張春芬一副做賊心虛的樣子反倒確定了。
這裳是黃的綢面兒襖子,瞧澤也鮮亮。一看就知不是李北鎮本地賣的。若是外人送,也不能送這麼不合不是?瞧這姑娘袖子短一截,擺也只到腳踝上頭。葉嘉笑了聲道:“拿人東西也不怕被正主瞧見!”
張春芬自然是不認。
葉嘉點點頭道:“那行,改天我問問那人。我到看看,是不是有人賣我名頭在拿好!”
張春芬臉頓時刷白,一手下意識地著耳鐺。做賊心虛也沒這麼明顯的。
葉嘉的眼睛瞇了起來。
葉張氏自然護著妹妹,幫腔道:“嘉娘,這裳真是春芬自個兒從外頭抱回來的。出嫁那日你都把柜子捎帶走,哪兒還有裳落家里?嫂子曉得你日子不好過,但也不能張口就指人是賊。哪有這麼說話的?再說,春芬也要說親了,相看的人能排到村外頭去。自是有人上趕著送好東西……”
有葉張氏幫腔,張春芬一口咬定就是別人送的。葉嘉都聽樂了。這張氏姐妹可真有意思。求人做事,偏還要人一頭。要好名聲還便宜一樣不能落,哪有這麼好的事兒?
“行,”點點頭,葉嘉也不跟扯這些。這次是被葉張氏求回來的,“既然有了好歸宿,嫂子盡管替張羅就是。我便不湊熱鬧了。家里還有人傷著起不來,我這就走了。”
Advertisement
葉張氏臉當即一變,反應過來就要攔。
護妹護慣了。往日在家就是這麼護著的,也沒人說什麼。倒是忘了葉嘉跟這家子人不一樣,氣大得很。拉拉扯扯的,正好幾個男人從門口進來。
為首的是葉老爺子和葉家莊的村長,后跟著幾個都是鄉老。
在葉家莊這窮山里,出一個讀書人不容易。葉老爺子是生,在村子里有幾分威。村里遇上什麼事兒村長就來尋人商量。這不開春又要征兵了,這兵丁要攤到每村每戶去。這年頭,打仗就是把腦袋栓腰帶上,誰家也不愿意。可若不出這人頭,又代不過去。一群人愁眉慘淡的,老遠就聽葉嘉眷在鬧。葉老爺子臉黑得跟鍋底似的。
他眼睛往張春芬上一瞥,心里頭憋了幾天的火一下子冒出來。
當初若非看在長媳連添四個男丁是葉家的大功臣,想著葉家老大在外頭當兵,一個婦道人家日子苦。接個姑娘回來,也不過添雙筷子的事兒,這才答應把人養在家里。誰知張家這個小姑娘如此歹毒。吃葉家的,穿葉家的,臨了還敢把葉家的姑娘往水里推。
任哪家的人心再好,也沒有這麼給人當冤大頭的。
“不是你把送走麼?怎地還在葉家?”
“爹,不是,你看,嘉娘都親自來說合了。”說著,葉張氏懟了懟葉嘉的胳膊,“嘉娘,你快來跟爹說說,那會春芬不是有意推你的是不是?嘉娘,你快說說。”
還指給們說話,哪兒來的底氣?!
被推的煩了,葉嘉當即道:“爹,張春芬當時可不僅把我往水里推,你看我這額頭。這就是拿石頭敲的。沒把我砸死,怕我回頭找算賬又把我扔到水里扔。運氣好,有人瞧見了剛好把我給撈上來。要不然不是水鬼一只?心里怕是恨得要死,恨人家多管閑事。”
“你胡說!”張春芬本還想裝,沒想到葉嘉紅口白牙的居然污蔑,“我只是推了你一下,是你自己磕石頭上!我頂多看著你掉水里沒管,哪有扔你!”
這一張口,把什麼底兒都給了。
葉老爺子臉鐵青,怒道,“張氏,今兒你若不把送走,你就自個兒走!老大人在外頭回不來寫不了休書,他老子替他寫!休了你這個胳膊往外拐的!”
“爹!”葉張氏慌了。
葉老爺子也顧不上在人前給長媳臉。如今村里誰不在背地里嘀咕他家養了一窩窩囊貨?笑話他親兒被外人這麼欺辱還好吃好喝供著人家。親兒差點被人殺了,葉老爺子哪里還能忍得了:“還不走?不走,好,休書現在就寫給你。”
葉張氏嚇得什麼話都不敢說,拉著張春芬就要躲進屋去。可葉老爺子這回是鐵了心,他是怎麼說都要把張春芬給送走。張春芬話一溜說出來后悔都來不及,就白著臉哭。
葉張氏一拍大往地上坐,還想學往日那般開始哭自己命苦。哭相公這麼多年來不在一個人拉拔五個孩子長大辛苦。指老爺子能看在勞苦的份上放過。葉老爺子雖是老好人,但讀書人都好面子。外人都在看著呢,葉張氏這般滿纏當真是把葉家的臉都丟盡了。
當下就要進屋寫休書。任誰都拉不住。
葉張氏嚇得要命,哪兒還敢哭?這會兒顧不上妹妹,沖過去就求老爺子別休。
公媳鬧將起來,自然是葉張氏認輸。就是再護著妹妹,那也沒自個兒重要。再說自己有四個兒子一個兒,妹妹再親能比兒子兒親麼?
吵吵鬧鬧的,休書沒寫,張春芬送走卻是板上釘釘的。今日就送走。人不送走,他就寫休書。葉張氏這會兒哪里顧得上葉嘉。哭哭啼啼地替妹妹收拾東西。葉嘉跟進去,正巧發現張春芬藏了好些東西。那銀耳環簪子的跟當的差不多款式,竟裝了一盒子。不僅首飾,裳也不。
那張春芬一看葉嘉眼神落到盒子上,跟防賊似的把東西裝起來。
葉嘉從屋里出來見院子里沒人,便也扭頭走了。
葉家莊看起來比王家村還大,這個村子至兩百戶人家。兩個村子離得不遠,公共一條河。葉嘉才從娘家出來,路過村尾的河邊。眼一瞥瞧見河岸邊上好些個婦人正在洗裳。
葉四妹正蹲在一塊石頭上,拿幾個皂角子使勁的往那被單上抹。
不過這年頭鄉下人洗澡不勤,冬日里天冷,自然是能不洗就不洗。有的人是一個冬天都不見得洗一回。睡的被子穿的裳臟得本洗不出來。那葉四妹往被子上打了好幾次皂角,洗的手都凍紅了,陳年的污垢還粘在上頭。葉嘉往旁邊一瞥,一排婦人都是這麼個況。
心想,皂角怎麼洗的干凈,就沒個皂洗的麼?
本來是隨便嘀咕,嘀咕完心里就一。
穿到這里這些天,葉嘉挖空了心思在琢磨找錢的路子。思來想去的,沒個章程。這會兒瞧著那皂角就在琢磨是不是能弄出皂來。本在現代是做過手工皂的,那東西制起來不難。當初自己在家做就是做著玩兒,但東西做出來比外頭賣的還好。
就是原料有點貴,周家目前的這況。別說花錢買本制香皂,糊口都難。
若香皂制得本高,那香胰子呢?
當初為搞手工皂,葉嘉專門去查過資料。古時候人用的香胰子,用的是豬的胰腺分泌加香皂制。一大塊香皂本高,但跟豬胰腺混在一能制出十來塊香胰子。但這東西是古時候富貴人家才用得起的,價格應該很高。葉嘉皺了皺眉頭,李北鎮沒這市場……
但也不一定,李北鎮地邊陲。這里有通往中亞國家的商路,往來的商隊很多。有本事走這條路的都是大商隊,不差那點兒錢。若是東西能被商隊收了,來錢應該也快。
這般一想,還是有搞頭的。不過若目標指向往來商隊,那東西就不能差。
葉嘉心里冒出了個念頭,立即就有了計劃。不過手一口袋,計劃也只能放放。飯要一口一口吃,錢要一文一文掙。得想個什麼法子,先賺到第一桶金。
西北的天兒是真的冷,這都二月中旬了,還沒有回暖的跡象。
天氣沉沉的,走到半路,一陣風能把葉嘉的耳朵給凍掉。著脖子,快步地往王家村走。等回到周家,剛進門,一場大雨嘩啦啦就降下來。葉嘉沒想到淋了個落湯。
與此同時,周家東屋。
余氏看著好不容易醒來的兒子,勸道:“允安,娘清楚你心里委屈。你娶葉氏這事兒確實娘心急了,可是娘怕啊!你爹你四個兄弟和你幾個侄子人全都沒了!到了這不見天日的地方,我周家就剩你一個獨苗。你子也不好,若你再有個什麼好歹,你娘跟蕤姐兒怎麼辦?”
余氏聲聲哀泣,實在怕周家的香火斷在手里。
“娘曉得你惦記著明熙。你們自定親又青梅竹馬一塊長大,自然是深些。可這不是沒辦法嗎!”急道,“周家敗了,他顧家還顯赫。顧明熙錦玉食,怎麼都不會來這苦寒之地尋你一個流放之人。你怎麼就這麼想不開?!”
“母親,”周憬琛無奈道,“與顧姑娘無關。”
“若非為顧明熙,那又是為何?”
余氏一個人撐到如今,已經是到頭了,“嘉娘確實俗了些,但相貌一等一的好,比顧明熙還明艷些!你若嫌愚鈍,不喜的。先生個孩子也是好的。將來拘在邊自個兒教便是。你難道眼睜睜看家里的香火就此斷絕?你娘將來如何面對周家列祖列宗……”
“聽話,先搬過去。”余氏也不想他,但形勢所不得不如此,“你瞧不上一個鄉野村婦娘明白,但如今家里這況,能娶到已經是掏空家底。你且與看……”
……
母子倆在屋里吵得兇,或者說,余氏不住這幾年的苦。
葉嘉頂著一腦門水回到家,剛進門便聽到周憬琛妥協似的嘆息:“兒子此生無意娶妻。與顧姑娘或者葉氏如何,并無干系。”
嗓音清越如山間霧,過耳邊是一陣麻。
葉嘉瞥了一眼那垂著的門簾,拿布巾子了腦袋上的水便轉回了屋。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公主在上:國師,請下轎
(本文齁甜,雙潔,雙強,雙寵,雙黑)世間有三不可:不可見木蘭芳尊執劍,不可聞太華魔君撫琴,不可直麵勝楚衣的笑。很多年前,木蘭芳尊最後一次執劍,半座神都就冇了。很多年前,太華魔君陣前撫琴,偌大的上邪王朝就冇了。很多年後,有個人見了勝楚衣的笑,她的魂就冇了。——朔方王朝九皇子蕭憐,號雲極,女扮男裝位至儲君。乃京城的紈絝之首,旁人口中的九爺,眼中的祖宗,心中的閻王。這一世,她隻想帶著府中的成群妻妾,過著殺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奢侈糜爛生活,做朵安靜的黑心蓮,順便將甜膩膩的小包子拉扯大。可冇想到竟然被那來路不明的妖魔國師給盯上了。搶她也就罷了,竟敢還搶她包子!蕭憐端著腮幫子琢磨,勝楚衣跟大劍聖木蘭芳尊是親戚,跟東煌帝國的太華魔君還是親戚。都怪她當年見
118.2萬字8 18555 -
完結310 章

我同夫君琴瑟和鳴
李泠瑯同江琮琴瑟和鳴,至少她自己這麼覺得。二人成婚幾個月,雖不說如膠似漆,也算平淡溫馨。她處處細致體貼,小意呵護,給足了作為新婚妻子該給的體面。江琮雖身有沉疴、體虛孱弱,但生得頗為清俊,待她也溫柔有禮。泠瑯以為就能這麼安逸地過著。直到某個月…
47萬字8 684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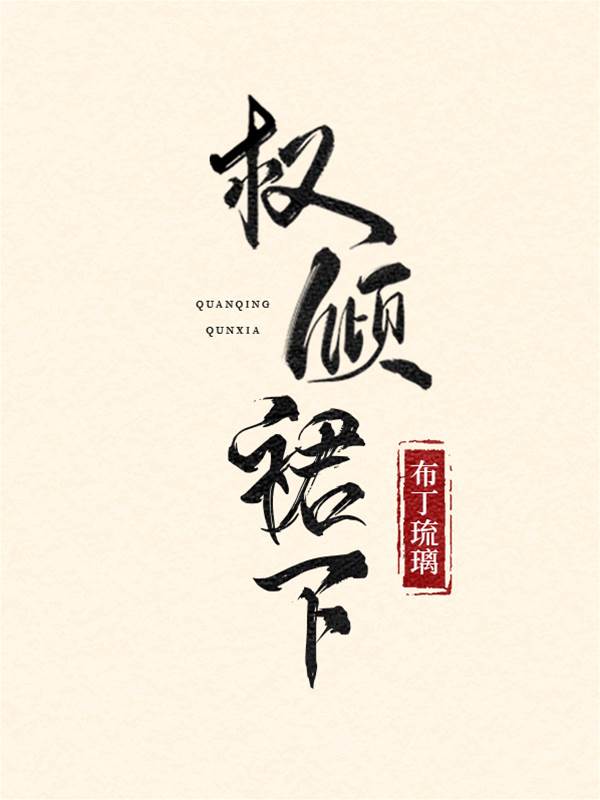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019 章

攝政王今天又在哄王妃
穿成了被繼母虐待被繼妹搶婚的懦弱伯府大小姐。云嫵踹掉渣男虐廢小三,攪得伯府天翻地覆。接著一道圣旨將她賜給了攝政王。攝政王權傾朝野,卻冷血無情,虐殺成性。人人都以為云嫵必死無疑,仇人們更是舉杯相慶等看好戲,豈料……在外冷血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卻天天柔聲哄著她:“寶貝,今天想虐哪個仇人。”
184.8萬字8 38042 -
完結183 章

誤酒
朝和小郡主黎梨,自幼榮華嬌寵,樂識春風與桃花,萬般皆順遂。 平日裏僅有的不痛快,全都來源於她的死對頭——將府嫡子,雲諫。 那人桀驁恣肆,打小與她勢同水火,二人見面就能掐。 然而,一壺誤酒,一夜荒唐。 待惺忪轉醒,向來張揚的少年赧然別開了臉:“今日!今日我就請父親上門提親!” 黎梨不敢置信:“……你竟是這樣的老古板?” * 長公主姨母說了,男人是塊寶,囤得越多就越好。 黎梨果斷拒了雲諫送上門的長街紅聘,轉身就與新科探花郎打得火熱。 沒承想,那酒藥還會猝然復發。 先是在三鄉改政的山野。 雲諫一身是血,拼死將她帶出狼窩。 二人跌入山洞茅堆,黎梨驚詫於他臂上的淋漓刀傷,少年卻緊緊圈她入懷,晦暗眼底盡是抑制不住的戾氣與委屈。 “與我中的藥,難不成你真的想讓他解?” …… 後來,是在上元節的翌日。 雲諫跳下她院中的高牆,他親手扎的花燈猶掛層檐。 沒心沒肺的小郡主蜷縮在梨花樹下,身旁是繡了一半的香囊,還有羌搖小可汗的定情彎刀。 他自嘲般一笑,上前將她抱起:“昨日才說喜歡我……朝和郡主真是襟懷曠達,見一個就能愛一個。” * 雲諫出身將府高門,鮮衣怒馬,意氣風發,是長安城裏最奪目的天驕。 少年不知愁緒,但知曉兩樣酸楚。 一則,是自幼心儀的姑娘將自己看作死對頭。 另一則,是她不肯嫁。
27.1萬字8 8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