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八零:嬌寵甜妻是富婆》 第16章傷愈
冷寒一笑,不知道是安還是打趣兒,“你小子有福了,人家可還是個小姑娘,你這老牛吃草啊!”
冷澈不語,隻是斜嫖了他一眼,冷寒臉上的笑容瞬間被凍得消失殆盡,好吧,現在不是他幸災樂禍的時候。
不過那丫頭可還小著呢,弟弟想要結婚,恐怕有的等嘍!
寧夏趴在床上哭的傷心,忽然覺手心有些意傳來。微的睫上還掛著兩滴淚珠,看起來如同被欺負慘了的小花貓一樣。
開手掌,視線落在手心,手掌中間裏不知何時多了一個水滴型烙印,烙印上正在慢慢匯集著霧氣,霧氣在眼前慢慢凝結水珠,剛好占據了整個烙印的地方。碧綠的。散發出一青草的清香。
寧夏仿佛到了一般,緩緩出舌頭,把碧綠水珠祉到口中,水滴順著咽流腹中,寧夏隻覺渾一震,由胃部向外散發著舒爽的清流,直舒服的讓想要出聲來,上傷口的灼熱痛也慢慢的消失不見。
Advertisement
寧夏覺很驚奇,抬手掀開一角自己的服,隻見上的青紫和吻痕正在以眼可見的速度消失不見,驚得趕蓋住不敢再看。
這碧綠水珠……好神奇啊!
竟然可以讓人的傷口快速愈合。。比神藥都不為過!
寧夏早就忘記了傷心,抬眼在看向自己的左手心,手心裏麵哪還有什麽水滴烙印啊,一片潔,除了脈絡沒有一痕跡。
寧夏好奇的用右手上去,眼前一晃,又置於寧府之中了。
寧夏好像想到了進出這裏的方法一樣,又在心裏想著出去,然後又出現在病房的床上!
16歲的小孩兒,上了從未見過的好玩東西,好奇心阻擋不住,就在進去和出來之間玩的開心,早就忘了自己剛剛還哭的像個淚人一般。
玩了一會兒之後,就覺得沒有意思了,寧夏起下床,下被撕裂的覺早就消失,也恢複了健康。。不在頭暈眼花,發酸發麻。
寧夏不歎,這碧綠水珠還真是個好東西!
在病房裏走走停停,著的適應程度,真的就像自己的一樣,完全應付自如。
寧夏打開窗戶,卻被窗戶上安著的玻璃吸引了目,這窗戶竟然是明的,用手上去,的還是實,真是奇怪。過窗戶看著外麵的世界,這是一副和大越國完全不一樣的畫麵。
從原主的記憶裏得知,這個世界裏的人竟然和男人一樣,可以出去掙錢養家,還有著婦也頂半邊天的名號,這一點,可比所在的大越好多了。
出生於寧府勳貴世家,即使父母比較開明,也從未有過拋頭麵的機會,現在,在這個世界,竟然可以明正大的走出去,真好!
寧夏的臉上出會心的笑容。
正想著,房門被打開的聲音傳來,寧夏轉頭去,從記憶裏得知,進來的這位是原主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300 章

穿成大佬的反派小嬌妻
醜到不行的沈從容穿書了。穿成膚白貌美,身嬌體軟,一心隻想給老公戴綠帽子的富家小明星。每天想著要蹭熱度,捆綁上位的娛樂圈毒瘤。全娛樂圈都知道沈從容矯揉造作,最愛艸小白花人設直到某個視訊上了熱搜……眾人眼中的小白花徒手乾翻五個大漢。網友狂呼:妹妹!你崩人設啦!當晚,癱在床上的沈從容扶腰抗議:「人家體弱,你就不能心疼心疼?」薄翊挑眉,摸出手機開啟視訊:「體弱?」沈從容:嚶嚶嚶……她要找拍視訊的人單挑!
186.5萬字8 14320 -
完結706 章

悔婚后,她成了帝國大佬的心尖寵
婚禮當天被陷害失身,未婚夫當眾宣布退婚迎娶親堂姐,她成了家族笑話,被祖父連夜送給江城活閻王——戰寒爵。傳聞戰寒爵是天煞孤星,娶了三任死了三任,是個又老又瞎又丑的鰥夫。天煞孤星?沒關系,反正她嫁他另有目的。可是,為什麼看…
129.3萬字8.18 87085 -
完結30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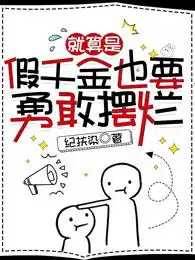
就算是假千金也要勇敢擺爛
【非穿越穿書非重生父母是反派目前定的有cp】12歲那年,沈玥喂魚時不小心掉進池塘后她知道了一件事,她爸媽不是她的爸媽,五個哥哥也不是她哥,她,是沈家的假千金!在注定會失去一切的情況下,沈玥直接卷……躺下,如果人注定會失去一切,那她為什麼不能趕緊趁擁有的時候好好享受呢?“大哥,公司好玩嗎,讓我康康。”趕緊趁她還是沈家女兒的時候進去玩一波,以后可就高攀不起
54.3萬字8.18 2616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