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著你眼紅紅》 第25章
收拾東西的事,大概傭人也會做了。
隻是剛從浴室出來的時候,便聽到了樓下的靳君揚正在打電話。
應該是打給梁宇的。
不然他不會清楚片場發生的事。
靳君揚眉間籠罩著一層淡淡的不悅,“真的就隻是拍戲了,你一步都沒有遠離?”
“除了上廁所,就連手機裏麵我們也裝了能竊聽的件,沒有任何人聯係,就是今天著實被狠狠的戲耍了一天了。”梁宇在手機那頭說道。
“以後這樣的事可以不用告訴我。”靳君揚冷冷的打斷道。
靳君揚又說了幾句,很快便掛斷了電話,轉過便看到正穿著睡站在樓上聽的葛小挽。
“怎麽,當聽狂這麽上癮?”
“我怎麽聽了,我是明正大的站在這裏聽,是你聲音恰巧傳了我的耳朵而已。”葛小挽不卑不道。
Advertisement
靳君揚幾步路走了上來,看見這個樣子,嘖嘖了幾聲,“穿這樣勾引我?”
“您,想多了。”
葛小挽的下被一隻骨節分明而又沁涼的手給了起來,力道很重,靳君揚打量著麵前的人,“他們有人說你很漂亮,的確是很漂亮,不過也就隻是一個蛇蠍人罷了,麗的皮囊再有力又怎麽樣,裏不過是早已經腐爛了的。”
“我的裏有沒有腐爛,好像也不關你什麽事。”
“你敢說不關我什麽事?葛小挽,是你的忘太大呢,還是裝傻呢?”靳君揚手上的力道加重了幾分,麵沉冷,而手勁因為太大都快要掐出一道深重的紅痕跡了。
“靳總,如果明天我要如約拍戲的話,您還是手下留比較好。”葛小挽揚了揚下,始終低著的目也迎向了麵前的這個男人。
靳君揚鬆開了鉗製,冷笑了一聲,便離開了。
像是不屑一顧。
葛小挽有些的,扶著旁邊的扶梯才能夠站立,能夠有這樣的勇氣說出怎麽一句頂回去的話,也是需要勇氣的。
很怕這個男人不管不顧,隻想讓不痛快。
可還好,他還有一清醒的理智。
葛小挽隻是錯楞了半晌,才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拿起床邊早已經放置好的劇本研讀了起來,一直看著看著,眼皮便耷拉了起來,就那麽緩緩的靠著床頭睡了過去了。
靳君揚能夠從影像裏看到這個人睡著的樣子,隨手便將屏幕給關了。
夜有些黑沉。
別墅的燈將整個區域映襯的非常的亮堂,在夜的靜謐下,反而有一種朦朧的。
手裏的紅酒,搖曳出細碎的芒流轉,這是每天都會喝的,也已經是慣例了。
靳君揚仰頭喝完手裏的紅酒,便走向了床上,想著那個人剛剛被自己住下的時候,抬起目的樣子。
他居然晃了一下神。
可見這個人,慣會演戲。
當初要不然也不會上了他的床了。
猜你喜歡
-
連載757 章

婚期365天(慕淺霍靳西)
(此書已斷更,請觀看本站另一本同名書籍)——————————————————————————————————————————————————————————————————————————————————————————————————————————————————————————————————慕淺十歲那年被帶到了霍家,她是孤苦無依的霍家養女,所以隻能小心翼翼的藏著自己的心思。從她愛上霍靳西的那一刻起,她的情緒,她的心跳,就再也沒有為任何一個男人跳動過。
133.4萬字8 22440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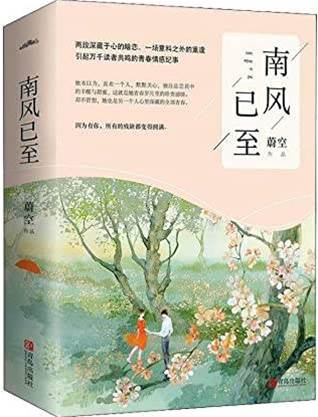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78 章

為情所婚
故事的開始,她闖入他的生活,從此天翻地覆。 故事的最后,他給了她準許,攜手共度一生。 一句話簡介:那個本不會遇見的人,卻在相遇之后愛之如生命。
20.9萬字8 19102 -
完結1547 章

墨少難惹:嬌妻帶球跑
他是商業帝王,清冷孤傲,擁有人神共憤妖孽臉,卻不近女色! 她是綠世界女王,冰冷高貴,卻…… “喬小姐,聽聞你有三禁?” 喬薇氣場全開,“禁孕,禁婚,禁墨少!” 轉瞬,她被丟在床上…… 某少居高臨下俯視著她,“禁婚?禁墨少?” 喬薇秒慫,想起昨夜翻雲覆雨,“墨少,你不近女色的~” “乖,叫老公!”某女白眼,拔腿就跑~ 某少憤怒反撲,“惹了我,還想帶球跑?”
272.3萬字8 60252 -
完結850 章

閃婚當晚,禁欲老公露出了真面目
【重生打臉+馬甲+懷孕+神秘老公+忠犬男主粘人寵妻+1v1雙潔+萌寶】懷孕被害死,重生后她誓要把寶寶平安生下來,沒想到卻意外救了個“神秘男人”。“救我,我給你一
87.7萬字8.18 36674 -
完結201 章

我欲將心養明月
高中暑假,秦既明抱着籃球,一眼看到國槐樹下的林月盈。 那時對方不過一小不點,哭成小花貓,扒開糖衣,低頭含化了一半的糖,瞧着呆傻得可憐。 爺爺說,這是以前屬下的孫女,以後就放在身邊養着。 秦既明不感興趣地應一聲。 十幾年後。 窗簾微掩,半明半寐。 秦既明半闔着眼,沉聲斥責她胡鬧。 林月盈說:“你少拿上位者姿態來教訓我,我最討厭你事事都高高在上。” “你說得很好,”秦既明半躺在沙發上,擡眼,同用力拽他領帶的林月盈對視,冷靜,“現在你能不能先從高高在上的人腿上下去?”
31.6萬字8 25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