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級綠茶穿成病弱白蓮花》 25
只是在這車上觀景,同在馬車上觀景究竟是不同。
他初被俘那段時間,尚是草木初見芽的時節,待到快出北境,也已是像這樣的秋末時節。只是北境苦寒,便是有著山巒,也是山林陡峭,風塵滾滾。他若是掀開簾子,便會被風沙撲個滿臉,什麼都尚未瞧見,臉倒是刮疼。掀開簾子稍稍久些,便立馬會遭到隨行士卒的喝止。一個被俘的國君,是沒有資格談尊嚴的,更不必提為君王的威儀。
坐在這車上不同。不必掀開簾子,他是亦能夠將窗外的景致盡收眼底。且坐在馬車上,視野也不若坐在車那般開闊,沒有辦法將山間的景致盡收眼底。
沈長思從小就對各種風景、建筑包括小都十分興趣,很小的時候就喜歡一個人在花園里寫生畫畫。沈如筠他低聲吩咐保鏢把車子開得更慢更沉穩一點,好讓長思能夠盡地欣賞窗外的風景。
車子繼續上前行駛,一道玄鏤刻著玄金暗雕花的大門自向兩邊退開。不若城門巍峨,可也較為氣派。
車子一路駛過古杉夾道的山路,地勢漸緩,一座主是紅瓦白墻,輔以綠瓦藍墻,同園林建筑相似,卻而又不盡相同的莊園,出現在沈長思的眼前。
沈長思在大恒,長在大恒,見慣了巧奪天工的天臺樓閣的他,著實被主樓邊上那棟綠瓦藍墻的建筑給驚到了。怎會有人拿綠瓦配藍墻?這也未免太過不倫不類。
倒是主樓青磚白墻前面頭,那一間明的玻璃溫房瞧著別致,應是一間花房,里頭花團錦簇,盎然的春意像是要從里頭跑出來,瞧著熱鬧。
車子在開闊的前庭停下。
保鏢替沈長思開車門,沈長思下意識地把手過去。余掃見保鏢玄西裝,而非小福子的綢緞長衫。沈長思垂下手臂,收攏了之指尖,從車上邁下。
Advertisement
沈長思抬頭,看了眼眼前這幢莊園。
日后,他便要鳩占鵲巢,以沈公子的份,于此安立命了麼?
…
“住了幾天的院,悶壞了吧?要在花園里坐坐,曬曬太,還是先回房休息?”
沈如筠也下了車,他走到長思的邊。
沈長思先是過了數年被俘的生涯,回大恒后又過了十余年冷宮幽的生活。莫名其妙來到這異世,又在醫館住了數日。他自是不愿先回房,又在一個相對閉的空間里。
“朕……(正)好,我想在花園里坐坐,曬曬太。”
“也好。多曬太補補鈣。我讓人給你泡一壺茶過來。肚子不,要不要讓廚房送幾塊蛋糕過來?”
無論是茶也好,蛋糕也好,都是沈長思未曾嘗過的。
沈長思還是太子時,便偏好甜食。小時候母后不許他多吃,吃多了壞牙,嚇唬他一個君王要是長了一口壞牙,難免為有礙君王威儀。長大后,又有阿元管束著他,無論是糕點還是果脯,只需他一日吃一回。一回還有數目上的約束。
母后跟阿元越是拘著他,他便越要貪。倒是后來去了金涼,金涼乃蠻荒之地,蔗糖乃至含糖的糕點跟其他甜食都是稀罕吃食,他一個俘虜自是吃不起的,漸漸也就將這偏好甜食的喜好給戒了。
沈長思有那位沈公子的記憶,知曉茶跟蛋糕,也知道他們的味道是甜的,可他腦海里的記憶畢竟模擬不出氣味同味道來。聽沈如筠提起這茶跟蛋糕,便起了興致。
他不習慣言謝,倒還是對沈老爺子說了一句,“有勞爺爺了。”
“跟爺爺還客氣什麼。”
沈如筠吩咐管家去廚房讓送茶跟蛋糕過來,他則一起陪沈長思在一樹下的圓桌旁坐了下來。
管家端上茶跟蛋糕,以及老爺子喝的白茶。
沈長思端起茶,瞥了眼這似土塊一般的茶,著實瞧不出這玩意好喝,也便有些猶豫,只是聞著確實香。沈長思試著嘗了口,這所謂的茶瞧著一點都不討喜,味道確是不錯。
茶的味道不錯,沈長思便也想要嘗一嘗蛋糕。沈長思沒在桌上瞧見筷子,只瞧見了這個朝代獨有的用餐工,刀叉。沈長思知曉這刀叉怎麼用,可他擔心他自己頭一回使用這玩意,就跟他自己穿那般,到底不練,會在老爺子面前出端倪,也就暫時沒去那塊蛋糕,只慢悠悠地喝著他的茶。
沈如筠喝了口白茶,嘆道:“我們爺孫兩人,有多久沒有像今天這樣曬著太了?也不知道爺爺還可以陪你曬多久的太。”
沈長思并非真正的沈家大爺,可他并非草木,他住院這幾日,除了這位沈老爺子,以及惺惺作態的裴慕之跟鐘麟兩人,誰也未曾來探過他。對于老爺子這份惜孫兒之心,沈長思自是記在了心里。
沈公子不知能不能回到這子里,如同他不知能不能再回到大恒,不管如何,沈公子一天不能回到這里來,他便替沈公子敬一天的孝。若是當真他得當一輩子的沈家大爺,他便也替沈公子抗下這責任。
沈長思將手輕輕地覆在老爺子放在桌子上的手背上,“爺爺,您一定能長命百歲的。”
沈如筠是個豁達的人,他并不忌談生死。他欣地拍了拍沈長思的手,“長命百歲也未必見得就一定是好事,其實爺爺不怕死,人難免總得走這一遭。爺爺只是擔心,要是哪天爺爺走了,你爸媽又都一心只在樂樂上,留你一個人……”
爸媽,樂樂?
沈長思在醫館里除了這位沈老爺子,一個家人也沒瞧見。他以為沈公子同他一樣,父母早亡。這會兒聽了沈老爺子的話,這才想起,沈公子的父母不但尚且健在,他還有一個小了數歲的胞弟。
沈長思喝著杯中的茶,眼底掠過一抹涼薄的嘲弄。怎的換了個子,竟還是給人當兄長?
“我原先覺得娛樂圈太過復雜,裴慕之又在這個圈子里待了太長的時間,覺得他并不那麼合適你。接下來,盡管依然不是很喜歡他,但是看在他對你還不錯的份上,也就幫著說服你爸媽,同意了你跟他的婚事。現在,既然出了他做出了這樣荒唐的事。長思,你給爺爺一句準話。關于你跟慕之,你到底是怎麼想的?你是打算原諒他,日子繼續就這麼繼續過著,還是……”
“長思!”
裴慕之氣吁吁地趕到,爺孫兩人的談話因此被打斷。
裴慕之稍稍緩了緩呼吸,他抿起,“爺爺,我能單獨跟長思聊聊嗎?”
還有臉追到這兒來!
沈如筠繃起臉,他轉過頭,看向沈長思,“長思,你的意思呢?”
…
不過一個戲子,焉配單獨同他談話?
沈長思慵懶地地放下手中的茶杯,他起離開位置,走到沈如筠的邊,笑著道:“爺爺,您一大早去醫院接我,又坐了一路的車,應該很累了。我先扶您進去休息好不好?”
這位一手創立了盛世百貨帝國的老人,哪怕如今年紀已近八旬,仍然思敏捷。
沈如筠當即領會了孫子的意思。老爺子把手搭在沈長思的手上,由長思扶著站起,“好,好。我們回屋休息。”
“長思!”
裴慕之追了上去,被保鏢隊長陸遠涉命人給攔下了。
“你們讓開!長思,長思——”
裴慕之不甘心地在后大喊。
沈長思停下腳步,“爺爺,您在這里等我一下。”
沈如筠在心底嘆了口氣。長思這孩子,心太了。實在不像是沈家的孩子。像是他的兩個兒子,包括娶進來的媳婦,婿,哪個心不?
長思這孩子,像他。老太婆心了一輩子,同誰都和和氣氣,老大同老三家的媳婦都不是省油的燈,待老太婆也算是客氣。長思這子,還是得找一個真心待他的,否則等哪天他閉了眼,把長思給裴慕之那樣一個人,他怎麼能放心?
等裴慕之離開,他還是得跟長思好好談談。
沈如筠沒有在原地等,他自己一個人慢慢地往屋子里走。管家要上前攙扶他,沈如筠擺了擺手,拒絕了,只低聲對管家吩咐道:“你讓小陸他們幾個跟在爺的邊,別離開。”
猜你喜歡
-
完結211 章

在他懷里99次撒野
許青梔等了霍南衍十年,卻只等回一個失去他們共同記憶的霍南衍。她不擇手段想要再次得到他,卻只將他越推越遠。而當她終于累了的時候,他卻回頭了。人人都說,霍南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絕不可能被那個臭名昭著的女人,玩弄於股掌之間。後來,他一句話破壞她的婚禮,她紅著眼將一紙妊娠書摔在男人的臉上:「霍南衍,你贏了,我會乖乖把孩子打掉。」男人怒極反笑,「許青梔,帶著我的孩子嫁給別人,你還有理了?」
47.6萬字8 8019 -
完結84 章

晨昏游戲
懷歆大三暑期在投行實習,對年輕有為、英俊斯文的副總裁驚鴻一瞥。——男人溫和紳士,舉止優雅,連袖口處不經意露出的一截手腕都是那麼性感迷人。足夠危險。但她興趣被勾起,頗為上心。同時也意識到這段工作關系對自己的掣肘。某天懷歆濃妝艷抹去酒吧蹦迪,卻…
32.1萬字8 6555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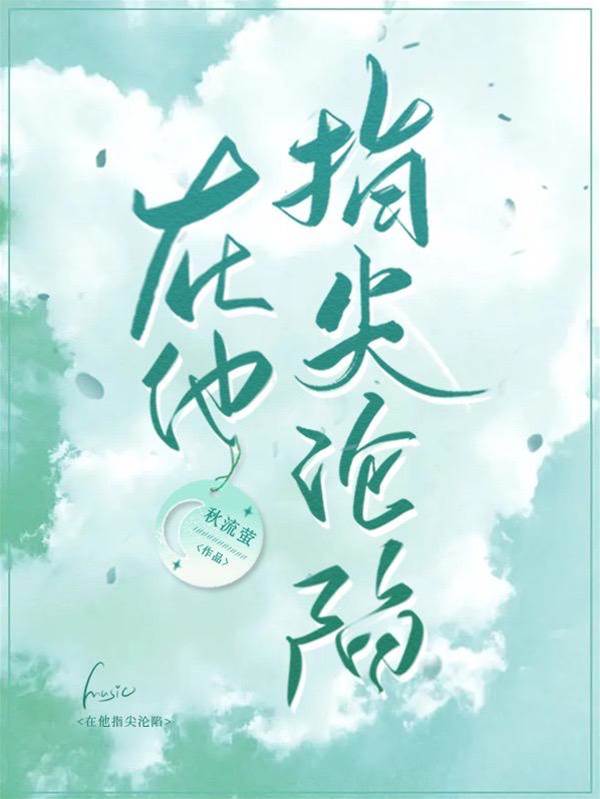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18 22009 -
完結314 章

被捕後,大佬將她押到民政局
未婚夫成了拆遷戶,領證當天當場悔婚,閨蜜帶她慶祝單身,醉酒後醒來竟被警察叔叔按頭結婚?“不好意思,我家農村的,條件不太好。”“沒事,我的收入也不穩定,以後多擔待。”沒想到婚後,天天在家不學無術的弟弟竟手握數十項專利身家數十億!隻會種田的親娘養父竟是農產品大亨,糧田遍布天下!親爹竟然就是自己公司的董事長,要把公司交給她打理!政府分配得來的老公:“這就是你說的家裏條件不好?”她指著電視裏在演說的年輕大佬:“這就是你說的創業中,收入不穩定?”某年輕大佬悻悻不語,心道:可能年賺百億,也可能年賺千億,可不就是收入不穩定?
57.8萬字8.18 49037 -
完結73 章

獨家偏愛
文案一易冉這輩子做過很多傻事:諸如在八歲那年把自己剔成了個刺猬頭,十三歲那年翻圍墻摔下來砸在了林昭身上。但什麼傻事,都比不過無視林昭的一腔愛意,離家出走,選擇去追逐顧則宴。她在顧則宴那傷了個徹底,不敢回家,在出租屋里熬夜畫畫。她不知道,每個風雨交加的夜里,屋外都會有一輛私人轎車,車里的男人,目光熾烈,是至死方休、糾纏到底的決絕。曾經,她害怕林昭的獨占欲。后來,徹底淪陷。文案二顧則宴經過數年的打拼,已經將顧氏發揚光大。而追逐了他三年的易冉,在別人眼里不過是個笑話。一個溫溫吞吞的女人,從來不得顧則宴一個好臉色,而對方的白月光也要回來了。顧則宴和白月光的愛情,易冉從很多人那里聽到過。沒有一個不感嘆那位白月光有多純潔,多有才華,多高貴,兩人是多麼的般配。易冉明白了,這是太愛了吧。所以即使他接受了她的告白,他也沒有對她流露出半分的溫情過。誰都沒想到,先離開的會是易冉。聽說她走后,顧則宴只是淡淡地說了句:“早晚會回來的。”而后來再次見到她時,她已經是小有名氣的畫手了。不單如此,她還是南城易家的獨女,是當家人易江的掌上明珠,也是創世集團總裁林昭的未婚妻。她正對著林昭明媚地笑著,那樣的笑容,落在顧則宴眼里,只有扎心。
13.7萬字8 66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