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嫁后影衛小夫郎揣崽了》 27
衛楚已經有些時日沒有活筋骨了,此番見到自己送上門來的,不由覺得新奇,同時也生出了困擾。
是先打斷左邊那人的,還是先折了右邊那人的胳膊呢。
衛楚視線緩緩下移。
他們兩個其中一人手握的尖刀上還印著跡,那未曾凝固的相比普通傷口流出來的要更為殷紅。
喪命在衛楚手下的亡魂不,故而見到這種狀況,衛楚也只需隨意一瞥,便能輕易得出那究竟是從脖頸流出來的,還是不慎傷了胳膊大之類的地方才流了的判斷。
想來是盜了人家的財不說,還殺人滅了口。
既如此,那便是徹底留不得了。
不過為了保險起見,他還是應當證實一下,以免真的殺了罪不至死的普通飛賊。
“如今走梁的也開始沾了?”
衛楚低頭整理了一下繁復的擺,引得那兩人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本顧不上回答問題。
良久,他們兩個才爭搶著對衛楚說道:“干咱們這行的,就得膽子大,沒點兒績又如何讓道上的兄弟們服氣?”
得出了正確的結論,衛楚也就明白了自己該怎麼做,他正要手,忽然聽見了院墻下方傳來一陣罵罵咧咧的男子聲音。
“狗娘養的,敢贏老子的錢,瞧我明日不找人弄死他!”
衛楚覺得這聲音聽上去很是耳,便歪頭凝神細聽了一番,順便抬手制止了對面兩人正朝他走過來的作。
那兩個飛賊見這姑娘倒當真是不怕人,于是又驚又喜地對了下眼神,心想著定要將人搞到手里好好供養起來留作賞玩,自是不知他們二人即將連封書都留不下地殞命于此。
“爺,咱們這個時辰才回來,不會被侯爺和夫人抓個正著吧?”
Advertisement
說話的另一個男子聲音尖細,倒比罵人的那個讓衛楚好辨識些,是聚荷廳那日,始終待在楊安達邊的小廝。
“別提了,每每想起這事我便氣得頭疼。”
楊安達的聲音越來越近,想是已經走到了府墻下方,很快便要轉過這個彎兒,走到侯府正門了。
“爺怎的頭疼了?可要小人去府醫在合閣中提早候著?”
“不用!我頭疼還不是因為那個死病秧子,廢!怎的一點都不明白我的意思!”
楊安達順手就給了邊人一耳刮子,勉強算是泄了憤。
“爺息怒,息怒,”小廝訕訕地賠著笑,“莫要氣壞了子,長公主殿下擔心了不是?”
“母親這個時候定然在為他的事忙活,何曾在意過我是否晚歸,是否康健!”楊安達哼笑一聲,“得虧太子殿下去年尋了個機會替我對他下手,可憾的是,竟然沒弄死他,不過好在斷了他的一條……”
衛楚的拳頭倏地攥,指節發出聳人的彈響聲。
楊安達頗為得意的話鋒陡然一轉,似是想到了什麼不高興的事,接著咬牙切齒地恨恨道,“我那時本以為他這輩子徹底是廢了,可誰想這個病秧子,這個病秧子他娘的竟然站起來了,真是氣煞我也。”
衛楚閉了閉眼睛,總算按下了心底急遽迸現的殺意,緩緩抬頭,朝對面那兩個盜賊看去。
.
鎮南侯府厚重威嚴的大門前,即將換崗的府兵們正等著下一批的兄弟前來接班,突然聽見屋檐上方傳來一道令人骨悚然的慘烈聲,隨后,兩個被牢牢捆在一起的男子便從漆黑燙金的門楣上掉了下來。
與此同時,楊安達正一腳邁上了侯府門前的夯實臺階,兩人摔下來的方向剛好不偏不倚地朝在他的正上方——
突如其來的意外讓楊安達來不及反應便被砸了個結結實實,險些一口大氣沒過來,直接就去了。
“啊——我的!我的!你們都眼瞎嗎?還不來扶本爺!家福!家福!”楊安達聲嘶力竭地吼道。
府兵們一腦兒地朝地上摔得半死不活的賊匪奔去,卻聽見了趴在地下的楊安達的罵聲,紛紛驚異道:“三爺?!”
小廝家福早在那倆人砸下來的瞬間便躥到了一邊,此時見到府兵們過來,心中也就沒那麼怕了,這才大驚小怪地朝楊安達跑過去,聲嘶力竭地哭起來:“爺!爺啊!你們快將這兩個東西搬開啊!爺若是傷了,你們就等著侯爺和夫人弄死你們吧!”
府兵們原本就對這在福中不知福的三爺十分鄙夷,此番見他邊的區區一個小廝就膽敢恐嚇他們,竟不約而同地都沒去管那躺在地上的楊安達。
“你們做什麼呢?!為何還不……啊——我的,為何還不將本爺扶起來?!”楊安達厲聲哭道。
“三爺有所不知,被重砸在上后,不可立刻起,要尋大夫來查看一番骨頭是否有損,才能再做決定,”一個看上去像是個管事的府兵微微頷首,朝被臺階硌得臉發青的楊安達抱了抱拳,算作是抱歉,“為了不讓三爺再次到傷害,只得委屈您在這兒躺到大夫來了。”
他這話說得十分在理,饒是極張口就罵的楊安達也挑不出病來,畢竟他現在疼得厲害,確實不想讓自己再一次傷。
得以轉移注意力的府兵迅速從其中一個賊匪的上搜出了一對兒玉白龍紋杯。
雖不知是哪家高門大戶得到的賜寶貝,但單憑直覺來判斷,便知這稀罕玩意兒是決計不會屬于這兩個猥瑣賊匪的。
對于膽敢盜賜之的賊人自是無需手,府兵可不管他倆的胳膊兒折了沒有,上去就是一個表忠心的飛踹:“吃了熊心豹子膽,敢到我們鎮南侯府來了?!”
***
衛楚回到臥房的時候,衛璟已經裝模作樣地睡下了,他只等院里的人都睡了,再地離開清沐閣,趁著月黑風高潛那私養孌給朝中高的吳德府中去。
通過楊安達賬本上的記錄得知,吳德將會在年后從涪州城弄來一批未經人事的孩子,藏在府中好生教習后,便打算讓他們去伺候京中癡迷此道的王公貴族,以此來達巨額的收益。
因此衛璟便想著要在年前去吳德府中將證據收集齊全,然后再在大年三十、除夕當晚,送給吳德及宮城中那位太子殿下一份厚禮。
一份足以讓他在最重視的父皇面前狠狠栽一跟頭的厚禮。
畢竟區區一個吳德,還不足以有能力支撐住如此龐大的人脈關系,他背后的那位太子殿下,才是這齷齪勾當中最大的獲利者。
在太子衛驍的心計劃下,吳德得到數之不盡的滾滾錢財,而他得到要挾控制大臣的重要把柄。
衛楚作輕緩地打開門,見臥房中的人似乎已經睡下了,便轉想要離開。
突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麼重要的事。
外頭寒氣人,連帶著衛楚的上都被冷意侵襲得徹,房門開合間,涼冷的空氣也趁機一起鉆了進來。
衛楚背著小包袱走了兩步,忽而擔心頭上珠翠的撞聲會吵醒衛璟,便抬手攥著步搖,小心翼翼地朝床榻邊上行進。
早在衛楚進了臥房時,衛璟就已睜開了眼睛。
床榻前垂墜著單薄的床幔,衛楚逆著,看不清床榻上的人沉睡與否,卻剛好可以被衛璟將他的樣貌看得一清二楚。
月過檀木窗欞,清暉落在衛楚瑩潤蒼白的臉上,映流輝,恍若謫仙。
衛璟迅速從下意識的呆滯中回過神來。
算著日子,今日衛楚該是在隔壁臥房睡才對,怎的會在這個時候來他的臥房?
不過世子妃一向穩重,定是自己記錯了。衛璟心道。
思慮間,衛楚已站定在了床榻邊上。
衛璟急忙闔上眼睛繼續裝睡,默默觀察著他接下來的作。
瞧著世子妃今日的狀態,倒不像是平日里落落大方的模樣,行為做派仿佛很……扭?
衛璟微微瞇起眼睛,從睫的隙中再次瞥了一眼衛楚的臉。
容姝麗的世子妃時不時地輕咬一下,似乎是在心中做著什麼令自己到為難的決定。
猜你喜歡
-
完結414 章

幸得相愛,陸少深深寵
陸總,您剛剛說了想結婚,不知道我可以嗎?遭遇背叛後,唐若初找了素昧平生的某人組團結婚,各取所需。卻不料,這一場婚姻是她整個人生的轉折,前路生死未卜,是又一場虐心的疼痛,還是真正蛻變的甜寵,亦或者是她這輩子對愛情最後的停靠?"--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70.2萬字8 259497 -
完結594 章

致命心動!
【瘋批男主+頂級豪門+團寵+雙潔強寵+超甜瘋撩】前世,虞桑晚錯信渣男,害得家破人亡,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她的貼身保鏢江遇白護著她,為她慘死。重生歸來,她虞桑晚勢要所有人付出代價!打臉虐渣、遇神殺神、遇佛殺佛!逼仄的車內,她笑眼彎彎的望向他:“江遇白,不準給別人做小白臉,我可以加錢~”他笑而不語,眸色瀲滟,性感的喉結滾動了一下,掩蓋了眼底的欲色。世人都嘲笑他是虞家大小姐養的小白臉。直到虞家落難時,媒體拍到京圈頂級豪門繼承人江三爺屈尊降貴將虞桑晚堵在墻角,掐著她的腰,啞著嗓音低聲誘哄:“我的大小姐,嫁給我,前世今生的仇,我一并為你報了。”虞桑晚:“!!!”有人認出,視頻里痞野矜貴的男人正是虞桑晚的保鏢——江遇白!【雙強+大小姐重生,專治各種不服】
89.3萬字8.33 27364 -
連載428 章

首富入贅我家寵瘋了,我負責數錢
逃婚前,白念是個扶弟魔。被父母長期PUA,每個月上交5000塊供弟弟讀名校,還房貸。 然而,父母為了給弟弟還賭債,拿了老男人50w彩禮把她賣了! 覺醒后,她轉頭就和路邊流浪漢扯了結婚證,領了個倒插門女婿回家,讓吸血鬼父母再也要不出一分錢彩禮! 誰知婚后她的財運竟直線飆升! 吃火鍋,享免單。 撿了一張刮刮樂,中大獎。 從售樓處門口路過都被選為幸運業主,免費獲得黃金地段大平層一套! 她以為狗屎運也就到此為止了,直到她到凌氏集團應聘…… 驚訝的發現凌氏總裁竟然和自己倒插門的老公長得一模一樣! 男人正襟危坐在辦公椅上對她莞爾微笑:“老婆,來應聘這里的老板娘嗎?” 白念懵了,回頭一看,全體員工早已畢恭畢敬:“歡迎總裁夫人蒞臨指導!”
84.7萬字8 1778 -
完結75 章

笨蛋美人是小細作
輕鶯最近頗爲苦惱,爲了探取情報,她被獻給權傾朝野的丞相裴少疏。 傳聞裴少疏淡漠禁慾,不近女色,唯獨對崇禾公主另眼相待。 偏她倒黴得很,居然長着跟公主七分相似的樣貌,便稀裏糊塗地被逼做裴少疏身邊的細作。 爲了引誘裴少疏上鉤,她使盡渾身解數。 假摔跌進人懷裏,不料一頭栽進池塘。 脫了衣裳跳舞,卻被衣衫絆倒在地。 笨手笨腳,破綻百出。 鬧了許多啼笑皆非的笑話以後,裴少疏仍舊不上鉤,始終一副清風朗月,清冷出塵的模樣。 任務不完成,她身上的毒就得不到解藥。 被逼急的輕鶯決意破罐子破摔,使出“強硬”手段,月黑風高夜,鑽進了某人寢屋被窩,卻不知該如何下手。 思索間,孤高清冷的丞相大人將她摁在榻上動彈不得,冷笑:“伺候人都不會,不會親就莫要‘獻醜’。” 輕鶯不明白自己哪裏醜,有點委屈:“沒人教奴婢……” 裴少疏淡淡垂眸:“張嘴。” “唔——!” 一夜春雨溼透,輕鶯默默裹緊自己的小被子,邊擦眼淚邊揉腰:說好的禁慾丞相呢?!謠言!通通都是謠言!
25.4萬字8 2313 -
完結2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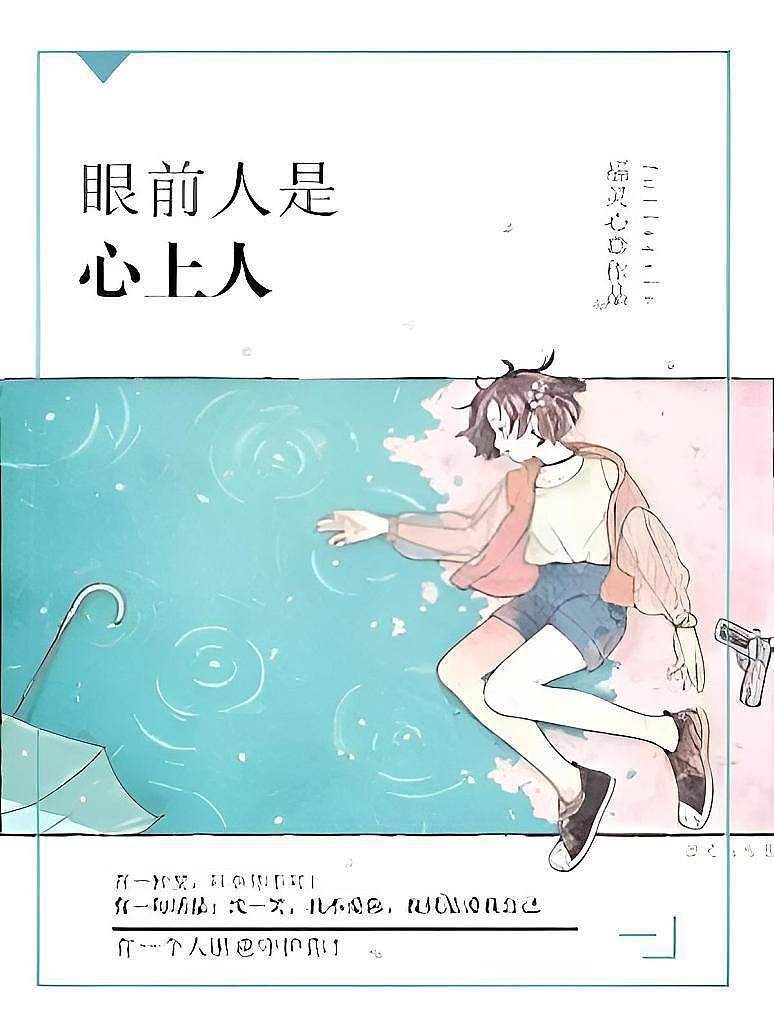
眼前人是心上人
巫名這兩個字,對于沈一笑來說,就是掃把星的代名詞。 第一次她不走運,被掃把星的尾巴碰到,所以她在高考之后,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離開。 卻沒想到,這掃把星還有定位功能,竟然跟著她來到了龍城! 本來就是浮萍一般的人,好不容易落地生根,她不想逃了! 她倒要看看,這掃把星能把她怎麼著。 然而這次她還是失算了。 因為這次,掃把星想要她整個人……
25.9萬字8 161 -
完結665 章

從良
溫婉賢良的宋意有個秘密,多年前,她在走投無路時跟過一個男人, 她見過他的狂浪,受過他的輕視,也在無數個深夜與他交頸而眠。 銀貨兩訖,她以為他們永不會再見。 多年后,她接醉酒的未婚夫回家,噩夢再現。 那個男人將她拽入包廂,把玩著她無名指上的婚戒低笑: “想從良?經過我同意了麼?” * 頂級惡霸×良家婦女 男女主權力、地位懸殊,強取豪奪戲份多,請勿過分代入、較真。
117.1萬字8 1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