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鍾》 第25章
25
額上的傷過了約莫一旬才見好,唐橋淵最後一次為方素解下白淨紗布,見那一塊傷口已徹底結痂,總算松了口氣。
這人心疼那旁邊完好的,問道:「還疼不疼?」
方素搖了搖頭,唐橋淵不敢當真上去,他自己倒毫無顧忌,手拿指腹輕輕,回道:「按著有點疼……但未再到頭痛了。」
唐橋淵蹙眉,急忙拉下他的手握在掌心,話裡帶著責備道:「別去,才剛拆了紗布,不知還要養多久。」
方素彎,沒有反駁,對他點頭回道:「我會小心一些。」話落暗自想著腦中倏然浮現的舊事。
所回憶起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方素那時可憐,而現在回首只覺好笑而已,不過縱然再覺有趣,眼下他看著這人如此張的模樣,都不忍把這故事說出口來,以免令其心疼。
方素想說的是小時候被罰跪的事,他忘了當初被二娘懲罰的緣由,只記得天已夜,他困乏不堪,卻仍被罰了個通宵,在門外院裡反省。
跪著跪著,小小年紀沒有足夠耐力,方素很快便打起了盹兒,腦袋一抖一抖,最後子「噗通」一下倒下去,額頭摔倒泥土上,好巧不巧被一塊糙小石子割破了一寸皮。
方素疼得「哇哇」大哭起來,方父起出來看,這才忍不住把他帶回房裡休息,而他的二娘見他腦袋上流著珠子,瞪了一眼後也不再繼續為難。
明明摔破了頭,年的方素卻覺得走了好運,終於能睡到床上。頭上摔破的地方沒有花錢買什麼金貴藥膏,僅是草草地敷了幾片方父從林裡摘來的藥葉子,不知不覺竟也完好如初。
如今即使仔細去看,也瞧不出半點傷痕。
Advertisement
方素一邊想著,一邊下意識地抬手,往回憶裡的那地方,轉眸向唐橋淵問道:「橋淵,我的傷口不淺,往後會留下痕跡嗎?」
唐橋淵看他剛才走神,不知他在想些什麼,此刻聞言不一笑,在他傷口旁邊親一下,回道:「大夫說不會,我雖不知究竟會如何,卻覺得留與不留都無甚所謂。」
「嗯?」方素出猶疑神,不是十分認同。
他不是子,不會在意自己是否面相俊秀,然雖如此,他亦不願自己變得丑陋古怪,更何況如今有相好之人在邊……在他看來,唐橋淵儀表堂堂,本就值得上更好的人,方素不希自己站在這人邊時總不願抬頭,只怕出疤痕會令其面無。
方素心裡如此作想,上不經意便說了出來:「額上留疤,別人看著都會害怕的……」
「這有什麼好怕的,」唐橋淵托著他下頜轉頭看來看去,作出凝神細思的神,罷了故作正經,回道,「害怕不會,倒很有一番特,我可以改口你‘丑素素’。」這人說著,故意抬手擋住他一邊臉頰道「這是素素」,隨後立馬又換一邊樂道「這是丑素素」。
「咦?這麼好的素素,我竟然有兩個。」唐橋淵笑著把他往懷裡抱。
方素忍俊不,斂不住滿目笑意,被他抱時手環住他後背。
心中甜如飲,他經歷過時悲傷與他人興許一生都不會遇著的險境,因此如今心存激,驚喜著為何偏偏就是他,能得到這樣的唐橋淵。
方素捨不得放手,聽唐橋淵此時玩笑開過,溫哄著:「我的素素最好看,就算留下疤痕,也最好看。」
這人道罷,俯首在他發頂一吻。
方素不想打破眼下的怡人氛圍,卻終究忍不住了,離他遠了幾寸之後猶疑回道:「橋淵,我有幾日不曾洗過頭發了……」
唐橋淵微愣,罷了揚眉笑出聲來,心想他的方素從前明明不會這樣說話。就在十幾日前,方素都還會為燒水沐浴而尷尬臉紅,沒想到現在竟也能這樣捉弄起他來了。
這人笑了許久,手方素「幾日不曾洗過」的頭發,頷首道:「那還是我替你洗,不過天晚了,正好一道沐浴了。」
方素點點頭,唐橋淵下榻起,去院裡喚人燒水,走到廊外時忽然想起了什麼,敲一敲窗又道:「素素,既然已經拆了紗布,明日便出外走走,你也在這府裡困了小半月了。」
方素當下答「好」,只因習以為常,鮮對這人說一個「不」字。等到外頭的腳步聲走遠之後他才緩緩一愣,又想起額上的疤來,總歸還是有些不給陌生之人瞧見……
正煩惱著,又有人聲漸近,片刻後房門被輕叩推開,姑娘行到簾外後停下腳步問候:「夫人,奴婢給您端藥來,您若方便,奴婢便進來了。」
「好,」方素頷首答應,白萍掀簾而,彎眉將湯藥送到他手上去,聽他靦腆接道,「有勞白萍姑娘。」
白萍習慣了他話裡的客氣,心知他只是生如此,並不是疏遠的意思,因而不像曾經那樣捉弄他,僅笑著回一句「夫人客氣了」。
藥碗捧在手中,方素沉默看了看,索也不用那瓷勺,端碗快速飲下,苦得直皺眉。
白萍在旁看得輕笑,接過空碗後問道:「夫人可要嘗些餞?奴婢去為您取些。」
「不必了,」方素擺手,「苦一苦就好了……白萍姑娘,這藥要喝到什麼時候,我額上傷口結痂了,也不再頭昏腦脹,今日拆了紗布,已經好了。」
他把話說得認認真真且頗有些委婉,但裡意思仍然瞬間便被人兒似的白萍給聽了出來。這姑娘無聲一笑,越發覺得方素雖聰明,但許多時候都格外單純,什麼心思都能擺在明面上,方才幾句看似簡單陳述,實則就是抱怨訴苦,不想再喝這藥湯了。
白萍有意不拆穿,也如他一般認真回道:「傷口確是結痂了,不過卻算不得好,夫人還需好生養著,湯藥還剩幾副,還當仔細服用。」
方素期待的雙目裡頓時閃過一失,不再說什麼,乖順地點點頭。
白萍「噗嗤」一聲,急忙抬袖掩,樂得不支,實在不忍再欺負下去,安說道:「夫人再忍耐數日,奴婢以後送藥過來都給您帶些餞果子。」
然而不安還好,如此一安,方素反而得雙頰泛紅,暗藏的心思被毫不留地穿,想他十八、九歲的年紀竟還害怕苦藥,更甚者,居然還是被一個姑娘家給發現了,真是太難為。
方素垂著眸子抿不言,白萍擔心再笑下去會令他更加窘迫,有意岔開話道:「對了夫人,白日時莊主曾向我提及,說是夏日氣候越發炎熱,該為您添些更加輕巧單薄的新。您剛來的時候裳都是隨意備下的,如今再行添置,還是問問您的喜好。」
「嗯?」方素果不其然被引開了心思,抬眼著,搖頭回道,「我都好,還是隨意一些吧,不必考慮我的意思……」
「倒不能不考慮,」白萍笑道,「您喜歡的,莊主才覺得滿意,否則再好的東西,他都能給扔出院子去。」
不過是一句玩笑話,方素卻驟然張,連忙回道:「那便添些淺的吧……我都喜歡,扔了多可惜。」
「是,」白萍聞言福,順眉應道,「奴婢記下了。」
方素聽著話裡笑意,後知後覺地明白過來,發覺白萍又趁他張時候將他善意捉弄了一番——什麼扔出院子去,他正用著的那些不都好好地在櫃子裡?
方素無奈看著前這姑娘,不知再說什麼才好。
恰逢此時,去外喚人燒水的那人回來了,白萍側,在唐橋淵進來時對他施一施禮,帶著空碗離開房間,留他二人獨。
唐橋淵坐回榻上,把方素披散在後背的長發攏到一側前,手他頸後,看他是否到悶熱發汗,但覺掌心溫熱,卻不見汗漬,便直接問道:「素素熱不熱?」
「這時辰了,不會覺得熱,」方素搖頭,「日中的時候稍微有些悶,不過我不常發汗,不會到粘膩難。」
「但總會不舒暢的,」唐橋淵笑道,「往後日中的時候,你若嫌悶,便人去冰窖鑿冰,涼些綠豆湯給你喝。」
方素從未聽過什麼冰窖,霎時出好奇神。唐橋淵瞧了出來,笑道:「明日帶你去看看。」
「好。」方素愉快點頭。
沐浴熱水還未備好,唐橋淵與他一同等著,閒得無事又問道:「素素方才同白萍聊了什麼?」
「嗯……白萍姑娘說,要添置一些夏給我,」方素扯了扯自己的袖回道,「橋淵,我上穿的就薄,其實不必再添。」
「要的,」唐橋淵滿臉正經,「我有兩個素素,一個人的裳就不夠穿了。」
方素先是一愣,隨即反應過來,記起了這人半晌前講的趣話,笑出聲來前便被這人攬著親了兩下。
「什麼都要雙份的。」
方素低聲笑個不停,片刻後輕輕著他食指,低聲回道:「但我只要一個橋淵就夠了……」
唐橋淵彎,反握住他的手,慢慢地將十指扣。
猜你喜歡
-
完結162 章

老婆粉了解一下[娛樂圈]
作為人氣偶像霍希的老婆粉 喬瞧最討厭的人就是捆綁霍希炒緋聞的女明星盛喬 日常除了扛著相機追活動,就是實名diss這個白蓮花 沒想到一朝撞到頭,醒來后她成了盛喬 與霍希首度合作的愛情劇拍攝過程中,第一場戲NG了二十七次 霍希:盛喬,你到底能不能行?不能行換人! 喬瞧:老公你別生氣啊,我行的! 霍希:??? 媒體:《盛喬漏嘴喊出親昵稱呼,霍希隱婚曝光》 霍希粉絲:cnm盛喬你這個蓮花婊快出來道歉澄清! 隔日,盛喬微博解釋:那個……老婆粉你們了解一下? 絕地反擊,逆風翻盤,強勢挽尊 【女主從全網黑嘲到全網追捧,順便和愛豆談個戀愛】 當紅小花盛喬最近被拍到跟影帝在交往 霍希接受媒體采訪時,記者請他給這位圈內粉絲送上戀愛祝福 他冷冷看向鏡頭:假的。 盛喬微博忙不迭辟謠:我獨唯,不爬墻,謝謝大家。 當晚,愛豆在她耳邊咬牙切齒:公布戀情,立刻,馬上。 【存稿充足,每天上午十點下午七點定時雙更,不虐不渣,甜蘇爽,請放心跳坑~】 【追星文/追星少女的日常/粉圈常態/,不喜誤入】 【各角色沒有原型】 【微博:@春刀寒】
47.1萬字8.33 13885 -
完結144 章

婚后
她和鐘先生的故事沒那麼多感情可講,他們只是場商業聯姻,領證那天也不過是他們的第三次見面。 鐘先生家世顯赫,是京圈頗有威望的名門,家業頗大,因此,他比較忙,在婚后的兩個月里,她很少能見到他。 他比她年長八歲,沉靜穩重,清雋淡雅,但她看得出來這是個冷情的人。
21.7萬字8 22963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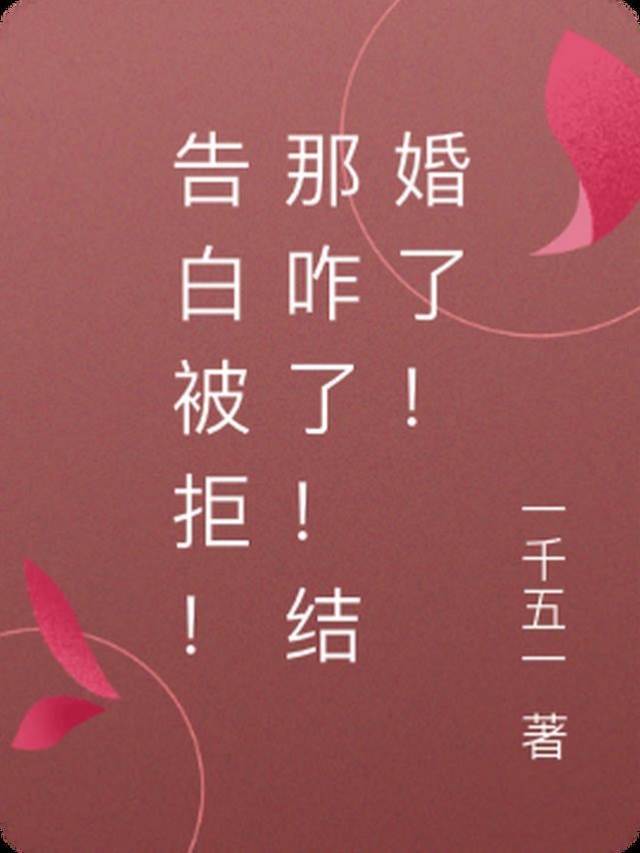
告白被拒!那咋了!結婚了!
【明著冷暗著騷男主VS明媚又慫但勇女主】(暗戀 雙潔 甜寵 豪門)蘇檸饞路遲緒許久,終於告白了——當著公司全高層的麵。然後被無情辭退。當晚她就撿漏把路遲緒給睡了,蘇檸覺得這波不虧。事發後,她準備跑路,一隻腳還沒踏上飛機,就被連人帶行李的綁了回來。36度的嘴說出讓人聽不懂的話:“結婚。”蘇檸:“腦子不好就去治。”後來,真結婚了。但是路遲緒出差了。蘇檸這麽過上了老公今晚不在家,喝酒蹦迪點男模,夜夜笙歌的瀟灑日子。直到某人提前回國,當場在酒店逮住蘇檸。“正好,這房開了不浪費。”蘇檸雙手被領帶捆在床頭,微微顫顫,後悔莫及。立意:見色起意,春風乍起。
26.9萬字8 9881 -
完結112 章

我怎麼這麼喜歡你啊
【溫吞軟妹×傲嬌拽哥】【開篇即大學/女暗戀/甜寵/大學男追女/雙潔1v1】 眾人皆知,陳江白是臨城一中的天之驕子,成績優異,長相出眾,是無數女孩子追求的對象。 林唯月默默望著耀眼的少年,將少女心思藏于盛夏。 高中畢業那晚,高三一班的同學玩得很放縱。 真心話大冒險環節,陳江白輸了一局,同學提出讓他給微信列表第四位女生發一句“我喜歡你”。 同時,默默在角落的林唯月手機響了一聲,上面赫然顯示著:我喜歡你。 只是一局游戲,沒有人放在心上,而林唯月卻偷偷歡喜了很久。 —— 后來,在大學的社團聚會上,游戲重演一遍,只是題目不同。 “給暗戀對象發一句‘我喜歡你’。” 京大皆知,陳江白性子狂妄高傲,喜歡就會轟轟烈烈,絕對不搞暗戀。 就在所有人以為沒戲的時候,陳江白默默給置頂的微信發了四個字過去。 包間瞬間炸了起來。 而林唯月喉間苦澀,借口離開包間。 聚會結束以后,醉意朦朧,無人注意樓梯間里曖昧相貼的男女。 陳江白俯身低語,“看到了嗎?” “我喜歡你。” —— “唯見江心秋月白。” 立意:總有人帶著滿懷真誠來找你,尋到一輪清冷明月。
23.3萬字8.09 1434 -
完結162 章

讓她當外室,她偏要另謀高枝
【溫軟清醒大小姐➕鮮衣怒馬少年將軍】【蓄謀已久➕甜寵➕男主超愛】 江綰是江家的獨女,家世富裕,有錢又美貌。 她方一及笄,便和陸家嫡子訂下婚事。 本以為是天作之合, 但春日宴上,她聽到陸景言親口說道: “商賈之女罷了,我豈會真的將她放在心上,玩玩而已。” 江綰這才驚醒,決定有多遠躲多遠! 她開始疏離陸景言,剛開始的時候,陸景言不以為然,以為這是江綰為了引起他注意,故意使的小把戲。 直到她成了謝行之的正妻,陸景言這才慌了…… 傳聞謝小將軍意氣風發,龍章鳳姿,是世間少有的好顏色,唯一的缺點就是不近女色。 但有時候一見鐘情就是這麼簡單。 譬如看到江綰的第一眼,他就連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PS:后續會加入郁漂亮和溫小梨的甜寵日常。 【男二上位➕蓄謀已久➕追妻火葬場不回頭】
29.5萬字8 168 -
完結346 章

致命牽引
溫和謙遜毒舌刺頭隨意切換醫生受VS撩神附體折騰自己非你不可總裁攻 1V1 這世上哪有什麼破鏡重圓,除非沒有破,除非沒有鏡,除非沒有圓。 莊念和顧言時隔七年的重逢發生在醫院里,顧言和他即將昭告天下的現任齊齊出現。 他親手送了莊醫生一張雕著郁金香的訂婚請柬,附在他耳邊說,“來參加我的訂婚宴吧,念念。” 原以為一切都成前塵往事,卻聽到顧言親口承認,險些送了命的車禍是他親自設計,只為了再見他一面。
69.9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