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等你》 第17章 chapter17
布桑城的天終于暗了下來,霓虹初上,夜流轉,高架上依舊川流不息,沈溥被霍明朗再次打擊,他臉有點差,覺得心煩。兩年來,無論做什麼,霍明朗永遠都是油鹽不進,一張冷淡側臉幾乎為他午夜夢回的現實場景。
手機鈴聲大作,他愈來愈心煩意,靠在地下車庫的門邊表淡淡,閃的名字時老宅那邊的電話,他用腳趾頭想想就知道是誰打來的。老爺子雖然脾氣急,但是為人出乎意料地堅持,沈溥知道他要是不接這個電話,老爺子能打到他手機沒電。
“喂!”依舊中氣十足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你在哪里?”
沈溥聽得出來,老爺子已經心不好,平素里沈溥這時候科打諢也就過去了,老人家麼還得哄著來。可是這一次,夜風的穿堂風從他耳邊呼嘯而過,每一次風聲幾乎要擊穿他的心臟,他腳下發寒,忽然覺得心累。
“在醫院。”
不清不楚的回答,老爺子還以為他又去附一院見霍明朗,頓時悶氣短,怒火冒了三層。立刻道:“現在、立刻、馬上帶天真去機場!”
沈溥有點不明不白,又不想跟宋天真牽扯,心里煩躁萬分:“爺爺,我現在很忙,沒時間去找宋天真,機場那邊你隨便派人就行,何必要我去?”
“你媽來了!你難道不去接麼!我看你是沉迷酒,腦子里都進水了,是吧?!”
早有消息要到,千呼萬喚始出來。沈溥卻有點興致缺缺,親生母親在他一兩歲的時候就與沈父離婚出國,他本沒有任何記憶,這個媽媽幾乎不存在過他的生命里。
聽到沈溥沒有回應,老爺子心里面失頂,他有預,即便兩家人再怎麼努力修復,兩個小輩估計還是要走上越來越遠的道路。
Advertisement
“小溥,你讀大學的時候還自己要去找你媽媽,現在既然來見你了,你就去機場接一下吧,畢竟濃于水。”
沈溥掛了電話,夜很好,星璀璨,他點了一支煙,在風中吸完最后一口,終于從車庫里開出車來。
現在他沈溥口口聲聲的媽媽不過是后母,這個事實是他在二十二歲的時候清清楚楚知道的。陳聰自從嫁給他父親之后,一直將沈溥看做自己小孩,百般寵人人都以為是沈溥的親生母親。所以當念大學的沈溥無意間得知他的親生母親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經不要他的事實之后,年輕氣盛的他兜里只揣了幾百金就獨自前往英國,他倒要問問到底是為什麼。
可是,當他從遠遠的地方看到一眼之后,他拿出僅剩的錢又立馬回了國,并且直奔拉斯維加斯,輸得只剩叮當響。
原因不過是,他看到笑容致的媽媽在拋棄他之后活得幸福滿,站在老外的邊一臉燦爛。
這個點,去機場的路依然很堵,沈溥什麼都沒有想,一直開了一個小時的路才到了布桑機場。英國的航班已經落地,沈溥在寬闊的機場大廳里環顧四周,終于發現了坐在人群中一聲灰系服的人。
跟他八年前驚鴻一瞥見到的不大一樣,現在臉上脂未施,有點顯老態,服也是一亞麻布,寬寬闊闊,人瘦了點。而在看書,很是安靜。沈溥沒有出聲,只是慢慢走了過去。
他終于站到面前,鎮定萬分,一點也沒有八年前的驚慌失措。
盧西幾乎在同一瞬間就抬起了頭,看了沈溥一眼,立刻出了他:“小溥。”
還笑了笑,很是溫和。沈溥神冷淡,只是朝點點頭,出手,就像是跟商業合作伙伴一樣:“你好。”
盧西倒不在意,站了起來,也握了握他的手:“你好啊。”隨手合上了書,沈溥瞄了一眼,竟然是一本佛經,他扯了扯角,倒還是有紳士風度的,隨后就拎起了盧西的所有行李。
一路無言,道路這會兒已經暢通,盧西住在市中心的一家五星級酒店,沒有訂到套房,也不甚在意,就住了一個大床房。沒有用服務生,沈溥拿著行李送到了門口,兩個人都還是沒有說話,只不過盧西輕輕笑了一下。
“再見。”沈溥首先告別,盧西抿了抿角,終于先抱了抱沈溥,笑起來,臉上的魚尾紋非常明顯,卻又有一種不一樣的味道。
“小溥,我們明天談談。”終于松開了他,最后拍了拍他的背,合上了門。
沈溥一臉平靜走到樓梯口,猛然間發怒,踹了一腳旁邊的垃圾桶泄憤。
與此同時,宋天真已經辦完出院手續,回了一趟湖東別墅。開始收拾東西,兩年來,是真的想把這里當做家的。冰箱里還有之前做的餛飩,因為是雙休日,家里一個人都沒有,往常這個時候,宋天真要開始換洗床單,明日一早別墅門口的晾架上就都是一水的白床單,風一吹,鼓起來,就像一頂頂飄在風中的帳篷。
日子過得安靜如同死水,宋天真將房子的里里外外又重新打掃了一遍。不知道做這些的意義在哪里,沈溥從來不在這里花費心思,而卻幾乎傾盡心。
大概是因為十分念舊,所以心里面還是有縷縷的不舍,但是還是得離開了。
沈溥中途去酒吧只喝了一杯酒之后就興致缺缺,錢樂樂倒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沈溥沒心思去聽,只模模糊糊知道說什麼又缺錢。他說了一句“你拿吧。”就隨手掛了電話。
酒杯見底之后,他就離開了酒吧,在市中心轉了一圈,回了湖東的別墅。
這套房子,是沈老爺子給的。沈溥在兩年里,卻回來幾十次。他今天也不知怎麼的,就想回來了。
宋天真在拖完地后,有點累,坐了會兒沙發,正當閉目養神的時候卻聽到了門鎖轉的聲音。幾乎第一時間,涌上心頭的卻是尷尬與難堪。
故意挑這個時候回來的,雙休日,學校也放假,沈溥應該要去見那個孩。以為能走得無聲無息。
避無可避,玄關傳來換鞋的聲音,很快,就在客廳里,沈溥一眼就看到了宋天真。
他進來的時候,發現家里地板好像是剛剛拖過,他腦子一轉就知道誰在這里。他到了客廳,看到地上的兩個大箱子時,一目了然。
“呵,這麼迫不及待。”幾乎第一時間,他的下意識反應就是打擊。
可是宋天真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笑瞇瞇地看著他,即便他說任何惡毒的話。這一次連看一眼都沒有看他,提了箱子,從包里掏出了鑰匙,輕輕擱在了茶幾上,就要走了。
經過他邊的時候,沈溥沒來由一怒火,一下子拽住了:“沒什麼好說的了?你這是給老子氣呢?跟你說話你沒聽見,是吧?”
宋天真只是側了側臉,一點表都沒有,神中似乎還有點不耐煩。
沈溥炸了:“喲,是不是門口還等著小白臉啊?這麼急啊,手斷了,他也不知道來給你拿一下行李啊?到底是外國人,懂什麼中華禮儀麼?”
他譏諷他惱怒,宋天真卻到無比心累,垂了垂頭,嘆了口氣:“你想得到什麼答案呢?”終于抬起頭來,沒有帶眼鏡,屋的襯得一雙大眼亮如星辰,如瓷,離得那樣近,臉上連一個孔都看不見。
好像比以前好看了點,沈溥不知怎麼腦子里浮現出這樣一個想法,難道是會打扮了?一想到這,他突然惡狠狠地說:“小白臉把你伺候得很好麼?!嗯?知道為悅己者容了?”
這些話就在耳邊,宋天真看了他一眼:“沈溥,你怎麼變這樣子了?”
“我變什麼樣子?!你知道我以前什麼樣子?!你特麼倒是說啊?”
面對已經盛怒的沈溥,宋天真松開了拉住皮箱的手,就在一瞬間,“啪”一下打了他一個掌。
沈溥一點也沒有準備,又用力狠力,腦子“嗡”的一聲,沈溥幾乎發昏,臉上頓時出現了紅印。他聽到宋天真冷淡的聲音回響在耳邊:“這樣你夠清醒了麼?可以放手讓我走了吧。”
他早已松開了拽住的手,宋天真皮箱的聲音在整個屋子里回想。
“他媽的。”沈溥暗咒一聲,忽然長一聲,一覺踹開了宋天真的手上的行李箱。他很快就單手重新拉住了宋天真,看到驚慌失措的臉時,他心里終于舒坦了點。
不知他用了多大的勁兒,皮箱已經被踢裂,里面的服灑落在潔如新的地板上。
沈溥大概被打昏了頭,一下子吻住了宋天真的。
猜你喜歡
-
完結367 章

前妻,敢嫁別人試試
三年前,她在眾人艷羨的目光里,成為他的太太。婚后三年,她是他身邊不受待見的下堂妻,人前光鮮亮麗,人后百般折磨。三年后,他出軌的消息,將她推上風口浪尖。盛婉婉從一開始就知道,路晟不會給她愛,可是當她打算離去的時候,他卻又一次抱住她,“別走,給…
95.4萬字8 74666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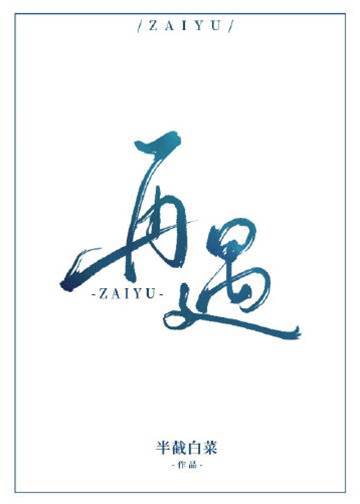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8890 -
完結641 章
重返七零之空間小辣妻
末世大佬唐霜穿到年代成了被壓榨的小可憐,看著自己帶過來的空間,她不由勾唇笑了,這極品家人不要也罷; 幫助母親與出軌父親離婚,帶著母親和妹妹離開吸血的極品一家人,自此開啟美好新生活。 母親刺繡,妹妹讀書,至于她……自然是將事業做的風生水起, 不過這高嶺之花的美少年怎麼總是圍著她轉, 還有那麼多優秀男人想要給她當爹,更有家世顯赫的老爺子找上門來,成了她的親外公; 且看唐霜在年代從無到有的精彩人生。
121.5萬字8 68733 -
完結2314 章

第一名媛:奈何嬌妻太會撩(盛莞莞凌霄)
“我愛的人一直都是白雪。”一句話,一場逃婚,讓海城第一名媛盛莞莞淪為笑話,六年的付出最終只換來一句“對不起”。盛莞莞淺笑,“我知道他一定會回來的,但是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父親車禍昏迷不醒,奸人為上位種種逼迫,為保住父親辛苦創立的公司,盛莞莞將自己嫁給了海城人人“談虎色變”的男人。世人都說他六親不認、冷血無情,誰料這猛虎不但粘人,還是個護犢子,鑒婊能力一流。“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麼?”“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說你不好,那個人依然把你當成心頭寶。”
426.6萬字8 397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