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屋暗燈》 第2章
第二天起來的時候,保姆已經做好了早飯,宋謹吃過之后,特意在樓下等了會兒,但宋星闌似乎毫沒有要下樓吃早飯的跡象。
宋謹于是端了早飯上樓,在房門外站了一分多鐘,他才有勇氣開口。
“星闌,給你拿了早飯,再不吃的話可能會冷了。”
沒有回應,宋謹雙手拿著東西沒法敲門,于是他又問:“你還在睡嗎?我進來把早飯放你桌上可以嗎?”
仍然得不到回答,宋謹于是彎下腰,用手肘下了門把,慢慢地推開門。
他以為宋星闌還在睡,但是床上并沒有人。
接著洗手間的門被打開,宋星闌從里面走出來,面容上還帶著初醒時的倦意。
一見到宋謹,他的臉上幾乎眼見著就浮現起厭惡的怒氣,眉頭皺:“誰讓你進我房間的?”
“我……”宋謹微微抬手,示意自己是來送早飯的。
“在那假惺惺。”宋星闌邁了幾步過來,不由分說地往宋謹肩上推了一把,“滾出去,別來我房間!”
宋謹毫無防備地被他一推,手上的熱粥晃了出來,灑在了手背上,他倒吸了口氣,忍著灼燙咬牙將碗放到一旁的柜子上,這才沒有倒一地。
“趕滾!”宋星闌指著走廊,聲音是抑過后的冷怒,“別讓我看見你!”
“好。”宋謹說。
他重新端起粥,走出了房間。
房門被砸上,宋謹走下樓,臉上沒什麼表。
他理解宋星闌,正如他年復一年地理解母親那樣。
小時候和媽媽一起拋棄了自己的人,在十多年后重新回到這個家,宋星闌的反應事出有因,畢竟親淡薄到可以忽略不計,自己如今只能算是個不速之客。
雖然當時的宋謹才七歲,別無選擇,可現在母親去世了,宋星闌的緒發泄對象也只有宋謹而已。
Advertisement
他是宋向平的親兒子,是宋星闌的親哥哥,現在卻不得不變這副寄人籬下忍氣吞聲的樣子,只能說命運流轉,逃不掉的只有他一個人。
宋星闌之后就出了門,到晚上都沒再回來,晚飯時宋向平讓司機來接宋謹出去吃飯,宋謹坐在宋向平和一個陌生人的對面,一言不發地吃著菜。
“星闌說跟朋友在外面玩,就不過來一起吃了。”宋向平這麼解釋道。
其實宋謹都懂,宋星闌只是不想看見自己。
好在馬上就開學了,宋謹申請了住校,高三生兩星期回家一次,他可以盡量減自己在宋家出現的頻率。
開學的那天早上,宋向平親自陪宋謹去學校。
兩人正站在客廳里,宋星闌下了樓,一利落的球服,手上拎著網兜,網兜里的籃球上寫滿了簽名。
他看也沒看宋謹一眼,面無表地往大門走。
“還有兩天就開學了,初三的人了,就知道瘋玩兒,多跟你哥學學。”宋向平說。
“他也配?”
宋星闌頭也不回,只留下執拗的背影和不屑的反駁。
宋向平無奈地看向宋謹,宋謹只是抿了抿:“沒事,他還小。”
高三過得尤其快,黑板右上角的高考倒計時不知疲倦地變著,宋謹一頭扎在題冊和考卷里,連放假都基本不回家,窩在宿舍沒日沒夜地學習。
他想拿出盡量優異的績,一是不想讓宋向平覺得他無能,二是,這或許確實是改變他命運的唯一途徑了。
他知道自己現在的境,表面上他有富有的父親和優越的住所,實際上他離無家可歸也只有一線之差而已。
在過去的十年里,哪怕住的地方再狹小仄,吃的東西再平淡無味,宋謹也從未有過這樣的想法,因為他和母親相依為命,不可或缺。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沒有人把他當支柱,沒有人對他掏心掏肺了。
一整年下來,除了寒假,宋謹回家的次數得可憐,與宋向平和宋星闌見面的次數也就屈指可數。
就連除夕那天,都是宋謹一個人在家過的,宋星闌去和朋友們年,宋向平在微信上給宋謹轉了筆錢當做歲紅包,然后說自己今天不回來,讓宋謹出去玩。
宋謹一個人坐在漆黑的臥室里,手里著與母親的合照,他看向窗外遠高樓的輝煌燈火,在十二點的鐘聲敲響之際,他輕聲說:“新年快樂,媽媽。”
凌晨三點,房門外突然傳來一聲沉重的響。
宋謹睜開眼,他聽到宋星闌的低罵聲。
他打開房門,宋星闌就坐在門邊,上傳來濃重的酒氣。
宋謹沒有去扶他,宋星闌不是第一次喝醉了,在宋謹為數不多的回家日子里,他撞見過宋星闌喝得爛醉,好幾次。
剛開始時宋謹會急著去扶他,然而下場都是被宋星闌一把推開,然后被指著鼻子罵,什麼難聽罵什麼,仿佛宋謹并不單純只是宋謹,而是所有宋星闌看不慣的人的合集,要被他放肆地發泄怒氣。
才初三,宋謹都想不通,現在的青春期男生都像宋星闌一樣麼?
“起來。”宋謹說,“你房間在隔壁。”
房子里一個燈都沒有開,他們互相看不見表,宋謹只聽見宋星闌有些重的息。
“滾開,要你管?”
宋謹平靜地說:“我沒有要管你,你撞到了我的房門,把我吵醒了。”
“嫌吵就滾出去啊!”宋星闌的聲音突然響了一些,“在這膈應誰?”
簡直無法流,宋謹嘆了口氣:“我說什麼都是錯的。”
“對。”宋星闌跌撞著站起來,湊到宋謹面前,“知道為什麼嗎?”
宋謹靜靜地等著他的下文。
宋星闌側頭靠近宋謹的耳朵,低聲道:“因為你是個同,所以你說什麼我都覺得惡心。”
黑暗像是變了千噸重的實,一塊接一塊地朝宋謹狠過來,他在如雷的心跳中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整個人有種天翻地覆的眩暈,仿佛被宋星闌上的酒氣侵染了五臟六腑。
見宋謹沒有反應,宋星闌笑起來:“被我說中了?”
“你喝多了。”宋謹勉強出一句話來,嗓音卻發啞,虛浮到極點。
“你跟那男的的接吻照我都有,裝什麼裝?”宋星闌的嗓音里是變聲期還未結束的低沉,“然后呢?那天你們接著去干了什麼?”
宋謹在初二的時候意識到自己的向,他從不覺得這是什麼難以啟齒的病癥,但這個世界也不值得他對誰道出這個事實。他沒想過任何關于的事,他知道之后的路會很難走,他只希能夠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僅此而已。
那個男生和他同屆,因為宋謹是轉學生,相貌又出,白皙秀氣的一張臉,多會引起些注意,對方明里暗里地試探過宋謹許多次,最后宋謹不堪其擾,答應了 [[他的邀約,準備和他在校外說清楚。
誰知道拒絕的話還沒說出口,對方就湊過來在他的臉上親了一下。
宋謹當時只是了自己的臉,說:“以后別來煩我,我沒空跟你浪費時間。”
對于宋謹來說,無論是還是娛樂,全部都是浪費時間,此刻的他沒有資本去消耗。
他沒想到會被宋星闌目睹,他最不敢啟齒的,宋星闌竟然是第一個發現的。
“你跟蹤我?”宋謹死死地摳著自己的手心,發著抖問。
“別他媽自作多了,我就是恰好路過,順手拍了個照。”宋星闌“嘖”了一聲,往后退了兩步,仿佛在躲避什麼臟東西,他說,“宋謹,你可真惡心。”
他從不哥,而是連名帶姓地宋謹的名字。
宋謹知道一個異取向的男生可能不會輕易理解自己這樣的人,可他沒想到宋星闌才那麼小,就會對同抱有這樣的惡意。
隨后他想到,宋星闌未必是惡心同,只不過剛好眼前站著的是宋謹+同,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加深了厭惡。
“對,我很惡心。”宋謹看著面前一片黑暗里宋星闌的模糊形,咽了一下嚨,“影響到你了,真對不起。”
“影響我?你以為你是誰?”宋星闌嗤笑,“管好你自己的破事,別再丟人現眼。”
宋謹未置一詞,退回房間關上了門。
他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破事需要心,他只是很想從這個家里逃離,太想了。
他也不恨宋星闌,他只是突然很恨母親,在除夕過后的幾個小時,他在想,為什麼母親不能多堅持幾年,為什麼母親不肯再讓他覺得自己被需要,為什麼他要被安排來面對這樣的弟弟。
宋謹寧愿自己和宋星闌一輩子都不再見,也不想要跟他對立站在如今的境地。
猜你喜歡
-
完結1257 章

頂不住了!前夫天天把我摁墻上親
盛相思心懷嫉妒,將丈夫身懷六甲的白月光推下樓,致使她胎死腹中血流成河。江城流言四起,盛相思驕橫跋扈,心腸歹毒。爲給白月光出氣,丈夫將她丟到了國外,不聞不問、任其自生自滅。四年後,盛相思回到江城。她和傅寒江一笑泯恩仇,從此相逢是陌路。再見面,盛相思成了舞場頭牌,無數男人爲求見她一面,一擲千金求而不得。傅寒江坐不住了。他堵住她,“生活這麼困難,不如回到我身邊?”盛相思微微一笑,“傅總,想約我?請領取號碼牌,後面排隊,謝謝。”
206.9萬字8 51354 -
完結252 章

離婚后,我虐前夫千百遍
暗戀江時羿的第十年,顧煙夙愿得償,成了江太太。她以為,他們會一生一世一雙人,直到他的白月光回國。那一夜,她被人所害陷入危難,滿身鮮血,求助于他,卻聽到電話那端女人的嬌笑。暗戀他十年有余,離婚轉身不過一瞬間。后來,江時羿在每個深夜看著她的照片,數著她離開的時間,從一天一周,到一月一年。直到經年后再重逢,他孑然一人,眼尾泛紅地盯著她,而她領著軟軟糯糯的小姑娘,泰然自若同他介紹“我女兒。”
49.7萬字8.18 25335 -
連載485 章

霍少你被騙了,夫人的身份是假的
一場逃婚,她從美若天仙的海城首富千金偽裝成了又土又醜的鄉巴佬。剛到京城的第一天,就招惹上了京城第一家族繼承人霍煜琛,那是一個今人聞風喪膽的男人,大家都稱他活閻王,做事六親不認,冷血無情、果敢狠絕。他為了氣自己的父親娶了她,整個京城的人都知道他娶了個醜的,殊不知她卸下妝容後美若天仙。婚後的生活她過得‘水深火熱’。不僅每天要麵對一個冰塊臉,還要時刻隱藏自己的身份,她每天都想著離婚,想著擺脫這個男人。 某一天,當她的身份曝光,她逃了,他慌了,他瘋了般滿世界找她……
87.1萬字8 7098 -
完結10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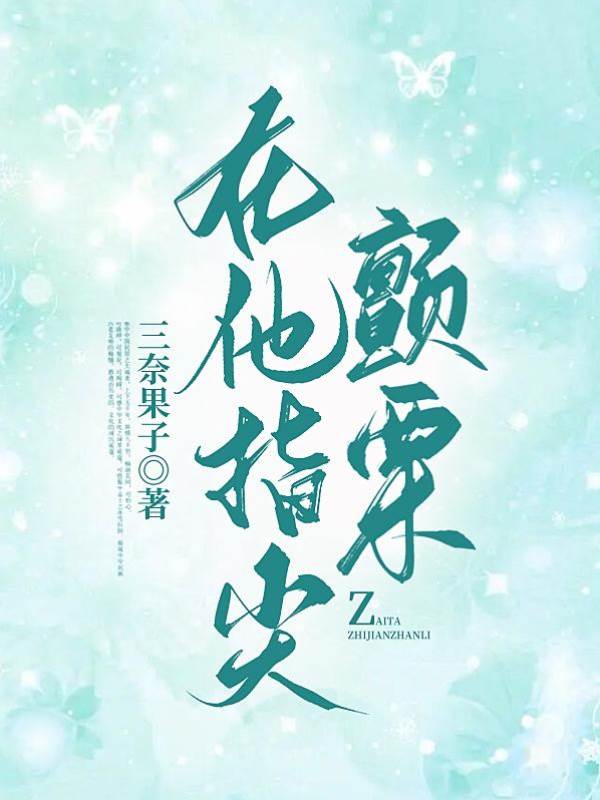
在他指尖顫栗
【美豔釣係旗袍美人VS清冷矜貴貧困大學生】【欲撩?甜寵?破鏡重圓?雙潔?暗戀?豪門世家】他們的開始,源於荷爾蒙與腎上腺素的激烈碰撞她看上他的臉,他需要她的錢他們之間,隻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蘇漾初見沈遇舟,是在京大開學典禮上,他作為學生代表正發表講話他一身白衫長褲、目若朗星、氣質清雅絕塵,似高山白雪,無人撼動驚鴻一瞥,她徹底淪陷人人說他是禁欲的高嶺之花,至今無人能摘下可蘇漾不信邪,費盡心思撩他,用他領帶跟他玩緊纏遊戲“沈會長,能跟你做個朋友嗎?”“蘇漾,”沈遇舟扣住她亂動的手,“你到底想幹什麽?”“想跟你談戀愛,更想跟你……”女人吻他泛紅的耳朵,“睡、覺。”都說京大學生會主席沈遇舟,性子清心冷欲,猶如天上月可這輪天上月,卻甘願淪為蘇漾的裙下之臣然而蘇漾卻突然消失了多年後,他成為醫學界的傳奇。再見到她時,他目光冷然:“蘇漾,你還知道回來?”房門落鎖,男人扯掉領帶,摘下腕表“不是喜歡跟我玩嗎?”他親吻她,偏執且病態,“再跟我玩一次。”“沈遇舟,對不起。”男人所有不甘和怨恨,在這一刻,潰不成軍他拉住她,眼眶發紅,眼裏盡是卑微:“別走……”沈遇舟明白,他是被困在蘇漾掌中囚徒,無法逃離,也甘之如飴
20.8萬字8 29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