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明今夜想你》 第13章 嫌惡
馳厭沒自己被打的臉,也不再看姜穗,回頭對朱峰爸爸說:“滿意了就聽我講。”
“馳一銘,做沒做?”
馳一銘頓了頓:“沒有。”
馳厭說:“我弟弟說沒有,你們說有,證據呢?”
朱峰爸爸說:“有個小姑娘說看見了馳一銘回教室。”
他一指那個小姑娘陳,陳早就被這個陣仗嚇怕了,也后悔出來指證馳一銘。
陳怯怯地站起來,正好對上馳厭的眼神,清清冷冷的眼,臉上一個通紅的掌印。同學們說得對,馳厭和馳一銘一點都不像。
馳厭又高又瘦,點墨般的眸寂冷,眉骨還有一道可怖的疤。
不言不語,讓人想到了巍峨的山。剛剛那一掌打得那麼響,馳厭的臉幾乎立馬腫了起來,可是他連臉都沒變。
陳連連搖頭,快要哭了:“我也不知道,我沒看清楚。”
朱峰爸爸怒道:“你這小姑娘!”
馳厭說:“你沒有證據指控馳一銘,手打人卻讓所有人看見了。我對你兒子發生的一切表示不幸,但是朱先生,放干凈點。”
朱峰爸爸還想上前打他,班主任連忙拉住。
這下子把朱峰關在廁所的不管是不是馳一銘,馳厭當著所有人的面挨了這一掌,都了朱峰爸爸理虧。
這件事最后只能揭過。
朱峰出事沒人負責,班主任為了安朱峰爸爸,在班里號召大家投錢送心,為朱峰買營養品。
晚上回去經過二橋下面,馳一銘腳步僵了僵,馳厭腫著半邊臉在修車。
看見馳一銘過來,馳厭并不理他,等把托車停好了,馳厭從兜里拿出五張十塊的遞給他。
“給朱峰的。”
馳一銘悄悄看看哥哥淡然的臉,突然不敢接這錢。
Advertisement
錢上沾了汽油,馳厭不在意地,塞進弟弟口袋里。
“哥,你沒有問的嗎?”
為什麼不好好讀書?為什麼要惹事?
他哥可不傻,兩兄弟沒爸媽活到現在都靠馳厭。
馳厭看他一眼,漆黑的眸有種煙灰般的淺淡,仿佛是不是馳一銘干的都不重要。
有那麼一瞬,馳一銘覺得自己從來沒有看懂過哥哥。
馳厭從來不為和疼痛哭泣,明明世上一切東西都能彎他的脊梁,他也習慣了向生活低頭,可是馳厭卻又平靜到像一灘死水。如果不是馳厭養了自己那麼多年,馳一銘甚至會懷疑是不是自己這個弟弟在他心中也毫無分量。
馳一銘接過錢。
這一年他真想知道,有一天哥哥為一件事在意瘋狂,究竟會變什麼樣。
姜穗也想知道,為什麼小混蛋馳一銘闖禍要馳厭承擔。
馳厭挨那一掌,隔著窗戶似乎都聽見了那種清脆的聲音,可是他臉變也沒變。姜穗心想,這世上能讓馳厭容的可能只有他的“白月”梁芊兒了。
盡管這一年十三歲的梁芊兒一點也瞧不起他。
那個掌要是落在自己臉上,估計角都會流。
姜穗吃了飯,把目落在小斑鳩上。
小斑鳩親昵地沖了兩聲。
等不到過年了。
姜穗把籠子取下來,又用布包好出了門。
在榆樹下等了好一會兒,姜水生催促道:“穗穗,起風了,還在外面做什麼呢?”
“爸爸,再等一下,我很快回來。”
天黑之前,大院兒回來一個清瘦的影。姜穗如今不太怵他,可是心中依然敬重。
揮了揮手:“馳厭哥哥。”
馳厭淺淡的眸安安靜靜落在上。
小姑娘蹲下來,揭開一層灰褐的布,出了里面的籠子。
籠子里面,一只呆頭呆腦、油水的斑鳩正打量著他。
這麼冷的天氣,小姑娘穿了一米棉,小斑鳩和都神奕奕的。
說:“這個還給你。”
馳厭薄在冷風中沒有,便顯得格外寡淡,他半邊臉依然沒能消腫,聞言點頭:“嗯。”
真是奇怪的人,姜穗忍不住看他一眼。他也不問為什麼還給他,或許是不是不喜歡,把籠子給他,他就接著了。
小斑鳩到了馳厭手上,終于不是那副呆懶樣,開始不安地踱步。
馳厭本來以為不喜歡。他從沒送過誰禮,人家不喜歡了不要也是正常的。
可是小姑娘眼地看著胖乎乎的小斑鳩,分明是很喜歡的樣子。
馳厭沉默了一下,又把籠子遞給。
姜穗被他看穿意圖,尷尬又怯:“不不,我不能繼續喂它了,我明年就初中了,你拿去……吃、吃了吧。”
馳厭微抿角。
姜穗抓著那塊灰褐的布,仰頭對上年眼睛。
馳厭這才發現,比一年前好了許多,臉上沒那麼傷痕了。棉外著一小片頸部,白得像牛一樣。
大院里孩子就屬最白,父親很。
說話時喜歡看人眼睛的人,大多很坦誠。
馳厭錯開小姑娘的桃花兒眼,打開籠子,小斑鳩笨拙地走到籠子口,撲騰著翅膀飛走了。
姜穗目瞪口呆。
馳厭把籠子還給:“拿著,回家吧,不能養就放了。”
他還沒喪心病狂到要吃小姑娘寵的地步。
馳厭走了幾步,不經意回了個頭。
彼時十一月,這年冬天還沒徹底到來。姜穗還站在那里,著天邊越飛越遠的小斑鳩,出松了口氣的表。
孩小小一只,天幕映在眼中,那雙瀲滟至極的桃花眼向下彎一個月牙兒,眼尾微翹,分明好看極了。
放走了小鵪鶉,姜水生雖然惋惜,但是也能理解。
他看著吃飯香甜的姜穗,眉眼出了一輕松的笑意:“穗穗啊,爸爸認識一個朋友,他說可以寒假帶你去C市第一人民醫院看病,那里有專家會診,也許可以醫好你這種況。等你考完試爸爸就帶你去。”
姜穗點點頭,也很高興,走路都走不穩實在太不方便了。
而且這次看病真正治好了自己這個疾病。
專家們沒有見過姜穗這種案例,于是開了一個研究小組探討病例,出于特殊,治療反而很便宜。
沒多久就六年級期末考試了,姜穗坐在座位上吃力地寫卷子。
上面的題基本都會,可是就是寫不完,行為跟不上思維,就是這麼難。馳一銘早就寫完了,回頭看了眼,出嘲諷的笑意。
姜穗也不理他,一直戰到了卷最后一秒。
想到能治病,心里松快不用摔倒了,可看著馳一銘又覺得危機重重。
然而轉瞬姜穗想,曾經對馳一銘不錯,所以他很喜歡自己,可是這次并沒有,話都沒有和他說,馳應該還不至于這麼犯賤。
這麼一想,姜穗松了口氣。
過年前,除了姜穗要去C市看病,還發生了一件大事。隔壁的陳彩瓊和單漢茅麻子結婚了。
姜穗被帶去吃喜酒的時候,還有種不真實的覺!
原來時間真的不知不覺快兩年了。
刻薄的陳彩瓊沒有為自己的繼母,嫁給了其他人。
陳彩瓊穿著紅裳,遠遠瞪了姜水生和姜穗一眼。
大院兒里搭了頂棚擺了宴席,幾乎全大院兒的人都在,瞧著倒是非常熱鬧。姜穗和梁芊兒孫小威他們坐在一桌,趙楠看見了也連忙跑過來,于是這一桌干脆坐滿了小年。
馳厭早早下了工,和馳一銘走在最后面。
馳一銘說:“哥,那邊有位子,我們坐那里。”
孫小威之前給馳一銘買了一年菜,心里的火氣沒發。這兩年孫小威長高了不,也意識到了自己可是二代,為什麼要怕馳厭這種小雜碎!
于是本來的兩個空位被他一橫,孫小威下一抬:“沒位子了!哪兒涼快哪兒待著去!”
馳一銘臉上的笑意沒了:“孫小威,你!”
馳厭冷冷掃了孫小威一眼。
姜穗小臉木著,簡直想給孫小威點三炷香。怎麼什麼人不能惹孫小威偏偏要惹!
趙楠笑嘻嘻地看熱鬧,一點也不為自家“表哥”著急。
梁芊兒不聲地看了眼馳厭和馳一銘,今天穿了去年那件雪白的棉襖,領口一圈絨襯得漸漸長開的容清麗。馳厭上沾了沒洗干凈的機油,看著就惡心死了。兩個空位就在邊,也不大樂意,于是說:“我看見那邊還有位置呢,你們過去坐吧。”
姜穗本來不想管,可是喜宴人本來就多,許多人探頭探腦往這邊看。
被人孤立的滋味并不好,清楚極了。
于是輕輕拍拍孫小威的:“放下來,你爸爸在看呢。”
孫小威狐疑地看了一圈,自己爸爸明明在和人說話,沒有看過來。
姜穗明亮的眼睛帶著溫和的笑意,糯糯的嗓音慢吞吞道:“孫小威,你最大方了,放下來吧,我給你倒飲料喝。”
孫小威斜了一眼,他喜歡聽好話,心里有些滋滋,于是哼了一聲,不不愿把放下來了。
馳厭和馳一銘這才有位子坐。
馳一銘挨著孫小威,馳厭挨著梁芊兒。
梁芊兒不高興極了,到底還不懂得掩飾自己緒,嫌惡地搬起板凳,往趙楠邊挪了挪,仿佛到馳厭就覺得臟似的。
馳一銘臉了。
馳厭也抿了抿。
姜穗心想,這可沒有辦法了。也沒想到原來曾經的梁芊兒這麼排斥馳厭,明明后來看到馳厭恨不得笑出一朵花兒來。
這樣一想,又覺得人真是奇妙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221 章

報告爹地:媽咪要逃婚
夏心妍嫁了一個躺在床上昏迷三年的男人,她的人生終極目標就是成為一個超級有錢的寡婦,然後陪著她的小不點慢慢長大成人。 「霍總,你已經醒了,可以放我走了麼?」 「誰說的,你沒聽大師說麼,你就是我這輩子的命定愛人」 一旁躥出一個小身影,「媽咪,你是不是生爸比氣了?放心,他所有的家當都在我的背包里,媽咪快帶上我去浪跡天涯吧」 男人深吸一口氣,「天賜,你的背包有多大,還能裝下爸比麼......」
193.5萬字8 13052 -
連載1504 章

夫人她A爆全世界
【甜寵,重生,虐渣,馬甲,團寵】“還逃嗎?”秦初使勁搖頭:“不逃了。”放著這麼好看的男人,她再逃可能眼睛真有病,前世,因錯信渣男賤女,身中劇毒鋃鐺入獄,自己最討厭的男人為替自己頂罪而死,秦初悔不當初,重回新婚夜,秦初緊抱前世被自己傷害的丈夫大腿,改變前世悲慘人生,成為眾人口中的滿級大佬。人前,秦初是眾人口中秦家蠢鈍如豬的丑女千金,人后,秦初是身披各種馬甲的大佬,某天,秦初馬甲被爆,全
135.4萬字8 16222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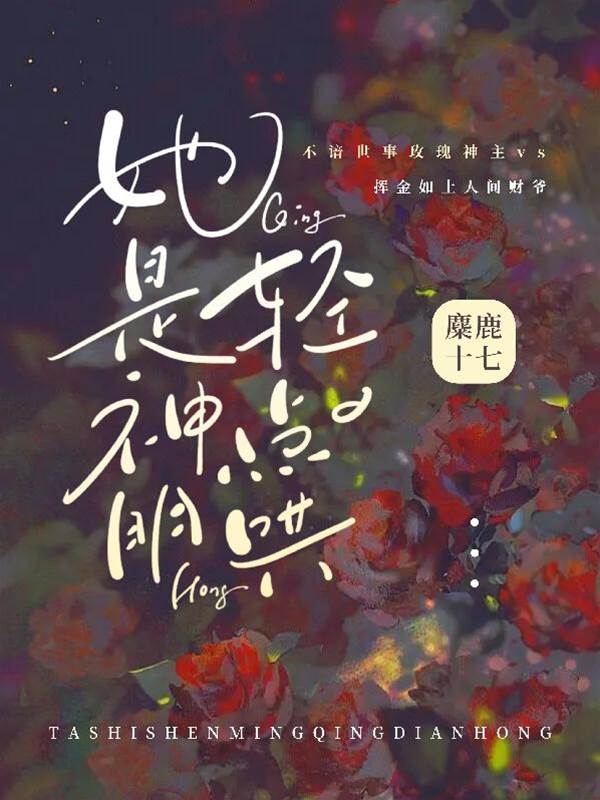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