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嬌》 第26章 相看
夫妻倆高高興興地說著己話,大伯母王氏拿了新鮮上市的水梨過來,說是給鬱棠嘗嘗的,妯娌間不免說起鬱棠的婚事,知道佟掌櫃要給鬱棠保,王氏喜道:“定了日子,你記得上我,我也去看看。”
陳氏笑道:“還不知道能不能?只是去探探口風。”
王氏不以為然地笑道:“就憑我們家阿棠,只有挑別人的,哪有別人挑的。”
陳氏顯然對這門婚事有所期盼,連聲笑著說“借你吉言”。
或者真的是有緣分,佟掌櫃那邊很快就回了信,說衛家的次子、三子都和鬱棠年紀相當,隨鬱家挑。
王氏聽了笑得合不攏,對鬱博道:“我看這衛家都是實在人,說不定真是一門好親事呢!”
鬱棠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何況關系到的終大事,鬱博雖然沒有親自去問,但也很關心,聞言仔細地叮囑王氏:“你年紀比弟妹大,行事又是最穩當妥帖的,阿棠的這件事,你要好好地看看,什麼都是次要的,這秉第一要。家和萬事興。要是脾氣不好,再有本事、長得再面、為人再老實,也過得不舒服。”
“知道了,知道了!”王氏說起這件事,想起了自己的兒子,坐在鏡臺前梳頭的時候和鬱博道,“遠兒的婚事,你是不是也拿個主意。”
王氏之前想和娘家兄弟結親的,誰知道那孩子長到八歲的時候夭折了,王氏嚇了一大跳,去廟裡給鬱遠算命,都說鬱遠不宜早結親,他的婚事才一直拖到了現在。
鬱家子嗣單薄,向來把孩子看得重。鬱博也不敢隨便拿主意,道:“我和惠禮商量了再說。”又問王氏,“是兩個孩子都相看,還是定下了相看誰?”
Advertisement
王氏笑道:“弟妹的意思,次子比阿棠大兩歲,年紀大一些,懂事一些,就相看他們家次子。”
鬱博點頭,不再議論此事。
鬱棠這邊事到臨頭了,心裡卻有些忐忑不安起來。
自己的婚事,就這樣定下來了嗎?
不知道那個衛小山的人長什麼樣子?是什麼格?怎麼看待這門親事?
長長地歎了口氣,自己告訴自己,衛家誠意十足,衛家的長子聽說還考上了生,能結這樣一門親事,也算是門當戶對了,應該很滿意才是。但想的是一回事,心卻不的控制,始終蔫蔫的,提不起興致來。
到了相看的日子,陳氏請了馬秀娘來陪鬱棠。
因相看的地方定在了昭明寺,鬱家除了要雇車馬,準備乾糧,還要在昭明寺定齋席,請中間牽線的人……陳氏忙前忙後的,鬱棠又有心遮掩,陳氏沒有發現鬱棠的異樣,馬秀娘卻發現了。
找借口把在屋裡服侍的雙桃打發出去,拉著鬱棠的手說著悄悄話:“你這是怎麼了?不滿意?還是有其他的……念想?馬上要相看了,若是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好,這件事十之八、九就定下來了。你要是有什麼覺得不好的,趁著現在木沒舟,早點說出來。一旦這親事定下來了,你就是有一千個、一萬個想法,可都得一輩子給我在心裡了。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會害人害己的。”
馬秀娘始終不相信鬱棠面對李竣這樣不論是模樣還是誠意都讓人挑不出病的人一點都不心。
鬱棠朝著馬秀娘笑了笑,只是不知道,的笑容有多勉強。
“我知道。”低低地道,“我姆媽和阿爹也不是不講理的人。我只是覺得,就這樣嫁了……”
有點害怕。
想當初,李端和顧曦,不知道多人羨慕。就是,在沒有發現李端那些下流心思之前,不也覺得他們夫妻喝酒行令、畫眉添香,是一對比翼鳥嗎?
馬秀娘不相信,但怕自己說多了引起鬱棠的反,以後有什麼話都不跟說了,像之前胡鬧似地跑去昭明寺會李竣,惹出更多的事端來就麻煩了。還不如看著點,別讓鬱棠出什麼事。
“大家都一樣啊!”索順著鬱棠的話安鬱棠,“你看我,和章公子也算得上是從小就認識了,可真的說了親,定下了婚事,我心裡還不是一直在打鼓。生怕這裡做得不好,那裡做得不好。等過些日子,自然就好了。”
鬱棠笑著謝了馬秀娘,好像被的話安到了,實則心裡卻更是不安了。
的害怕,和馬秀娘所說的害怕還不一樣。
不怕環境改變了,也不怕自己嫁人之後會過得不好,怕的是,不想嫁給這個人……
念頭閃過,鬱棠愣住了。
,原來是不想嫁給這個人嗎?
可這個人有什麼不好的?
大家不都是這樣的嗎?父母之命,妁之言。門當戶對的,就能結親了。
衛家還把腰彎到了地上,兩個兒子任他們家選,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想找什麼樣的人?
鬱棠被自己嚇了一大跳。想和馬秀娘說說,卻又不知道從何說起。
陳氏已經在外面催們:“你們收拾好了沒有?馬車到了,我們還要趕到昭明寺用午膳呢!”
馬秀娘忙應了一聲,幫著鬱棠整理一番就出了門。
鬱棠再多的話都被堵在嗓子裡。
昭明寺還是像從前一樣高大雄偉,可看在此時的鬱棠眼裡,卻覺得它太過嘈雜浮華,沒有鎮守一方大鎮的威嚴和肅穆。
或許是因為心境變了,看什麼的覺也變了。
在心裡暗暗琢磨著,被陳氏帶去了天王殿。
來陪著鬱棠相看的人還不,除了鬱文兩口子,眷這邊是馬秀娘和王氏,男賓是佟掌櫃和鬱博、鬱遠。
按照和衛家的約定,兩家各自用過午膳之後,大家就去遊後山,然後在後山的洗筆泉那裡裝著偶遇的樣子,兩家的人就趁機彼此看上幾眼。
鬱棠心事重重地用了午膳,和馬秀娘手挽著手,跟在陳氏和王氏的後,往洗筆泉去。
為了不喧賓奪主,馬秀娘今天穿了件焦布比甲,著鎏銀的簪子,戴著對丁香耳環,非常的樸素。鬱棠則穿了件銀紅的素面杭綢鑲柳綠掐牙邊的褙子,梳了雙螺髻,了把鑲青金石的牙梳,華麗又不失俏皮。
衛家的人在人群中一眼就看見了鬱棠。
衛太太等不到兒子表態就已非常滿意了。
待回過頭去看兒子,兒子已經滿臉通紅,抬不起頭來。
衛太太忍不住就抿著笑了起來。
鬱家的人也一眼就看見了衛小山。
他穿了件還帶著褶子的新裳,高高的個子,材魁梧,人有點黑,但濃眉大眼的,敦厚中著幾分英氣,是個很神的小夥子。看鬱棠的時候兩眼發,亮晶晶的,著讓人一眼就能看明白的歡喜。不要說鬱家的人了,就連來時還有點不快的鬱棠,都對他心生好,飄忽的心頓時都變得安穩了幾分。
若是這個,倒也還好。
在心裡想著,不仔細地打量了一眼衛家的人。
衛父一看就是個沉默寡言的莊稼人;衛太太明外,目卻清正;衛家的長子和衛小山長得很像,只是眉宇間比弟弟多了幾分儒雅;衛家的長嫂也不錯,清秀溫和,說起話來慢條斯理的,看著像是讀過書的。還有個相陪的,是衛太太娘家嫂子,看著也是個明能乾的。倒是衛家跟過來的老五衛小川,剛滿十歲,看到鬱棠之後就一直有些氣呼呼的。兩家人說話的時候他落在大家的後,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折了一條樹枝,一會兒掃著路邊齊膝的雜草,一會兒打打邊的樹枝,時不時地弄出些靜來,打斷了兩家人說話的興致。
衛太太看著直皺眉,把長子過去低聲吩咐了幾句,衛家的長子衛小元就沉著臉將衛小川拎到了旁邊,低聲斥責了他幾句,衛小川竟然發了脾氣,一溜煙跑了。
鬱家的人看著,有些奇怪。
衛太太應該一直觀察著鬱家人的臉,忙向陳氏解釋道:“這孩子是最小的一個,被家裡人慣壞了。今天原本沒有帶他,可到了昭明寺才發現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跟了過來,隻好帶在了邊。親家……嗯,鬱太太不要放在心上。我回去了之後會好好教訓他的。”
陳氏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人,見衛太太這樣的客氣,忙道:“小孩子都是這麼頑皮,衛太太不必放在心上。”
衛太太聽了,立刻就和陳氏搭上了話。說的雖然都是些日常瑣事,卻能看得出來,對陳氏很用心,非常想和鬱家結親。
陳氏對衛太太一家也滿意,散的時候明確表示讓衛太太有空的時候去家裡做客。
衛家的人包括衛父,都面喜。
回去的時候馬秀娘也一直在誇衛小山。
鬱棠籲了口氣,開車簾回頭著漸漸遠去的昭明寺,良久一顆怦怦跳的心才慢慢平靜下來。
第二天一大早,衛家就請了人上門,誇鬱棠的話說了一籮筐,陳氏臉上的笑就沒有褪下去過,但還是按照習俗矜持地表示要考慮考慮。
婆知道這門親事十拿九穩了,歡歡喜喜拿了陳氏的賞銀走了。
大伯母想著之前大家議論鬱棠心高氣傲要招讀書人做婿的傳言,有心把這門親事傳了出去。
猜你喜歡
-
完結315 章
冷帝在上,傲嬌皇後求休戰
一朝穿越,冷羽翎隨還冇搞清楚狀況,就被成親了! 他是萬人之上的皇帝,高冷孤傲,“我們隻是假成親。” 成親後,冷羽翎感覺自己被深深的欺騙了! 為什麼這個皇帝不僅要進她的香閨,還要上她的床 這也就算了,誰能告訴她,為什麼他還要夜夜讓自己給他生娃呢!
53.9萬字8.8 66122 -
完結260 章

流放路上炮灰寡婦喜當娘
許柔兒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穿成炮灰寡婦,開局差點死在流放路上!不僅如此,還拖著個柔弱到不能自理的嬌婆婆,和兩個刺頭崽崽。饑寒交迫,天災人禍,不是在送死就是在送死的路上。但許柔兒表示不慌。她手握空間富養全家,別人有的我們也有,別人沒有的我們更要有!“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爹。”“爹?”許柔兒看著半路搶來的帥氣漢子,見色起意,一把薅來。“他就是你們的爹了!”帥男疑惑:“這可不興喜當爹。”“我都喜當娘了,你怕什麼喜當爹!”
47.3萬字8 29692 -
完結377 章

女主,你狐貍尾巴露了
養狐貍之前,裴鳴風每日擔憂皇兄何時害我,皇兄何處害我,皇兄如何害我?養了狐貍之后,裴鳴風每日心煩狐貍是不是被人欺負了,狐貍是不是受傷了,狐貍是不是要離開自己了。冀國中人人知宮中有個“狐貍精”,皇上甚為寵之,去哪帶哪從不離手。后來新帝登基,狐貍精失蹤了,新帝裴鳴風帶了個蕙質蘭心的皇后娘娘回來。
66.9萬字8 11395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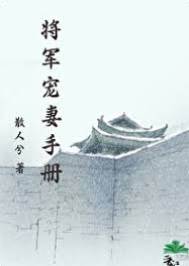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