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誘他瘋寵》 第1卷 第734章 為什麼非要不乖呢
言懷安猛的沖出去,外面已經沒了人。
這麼快,上哪兒去了?
言懷安臉瞬間變得難看,馬上給業打電話,又給言維漢打電話:“二叔,笙笙不見了……剛剛還在家,外面有人敲門,只是去開了個門,就被一只手拉走了。我沖出去的時候,樓道沒人,電梯也沒靜。”
言懷安一顆心“怦怦”猛跳,這眼看到晚上了,見鬼了?!
“打業電話了嗎?”
“打了。”
“行,我馬上過去,你看好孩子們,把門鎖好,我沒到之前,任何人敲門都不許開,明白了嗎?”
“明白了。”
言懷安趕把三個孩子喊到一起,將對門鎖了,回到自己這邊,房門關上,鎖死。
業很快上樓:“你好士,剛剛是您打的電話嗎?很抱歉,我們這層的監控剛剛壞掉了,并沒有找到可疑人員。”
言懷安氣壞了。
Advertisement
隔著門罵:“咋的我不是業主啊!你們一句很抱歉就算完事了?我告訴你們,我姐要是不出事就算了,我姐要是出了事,我讓你們賠命!”
罵歸罵,反正不開門。
“媽咪怎麼了?”
忽的問道,聶錚皺著小眉頭,甜甜偏著腦袋,“又有壞人了嗎?”
“乖,沒事的。你們先一邊玩。”
言懷安哄著三個寶寶回房間,又給言維漢打電話,“二叔,業說監控壞了。”
言維漢已經在趕來的路上:“我馬上就到。”
隔壁房間,顧一笙昏迷在地毯上,姣好的形玲瓏有致,部更是高,溫。
男人單膝跪落,低著頭看。
他致,有形,張力拉滿。
哪怕只是一個側臉,一個單膝跪地的作,就能看到他上極致的矜貴。
天之驕子,無人能及。
可偏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上跌跟頭。
“笙笙,你乖乖聽話不好嗎?為什麼,非要挑戰我。”
男人低低的說,聽到外面的業在拍門,也聽到言懷安在憤怒的著,但這些都跟他,也跟,都不會再有關系了。
隔壁的房間門開了又關,后有男人抱著懷里的人離開了。
業經理回頭看了眼,只當是隔壁的業主,也沒理會。
趕轉頭又去拍門,至,房里的人總得出來見個面吧!
“你說什麼都沒用!我要報警,我要等律師來!”言懷安大吼著。
才剛剛回到春城就出事,還是在的眼皮底子下……這到底是誰,也太猖狂了!
再看看后三個小崽崽,言懷安咬了咬牙,如果只有一人,早就沖出去了。
電梯門開了又關。
兩梯四戶的格局,上行下行的電梯,剛剛好錯過。
電梯門打開,言維漢快步走出:“安安,是我。”
地下車庫,男人懷中抱著昏迷的人,上了車。
車全部著防窺,男人坐進去,沉聲道:“所有人,現在分四個方向,開出小區。”
一模一樣的四輛車,開出地庫后,又在同一時間,開出小區。
十分鐘后,男人開著紅寶馬車,緩緩駛離地庫。
猜你喜歡
-
完結268 章

掌上尤物
白天,她是許清晝的私人秘書,負責替他賣命工作處理他接連不斷的小情兒。晚上,她頂著他未婚妻的身份任他呼來喝去,為所欲為。訂婚八年,許清晝的心上人一朝回歸,江羨被踹下許太太的位置,落得個眾人嘲笑奚落的下場。人人都等著看她好戲,江羨卻笑得風情萬種,當晚進酒吧,左擁右抱,勾來俊俏小狼狗,愉悅一整晚。她肆意卷土重來,各大財閥集團為爭搶她而大打出手;日日緋聞上頭條,追求者不斷。釣系小狼狗:“今晚約?房已開好等你來。”純情大男孩:“親愛的,打雷好怕你陪我睡。”快樂是江羨的,只有獨守空房的許清晝氣得兩眼發紅,...
55.9萬字8 63404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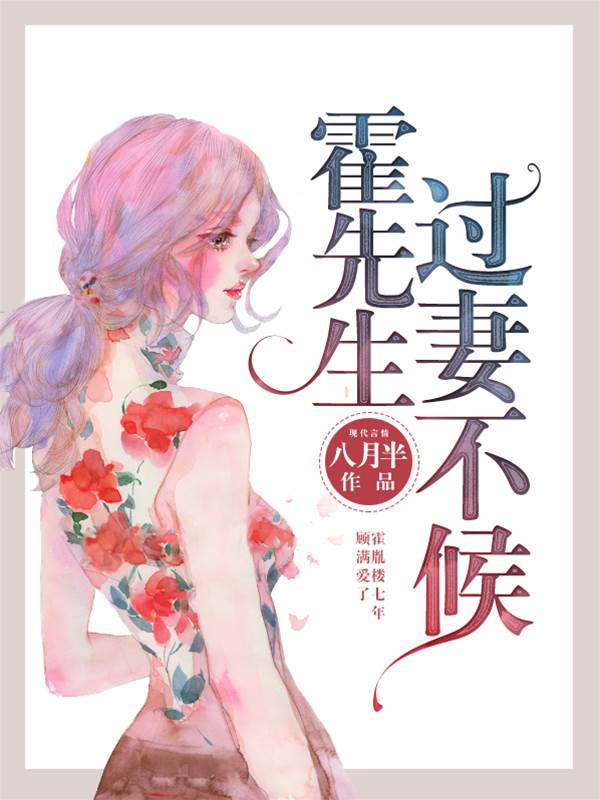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
完結108 章

哥哥他總想與我保持距離
曾經的他是一輪皎月,祈望驕陽;后來皎月已殘,又怎堪配驕陽?江歲和斯年第一次分別那年,她八歲,他十四。 彼時她緊緊地抱著他不撒手,口中歇斯底里的哭喊著:“年年哥哥,你別走!” 可他還是走了,只給她留下兩樣東西和一個約定。 十年后異地重逢, 他來機場接她, 他在她身后試探地喊她的名字:“江歲?” 她朝他不敢確定地問:“你是,斯年?” 兩個人面對著面,都差一點認不出彼此。 而此時他已跌落塵埃,卻依然對她痞笑著問:“呵,不認識了?” 匆匆一年,江歲像驕陽一樣,熾熱地追逐著他,溫暖著他。 而斯年卻深藏起對她深沉的感情,時刻想著與她保持好距離。 江歲可以忍受別人誤解她,嘲諷她,但她見不得有人在她面前羞辱和挑釁斯年。 斯年同樣可以忍受任何屈辱和諷刺,卻見不得江歲在他面前被人欺辱。 他竭盡一身力氣洗去泥濘,只為能站在她身邊。 然而造化弄人,他只能一次次親手將她推開。 江歲此生惟愿年年長相見。 斯年此生惟愿歲歲永平安。 前期:清純大學生女主vs多功能打工男主 后期:高級翻譯女主vs神秘總裁男主
29.4萬字8 1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