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奪我軍功,重生嫡女屠了滿門》 第326章 她有心上人了
平王從花壇中踉蹌站起,玄紅錦袍沾了泥土,卻毫不減他周凌厲的氣勢。
他狹長的眸微微瞇起,薄勾起一抹冷的笑:“許靖央,你竟敢摔本王!”
他一步步近,修長的手指過袖口沾染的灰塵,嗓音低沉而危險:“你是不是太過放肆了,三番兩次的冒犯僭越,真以為本王不舍得罰你?”
威國公此時急匆匆沖過來。
他一臉急:“靖央,你糊涂啊!那可是寧王殿下,你知道拒絕意味著什麼嗎?就算要拿喬,也該先收下聘禮再慢慢談條件!你倒好,直接回絕,一點面子余地都不留,讓王爺的臉往哪兒擱?”
平王突然轉頭,狹眸中閃過一異樣的彩:“拒絕了?”
威國公這才注意到平王也在場,連忙行禮:“平王殿下見笑,小不懂事,臣這就去寧王府賠罪。”
“你竟拒絕了蕭賀夜。”平王又看著許靖央重復一遍。
忽然,他低笑出聲,方才的鷙一掃而空,眼底泛起淡淡愉悅。
他抬手理了理凌的襟,目灼灼地盯著許靖央:“這麼說,你不想嫁給他。”
許靖央面始終如常。
“寧王殿下很好,可我現在不想婚,就這麼簡單,其余的,我想不用再跟王爺您贅述了。”
平王指著,點了兩下,似是想說什麼,旋即不知怎麼,又嗤的一聲垂眸低笑出聲。
“好個臭脾氣,總給本王驚喜,”說罷,他負手瞇眸,“行了,別擔心,二哥要是因此記恨刁難你,本王替你擔著。”
Advertisement
許靖央眸冷淡地皺了下眉。
平王心愉悅,轉就走,順帶拍了拍威國公的肩膀。
“賠什麼罪?郎妾意婚才有意思,二哥不由分說下聘提親,被姑娘家拒絕是活該。”
他大搖大擺地走了,威國公愣在原地,抹去額頭虛汗。
“靖央,平王殿下這是什麼意思?今天這件事跟他有什麼關系嗎?”
在許家人眼里,平王來質問這件事,本就奇怪。
許靖央也毫不客氣地冷冷說:“沒關系,他素來多管閑事,不必理會。”
說完,轉就走,威國公又追了上去,勸說親自去給寧王賠罪。
他們離開后,大房和三房才暗暗松口氣。
許靖妙輕輕拍了拍心口:“平王方才的表太嚇人了,真怕他生氣起來連自己都砍。”
許靖姿思索,到古怪:“阿姐婚,又不是他提親,他急什麼?”
說到這里,家人們對視了一眼,仿佛都有了某種猜測,但心照不宣地沒有開口。
平王晴不定,更驕縱恣意慣了,許靖央似冰,他就像火,兩個人若在一塊,還不得日日相互比著制?
許靖央定會吃苦。
只有三老爺默默地說了句:“相較之下,還是寧王殿下好。”
消息不過兩日就傳遍京城。
這兩天,許靖央跟蕭賀夜兩個當事人,都沒有見對方。
但朝堂中和私下里,對他們的議論可不。
期間威國公帶著大老爺和三老爺,一塊登門寧王府向蕭賀夜賠罪。
卻沒有見到蕭賀夜的面。
而是由管家代勞,好茶招待,又一番太極話送了出來。
不準蕭賀夜到底生氣與否,威國公連覺都睡不好了。
夜里翻來覆去,伺候他的春云都覺得有些厭煩。
“老爺怕什麼,兩日過去,皇上沒怪罪,這不代表沒事嗎?”
“婦人之見,真是目短淺!王爺提親都敢拒絕,我哪兒還睡得著?”
威國公著心口坐起來,想著若是再來一次,可不得這番刺激了。
蕭賀夜不見他,說不定就是記恨了。
威國公改變不了許靖央,現在主意大,不聽他的管教。
于是思來想去,他只能替許靖央想個蹩腳的借口。
說來奇怪,這兩天平王待他格外好。
先是送了他兩個莊子,又安排專人陪伴威國公去買玉。
知道威國公喜歡排場,于是去哪兒都前呼后擁,將他快捧到了天上去。
直至酒桌上,好吃好喝的伺候,眼看著威國公喝了酒,已經飄飄然開始吹牛了。
那位平王安排來的雅俊吏便含笑道:“國公爺,您看,現在城中對昭武郡主拒絕寧王殿下的事,議論紛紛,在下斗膽,真想問問其中緣由。”
“昭武郡主之所以拒絕,莫非是你們對的婚事另有安排?”吏親自倒酒,彎腰躬,態度恭敬至極。
威國公了下沾著花生米碎屑的胡須,提到這件事,眼神顯然清醒了幾分。
他低聲音:“不瞞你說,我這個兒任得很,能耐足,我可管不了,不過拒絕王爺,確實另有。”
“哦?在下愿洗耳恭聽。”
“不能說給你知道,否則,對我兒名聲不好。”
“在下絕不傳,您盡管放心,否則,昭武郡主也不會放過在下,您說是不是?”
威國公有意將消息出去,故而沒再藏著掖著,而是掩低聲音說:“我兒有心儀之人!”
吏眉心一跳,暗自記下:“當真?您再說仔細些……”
將爛醉如泥的威國公送回府邸,吏便趁夜去了平王府。
將他從威國公那兒打聽來的話,據實稟奏。
平王拭匕首的作一頓,狹眸回顧:“心儀之人?誰?”
吏拱手:“威國公倒是沒細說,但在下同他相的這幾日,發現他這個人的習慣撒謊托大,十句里九句不實,此事未必是真,王爺還要謹慎看待。”
平王放下匕首,修長的手掌撐著桌子沉。
以許靖央的格,倒是真有可能,因為喜歡別人,才敢果斷拒絕。
他忽然在想,此人有沒有可能是他?
畢竟許靖央從未說過討厭他,不是麼?
三月三,上巳節,也是大燕的兒節。
在這天常有男相看定親的傳統,更因為是春天,萬萌發之際,過往文人墨客都將這日賦予了容易意萌的特殊意義。
宮里辦宴,皇后邀請世家門閥的閨秀公子共同赴宴。
這種場合,許靖央素來是裝扮素雅低調,然,這次卻一反常態,披了段明紫的錦帛,將原本素雅的妝點得明麗。
一個清艷滴的人,在上巳宴里,分外出眾。
在進宮之前,許靖央就猜到,皇后或長公主,肯定會借這次機會,打探的態度。
故而叮囑許靖妙和許靖姿,若被傳召走,要們互相照顧。
果不其然,許靖央剛到沒片刻,大宮就走過來福。
“昭武郡主,皇后娘娘和長公主在那邊的賞花亭等您過去說話。”
許靖央抬眸看去。
籠紗輕搖,映出賞花亭幾道影,或坐或立。
紗幔被風吹拂,分開一角,許靖央跟蕭賀夜四目相對。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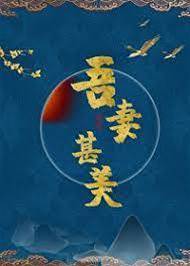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2238 章

天下第一妃
她,二十一世紀Z國軍情七處的頂尖特工,一朝穿越成為懦弱無能的蕭家廢物三小姐!未婚夫伙同天才姐姐一同害她遍體鱗傷,手筋腳筋被砍斷,還險些被大卸八塊?放肆!找死!誰再敢招惹她,休怪她下手無情!說她是廢物?說她沒有靈獸?說她買不起丹藥?睜大眼睛看清楚,廢物早就成天才!靈獸算個屁,神獸是她的跟屁蟲!丹藥很貴?別人吃丹藥一個一個吃,她是一瓶一瓶當糖豆吃!他,絕色妖媚,殺伐決斷,令人聞風喪膽的神秘帝王。當他遇上她,勢必糾纏不休! “你生生世世只能是我的女人!
411.7萬字8 36333 -
完結1065 章

新婚夜和離,失寵醫妃冠絕京城
醫學天才穿越成淩王棄妃,剛來就在地牢,差點被冤死。身中兩種蠱、三種毒,隨時都能讓她一命嗚呼。她活的如履薄冰,淩王不正眼看他就算了,還有一群爛桃花個個都想要她的命。既然兩相厭,不如一拍兩散!世間美男那麼多,為什麼要天天看他的冷臉?……“我們已經合離了,這樣不合適!”“沒有合離書,不作數!”就在她發覺愛上他的時候,他卻成了她殺母仇人,她親手把匕首插入他的心口……真相大白時,他卻對她隻有恨,還要娶她的殺母仇人!“可是,我懷了你的孩子。”“你又要耍什麼花招兒?”
177.9萬字8.18 12197 -
完結274 章

醜女絕色,瘋批暴君夜夜囚寵
前朝覆滅,最受寵愛的小公主薑木被神醫帶著出逃。五年後她那鮮少接觸過的五皇兄平叛登基。她易容進宮,為尋找母親蹤跡,也為恢複身份……一朝寒夜,她忽然被拉入後山,一夜雲雨。薑木駭然發現,那個男人就是龍椅之上的九五之尊……她再次出宮那時,身懷龍胎,卻在敵國戰場上被祭軍旗,對麵禦駕親征的皇帝表情冷酷無比,毫不留情的將箭羽瞄準於她……他冷聲,“一個女人罷了…不過玩物,以此威脅,卻是天大笑話!”(注:此文主角沒有冒犯任何倫理)不正經文案:……獨權專斷的暴君為醜女指鹿為馬,即便醜陋,也能成國家的絕美標桿!恢複真容的醜女:……那我走?——————種植專精小能手,從人人厭憎的“禍國妖妃”,變為畝產千斤的絕色皇後!
49萬字8 2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