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第1卷 第30章 亂了心動了情
午飯之后,謝令窈又被瓊枝公主拉著說了好一會兒話才把人放回去。
京都的風向最是變化無常。
謝令窈來的時候人人看向的目都倨傲之下又都藏著眸睨。
從公主府離開之時,見了的人都很熱地朝打招呼,突然所有人都變得親善起來。
謝令窈進了馬車,已經笑僵的臉終于有機會得到息。
江雨霏們幾個已經先回去了,謝令窈被留到現在,只有自己一個人乘了那車往侯府去。
謝令窈半靠在墊上閉目養神,突然馬車一沉,瞬間睜開眼,只見一只修長均勻的手霸道地掀開了簾子。
“江時……江公子?”
謝令窈訝異地輕呼出聲,不敢相信江時祁竟敢直接闖進的馬車之中,做出如此不統的行徑來。
江時祁倒是神自然,順勢就落了坐。
“我來時是坐的同僚的馬車,謝小姐左右都是要回侯府的,勞煩順便捎江某一程。”
謝令窈從沒見過江時祁如此不客氣的一面,呆愣之間,下意識地點了點頭。
“多謝。”
人已經上來了,再想請下去也顯得不通人。
謝令窈此刻也沒心去計較這些有的沒的
自覺收了收,給江時祁高大的軀多騰了些位置出來,復而重新閉上眼。
江時祁的視線過謝令窈的眉眼,最后落在隨著馬車的搖晃而一上一下晃的步搖上。
江時祁問:“你在為瓊枝公主挑破你我二人的婚事而煩心?”
“不是這個。”
“還有什麼?”
謝令窈并未睜開眼,聲音染上了些疲倦:“還有江公子你的態度。”
知道,江時祁從來不會在無意義的事上浪費力,他愿意同自己拉扯糾纏,很明顯,他在搖。
江時祁間溢出輕笑,他還真沒想到謝令窈會如此直接。
Advertisement
“江公子,此刻就你我的二人,有些話不妨直說。”
江時祁指尖輕輕過自己的下,覺得有些為難。
他自己尚未明晰自究竟意何為,他深陷于猶豫且反復的困境之中,既全又霸占……
江時祁慣會掌控局面,謝令窈為難他,他也反過來去為難謝令窈。
“既然謝小姐亦覺得應當坦誠相告,那可否煩請你先為在下答疑,那日你酒醉之后所言,究竟所為何故?”
謝令窈不記得說了些什麼,從江雨霏的口中,只知道罵江時祁是個王八蛋。
沒有罵錯!
“恐怕要令江公子失了,那日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統統都不記得了。”
“無妨。”江時祁頓了頓:“我還都記得,我可以替你回憶。”
謝令窈角狠狠一,呵呵干笑兩聲:“大可不必。”
可無奈江時祁并不是個之人,忽略了謝令窈的拒絕,面無表卻又毫不猶疑地問出他心中疑。
“你說,你恨死我了。”
“為什麼?為什麼會恨我?”
謝令窈心口一陣刺痛,為什麼?突然覺得有些不公平,憑什麼背負著前世的種種,而一無所知的江時祁卻可以心安理得地問為什麼?
那顆炙熱而雀躍的心,早就被他一盆又一盆的冷水澆滅澆,只剩一縷輕煙茍延殘。
“江公子希得到什麼答案?”
江時祁一字一句道:“實話實說就好。”
謝令窈向來不會撒謊,稍作遲疑后,終究還是決定信口胡謅。
“由于這樁你不愿我亦不愿的婚約橫亙于我與我心之所系之人之間,致使我與他的滿心深只能深埋心底,難道我不該恨你麼?”
江時祁的角一點一點垂了下來,繃的下頜線顯示了他不悅的心緒。
“謝小姐當真心有所屬?”
“是!”謝令窈睜開眼,一錯不錯地對上江時祁狹長的眼睛,以證明所言非虛。
“他是誰?”
謝令窈避而不答,只道:“這是我的私事,不便告訴江公子,還請見諒。”
氣氛慢慢沉寂下來,江時祁低垂的眼被纖長的睫蓋住,讓人猜不出他在想什麼,就在謝令窈以為他不會再說話時,他卻陡然開口。
“是李之憶麼?”
“不是。”謝令窈飛快反駁:“我與他統共也沒見過幾次。”
此刻急需一個擋箭牌,然而卻并不打算將李之憶牽扯進來,謝令窈雖對他并無喜之,但也深知一份真摯的不應被肆意踐踏。
“他與我一樣,生在簡州長在簡州,與我算是青梅竹馬,我們深厚卻困于這段本就不該存在的婚約。只待你我婚約解除,我即刻便返程回簡州同他親。”
直至夜,江時祁耳邊依舊回響著謝令窈這番無無義的話。
他沉默地飲下一口神醉,堵在心口的緒不是惱怒不是怨恨,竟是委屈。
明明與他早有婚約,謝令窈怎麼可以上旁人?
他不想承認自己了心了,可事實如此,容不得他抵賴。
江時祁自覺可笑,二十余年來心如止水,竟如此輕易地被搖,明明謝令窈對他避之不及,猶如躲避瘟疫,他卻還不知死活地妄圖奉上一片赤誠之心。
喝下半壺神醉,江時祁向來清明的頭腦終于是昏沉了,他強撐著沐浴之后將自己重重砸在了床上。
可明明喝酒就是為了忘卻一切,安心睡,可偏偏卻又不得如愿。
他又夢見了謝令窈。
他總覺得浩瀚閣有些空寂,哪怕被周氏添置了許多奢華的的家,依舊顯得有些空。
可夢里卻不同,自從江時祁進院門起,便發現有許多被逐漸侵的痕跡。
院里的花花草草規整有序,翠綠的草木間點綴著艷的花朵,院中央搭建了一個簡潔的秋千,上面攀附著薔薇,顯然是為某位子心準備的。
江時祁沿著小徑一點一點往里探索,不有些張,又有些期待,會是麼?
順著院門一路進來,忙忙碌碌的下人似乎并沒有發現他,全都專心致志地干著手上的活兒。
浩瀚閣從來沒有這樣熱鬧過。
直至走到了他的臥房前,江時祁抬眼去,瞳孔猛地了。
過大開的窗戶,江時祁看見了謝令窈。
儼然一副婦人的裝扮,發高高挽起,出一截白皙的脖頸,手中抱著一個襁褓中的孩子,窗外的合歡花的過燦爛的暖,投出綽綽的影子落在洋溢著溫和靜謐的笑意的臉上。
那是謝令窈的孩子麼?
江時祁怔然,腳步不聽使喚地靠了過去。
進了屋,江時祁環視一周,屋擺上了一個碩大的妝臺,上面滿滿當當擺滿了謝令窈的胭脂水,床幔被褥皆換了艷鮮的,敞開的柜子里也全是的漂亮裳,他那一向冷冷清清臥房現在四都是謝令窈一點一點進他生活的點點滴滴。
謝令窈聽見聲音,抬頭去看他,有些手足無措,慌忙起要把孩子放回小床上。
“夫君今日怎麼有空回來了?”
江時祁心口一熱,原來那是謝令窈和他的孩子?
“夫君?”謝令窈走到江時祁邊,小心翼翼地抬手抱住他的胳膊:“可是累了?”
“他……”
江時祁僵了子,看了看睡中的孩子,有些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謝令窈眼睛彎了彎,松開他的手,轉而抱起了孩子。
江時祁手臂驟然一空,還來不及失落,一個乎乎的孩子就落在了他手上。
“舟兒今日可乖了,吃飽了就好好睡了一整個下午,一點兒也沒鬧人。”
江時祁新奇地了孩子藕節兒似的小手,又又。
掂了掂,江時祁笑道:“還重。”
謝令窈赧一笑:“舟兒可能吃了!就是不要娘,非要我親自喂……”
江時祁下意識瞥了一眼謝令窈本就盈的那,果然……
江時祁呼吸一熱,艱難移開目。
謝令窈似有些傷,咬著紅了眼:“夫君可是嫌我胖了?”
“沒有。”江時祁不自然道:“你這樣很好。”
江時祁沒說謊,多了些的謝令窈并不顯臃腫,的模樣別有一韻味。
“可是你……自我有孕后,再沒過我。”
謝明窈極,轉過去,不肯讓江時祁看見紅的臉。
江時祁險些失手將手里的孩子丟了出去,他是個正常男人,哪怕還未經事,也知道謝令窈話里的意味是什麼。
江時祁的呼吸變得急促,頭滾,手里的孩子突然變得有些礙手。
這不過是一場夢罷了。
等他吻上謝令窈的那刻,他腦海便只剩下這句自己安自己的話。
夢里的事,如何能當真?便讓他放縱這一回吧。
江時祁對這種事不過是紙上談兵,本應生疏,可夢里的他分明十分稔,畔輕之后便輕車路地用舌尖撬開閉的貝齒,再然后……一切都變得失控起來。
極致的愉悅過后,江時祁徹底驚醒。
下的狼藉讓他眼眶發紅,間發苦。
在漆黑的夜中,他翻了個,絕地拉過被子蓋住自己的臉,也蓋住他的恥辱。
寂靜之中,是江時祁發的低喃。
“江時祁,你怎麼可以這樣無恥?”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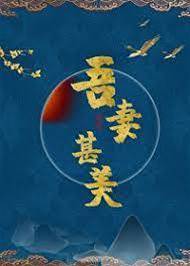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2238 章

天下第一妃
她,二十一世紀Z國軍情七處的頂尖特工,一朝穿越成為懦弱無能的蕭家廢物三小姐!未婚夫伙同天才姐姐一同害她遍體鱗傷,手筋腳筋被砍斷,還險些被大卸八塊?放肆!找死!誰再敢招惹她,休怪她下手無情!說她是廢物?說她沒有靈獸?說她買不起丹藥?睜大眼睛看清楚,廢物早就成天才!靈獸算個屁,神獸是她的跟屁蟲!丹藥很貴?別人吃丹藥一個一個吃,她是一瓶一瓶當糖豆吃!他,絕色妖媚,殺伐決斷,令人聞風喪膽的神秘帝王。當他遇上她,勢必糾纏不休! “你生生世世只能是我的女人!
411.7萬字8 36333 -
完結1065 章

新婚夜和離,失寵醫妃冠絕京城
醫學天才穿越成淩王棄妃,剛來就在地牢,差點被冤死。身中兩種蠱、三種毒,隨時都能讓她一命嗚呼。她活的如履薄冰,淩王不正眼看他就算了,還有一群爛桃花個個都想要她的命。既然兩相厭,不如一拍兩散!世間美男那麼多,為什麼要天天看他的冷臉?……“我們已經合離了,這樣不合適!”“沒有合離書,不作數!”就在她發覺愛上他的時候,他卻成了她殺母仇人,她親手把匕首插入他的心口……真相大白時,他卻對她隻有恨,還要娶她的殺母仇人!“可是,我懷了你的孩子。”“你又要耍什麼花招兒?”
177.9萬字8.18 12197 -
完結274 章

醜女絕色,瘋批暴君夜夜囚寵
前朝覆滅,最受寵愛的小公主薑木被神醫帶著出逃。五年後她那鮮少接觸過的五皇兄平叛登基。她易容進宮,為尋找母親蹤跡,也為恢複身份……一朝寒夜,她忽然被拉入後山,一夜雲雨。薑木駭然發現,那個男人就是龍椅之上的九五之尊……她再次出宮那時,身懷龍胎,卻在敵國戰場上被祭軍旗,對麵禦駕親征的皇帝表情冷酷無比,毫不留情的將箭羽瞄準於她……他冷聲,“一個女人罷了…不過玩物,以此威脅,卻是天大笑話!”(注:此文主角沒有冒犯任何倫理)不正經文案:……獨權專斷的暴君為醜女指鹿為馬,即便醜陋,也能成國家的絕美標桿!恢複真容的醜女:……那我走?——————種植專精小能手,從人人厭憎的“禍國妖妃”,變為畝產千斤的絕色皇後!
49萬字8 2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