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死后,薄爺跪在墓碑前哭成狗》 第638章 要不要跟我回家?
脖頸被那只手寸寸勒,吸的空氣稀薄至極,快要窒息。
喬予拼命著江嶼川的大手:“你跟沈茵……有過一個孩子……你真的不記得了嗎!那個孩子……江貝……”
江貝?
江嶼川頭痛裂,手部力道輕微卸力后,喬予猛地推開他,大口大口的著氣。
江嶼川被推的跌坐在床沿,微微弓著,臉蒼白而繃。
那些如同碎片的記憶,像是一張不氣的網,將他死死箍住,畫地為牢。
“江貝……那個孩子是怎麼死的?”
喬予在平復片刻后,防備的看著他說:“是你妹妹江晚買兇親手害死的,那個孩子在沈茵肚子里不過三個月大,就因為那場蓄意謀殺的車禍,差點一尸兩命。孩子沒了,沈茵從鬼門關走了一遭,卻被害得終生不孕。”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你的記憶里,沈茵了害死江晚的兇手。大概是因為,沈茵在車禍恢復記憶后,把江晚害死我養母的事告訴了薄寒時。”
“沈茵很聰明,也的確有私心,也知道按照薄寒時的格,如果知道這件事,不會讓江晚好過。借了薄寒時這把刀,替自己和你們的孩子報了仇。”
“因為江晚是你的親妹妹,知道你心,下不去手,在和孩子跟你妹妹江晚之間,江嶼川,你捫心自問,有沒有一次、哪怕是一次,你毫不猶豫的堅定地站在沈茵和孩子這一邊?”
Advertisement
“如果你不包庇江晚,堅定地站在沈茵這邊,我想當時沈茵不會孤立無援的去給薄寒時通風報信,跟薄寒時并沒有多。如果你能替做主,替和你們的孩子報仇,哪怕是押著江晚去自首,那沈茵也許不會跟你離婚,更不會離開你。”
“至于江晚,即使上背著幾條人命,如果你當初不
那麼縱容的放走,提前去自首,大概率也不會死在薄寒時手里。”
“江嶼川,你走到今天這步,是你自己選擇的,沒有人你。你現在眾叛親離、孑然一,不是你邊的人要走,是你自己親手走了他們。”
“沈茵在最你的時候,你是怎麼對的呢?你包庇差點害死的兇手,欺騙結婚,親手抹滅了對你最后的。你總說羨慕我跟薄寒時,可沈茵也那樣過你,是你自己抓不住。”
“是你自己走了沈茵,又推開了薄寒時。我不知道你跟薄寒時徹底決裂的時候,你是什麼,但我很清楚的記得,薄寒時其實很難過,即使他上不說,可我知道,他甚至在心里后悔過,如果當初對江晚留有一余地,你們之間是不是就不用走到今天這一步。”
“我知道也許你不會信。但在你跟他割袍斷義之后,套現百億從SY離開卻安然無事,你以為是因為你做的夠干凈嗎?后來你又使手段挖走SY的高管,你覺得薄寒時會不知道是你干的嗎?”
不帶緒的陳述著這些事實,一字一句像是利刃一般,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扎的江嶼川連呼吸都是刺痛的。
他僵在那兒,好半晌沒有回音,死寂一片。
喬予又說:“就是因為心里對你有愧疚,所以他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你。就像現在,你即使這樣對我,他也不會真的把你怎麼樣。因為在他心里,你曾經是他用心維系了十余年的兄弟,他上對你再狠,可依舊
給了你背刺他的機會,他把刀遞給了你,如果你捅他,他會選擇著,直到他認為,他不欠你為止。”
江嶼川弓腰坐在那兒,陷在一片昏暗之中,消沉而頹靡。
他的臉,垂的很低。
喬予看不見他的表,只深吸了口氣說:
“你現在當然可以不計后果的毀了我,你毀了我,就等于毀了薄寒時。但江嶼川,你確定,你在把跟他十余年的友全部葬送以后,你會得到一一毫的高興嗎?”
他不知道消化了多久。
大概是并不愿意接這些事實,逃避又或者是不敢,試圖自己將錯就錯下去。
他抬起暗淡蒼白的臉,冷冷看著喬予嘲弄道:“你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自以為能打我,覺得我會念著一舊放過你是嗎?”
“我沒想過你會放了我,你可以拉著我和你爛死在一起,可這樣的話,沈茵又算什麼呢?你說你曾經喜歡過我,你喜歡一個人就是去毀了一個人嗎?所以你沈茵,你就讓在你們的里變得支離破碎、失頂。江嶼川,我以前只是覺得你心懦弱,可現在我又覺得,你像條可恨的可憐蟲,用這種骯臟下作的方式來挽留邊人對你的,可你越是這樣,就越是什麼都握不住。”
“你說夠了嗎!說夠了滾出去!”
喬予這些話像是了他的肺管子,他手一揮,床頭柜上的東西掉落,包括那罐來歷古怪的安神香,末散了一地,香氣漂浮,濃郁。
喬予暗暗松了口氣,快步離開主臥,剛出手機,就收到薄寒時發來的信息。
【出來,我在附近。】
他
一直在那頭監聽著,知道現在的形。
喬予看了一眼樓上閉的臥室門,快步出了別墅,剛要問薄寒時他在哪兒,眼前忽然落下一道黑影,整個人被強勢卷一膛里,都來不及看清對方的臉,已經被裹挾著塞進了車里。
聞到那抹悉的冷冽氣息,喬予繃懼怕了一晚上的軀在頃刻放松下來,將臉埋在他懷里,抱住了薄寒時的腰。
頭頂上方響起薄寒時冷不丁的聲音:“現在知道怕了?剛才激怒老江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他真的會失手掐死你?”
盡管喬予極力克制著,可渾還是止不住的在他懷里輕抖。
剛才江嶼川要是再下一點死手,就會窒息而亡。
說不怕是騙人的。
薄寒時責備的同時,又忍不住心疼,抱著的雙臂不自覺收了一點,將按進懷里,給足安全。
他低頭去查看的脖子。
泛著一涼意的指腹上去,落在脖頸的紅勒痕上,再想開口責備的時候,看見倉惶未定的眼神,終是輕輕嘆氣:“疼不疼?以后還敢不敢?”
見抿著不說話。
他指腹稍稍用力按了下那勒痕,喬予微微皺眉:“疼。”
薄寒時輕輕握著后頸,又仔細查看一番,嘆息:“知道疼,那要不要跟我回家?”
“……”
喬予從口袋里出一小袋東西,塞進他手心里,“也還是有點收獲的,在江嶼川臥室發現的,點燃之后會有一種特殊的香氣,聞久了好像會讓人產生幻覺,也會干擾記憶。你讓宋淮化驗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猜你喜歡
-
完結86 章

不見面的男朋友
謝桃交了一個男朋友。他們從未見面。他會給她寄來很多東西,她從沒吃過的零食,一看就很貴的金銀首飾,初雪釀成的酒,梅花露水煮過的茶,還有她從未讀過的志怪趣書。她可以想象,他的生活該是怎樣的如(老)詩(干)如(部)畫。因為他,謝桃的生活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不用再打好幾份工,因為他說不允許。她的生活也不再拮據,因為他總是送來真金白銀。可她并不知道,她發給他的每一條微信,都會轉化成封好的信件,送去另一個時空。
33.7萬字8.18 24275 -
完結493 章

重生歸來,家里戶口本死絕了
前世,顏夏和顧家養女一起被綁架。無論是親生父母、五個親哥哥,還是青梅竹馬的男朋友,都選了先救養女,顏夏被撕票而死。重生歸來,和父母、渣哥斷絕關系,和青梅竹馬男朋友分手,她不伺候了。為了活命,她不得不卷遍娛樂圈。大哥是娛樂圈霸總。轉眼親妹妹開的明星工作室,居然變成了業內第一。二哥是金牌經紀人。轉眼親妹妹成了圈內的王牌經紀人。三哥是超人氣實力派歌星。轉眼親妹妹一首歌紅爆天際。四哥是知名新銳天才導演。轉眼親妹妹拍的電影票房讓他羨慕仰望。五哥是頂流小鮮肉。轉眼...
89.8萬字8.5 160248 -
完結244 章

一眼著迷
五歲那年,許織夏被遺棄在荒廢的街巷。 少年校服外套甩肩,手揣着兜路過,她怯怯扯住他,鼻音稚嫩:“哥哥,我能不能跟你回家……” 少年嗤笑:“哪兒來的小騙子?” 那天起,紀淮周多了個粉雕玉琢的妹妹。 小女孩兒溫順懂事,小尾巴似的走哪跟哪,叫起哥哥甜得像含着口蜜漿。 衆人眼看着紀家那不着調的兒子開始每天接送小姑娘上學放學,給她拎書包,排隊買糖畫,犯錯捨不得兇,還要哄她不哭。 小弟們:老大迷途知返成妹控? 十三年過去,紀淮周已是蜚聲業界的紀先生,而當初撿到的小女孩也長大,成了舞蹈學院膚白貌美的校花。 人都是貪心的,總不滿於現狀。 就像許織夏懷揣着暗戀的禁忌和背德,不再甘心只是他的妹妹。 她的告白模棱兩可,一段冗長安靜後,紀淮周當聽不懂,若無其事笑:“我們織夏長大了,都不愛叫哥哥了。” 許織夏心灰意冷,遠去國外唸書四年。 再重逢,紀淮周目睹她身邊的追求者一個接着一個,他煩躁地扯鬆領帶,心底莫名鬱着一口氣。 不做人後的某天。 陽臺水池,紀淮周叼着煙,親手在洗一條沾了不明污穢的白色舞裙。 許織夏雙腿懸空坐在洗衣臺上,咬着牛奶吸管,面頰潮紅,身上垮着男人的襯衫。 “吃我的穿我的,還要跟別人談戀愛,白疼你這麼多年。”某人突然一句秋後算賬。 許織夏心虛低頭,輕踢一下他:“快洗,明天要穿的……”
36.7萬字8 11823 -
連載332 章

禁止離婚!傅先生強寵小甜妻
認識不到兩小時,姜蔓便和傅政延領證結婚。 她爲了臨時找個地方住,他爲了應付家族聯姻。 婚後,姜蔓一心搞事業,努力賺錢,想早點買房離婚搬出去, 然而,傅先生卻對這小妻子寵上癮了, “老婆,禁止離婚!“ “我不耽誤你搞事業,你上班的時候,還可以順便搞一搞我~” 姜蔓這才知道,原來自己的閃婚老公,竟是公司的頂級大老闆! 公司傳聞:傅總裁寵妻無度,和太太天天在辦公室搞甜蜜小情趣~
58.4萬字8 3247 -
完結2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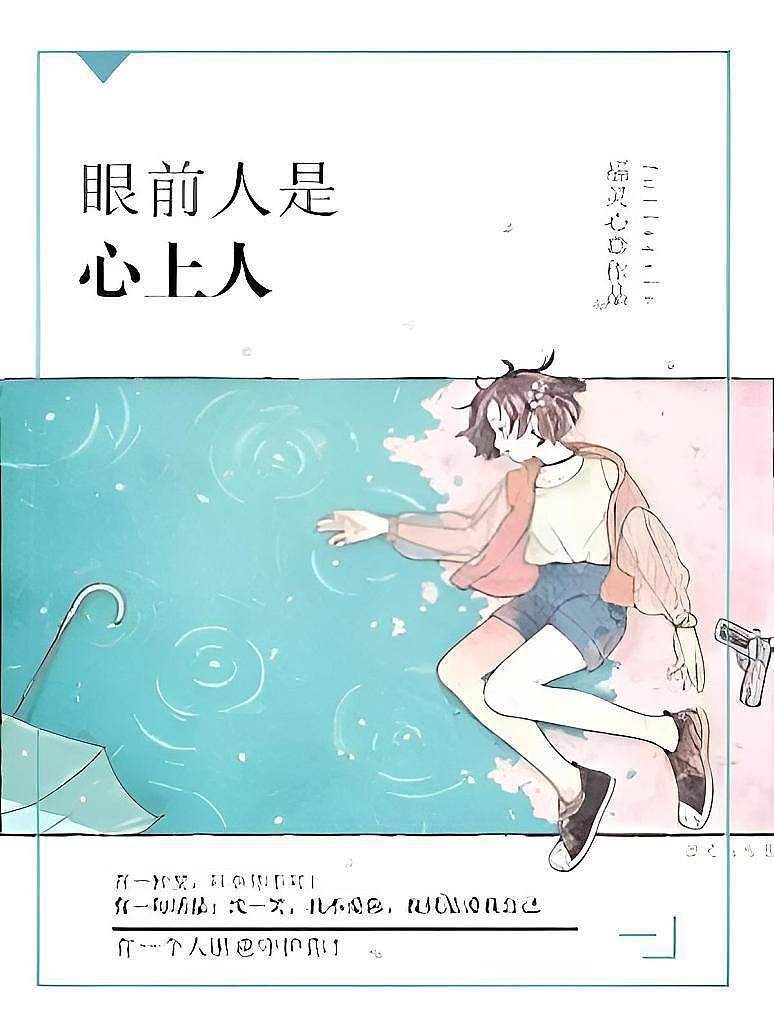
眼前人是心上人
巫名這兩個字,對于沈一笑來說,就是掃把星的代名詞。 第一次她不走運,被掃把星的尾巴碰到,所以她在高考之后,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離開。 卻沒想到,這掃把星還有定位功能,竟然跟著她來到了龍城! 本來就是浮萍一般的人,好不容易落地生根,她不想逃了! 她倒要看看,這掃把星能把她怎麼著。 然而這次她還是失算了。 因為這次,掃把星想要她整個人……
25.9萬字8 1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