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為餌》 第153章 既定賭約
“原來如此!”將離點點頭,見天不早了,便繼續趕路,同時催促:“咱們快走吧!上山還要一會時間,若是慢了,連齋飯都趕不上。”
白餌可沒他那麽貪吃,輕輕揚起頭,閉上眼睛,任熱地照在的臉上,任溫暖深每一寸,等微風夾雜著野草的芳香,徐徐吹來,心裏隻覺得暖暖的,有那麽一瞬,覺得風是暖的,就像是......就像是春風的味道。
“我說你發什麽愣?快走吧!快走吧!”
將離一個人大步流星上了好幾個臺階,回頭時,才發現仍舊停在那,是一副呆若木的樣子,他吐吐氣,又灰溜溜地折回去,一把將拖走。
被他拉得連連摔了好幾個踉蹌,連鬥笠上垂下來的皂紗也被風吹得淩不堪,白餌頓時從好中驚醒,後一陣拔涼。一邊手忙腳地扯著眼前的皂紗,一邊驚喜地呼喚:“我跟你說,我方才好像到了春風,暖暖的......”
“這天寒地凍的,哪來什麽春風?是你自己臆想的吧!”將離隨意接口道,催促著趕路:“快走吧!別想那些有的沒的了,要想也先想想怎麽填飽肚子!”
白餌眼神有些飄忽不定,聽他那口氣,頓時有些無可奈何,隻覺得自己就是對牛彈琴,努力扯開被他攥得有些疼痛的手,裏念念有詞:“吃吃吃,我看啊你就知道吃!”
埋著頭,提起,自顧自地往前走了,經過他邊時,連一個眼神都懶得丟給他,頂多肩。
見一溜煙地從自己麵前經過,將離頓住腳,有些納悶,一眨眼,便見走遠了,著急呼喊:“喂!你等等我!”
“這臺階這麽陡,你走慢些,可別急功近利啊!你若一來就將力氣全用完,到後麵還沒登到頂,我猜你就要倒!”追上後,挨著的步子,很是認真地提醒道。
Advertisement
聽到這話,白餌打心裏樂嗬,好悉的字眼,好悉的話呀!當初囚奴囹圄中,王福覺得自己輕胳膊輕,定然挨不住工地上的那些重活,也賭會倒下,可結果呢?王福自個累得半死,卻自我覺良好。
如今連將離也瞧不起,還真有點生氣了,腳步陡然加快,狂擺作幅度,以泄心頭之怒,腦袋裏麵哄哄的,思前想後還是有些氣不過,驟然停下來,猛地一個轉:“我——”
低著頭追而上的將離,對驟停的腳步毫無防備,一不留神,便撞在了的上,但那隻是蜻蜓點水一瞬間的事,他頓時有些發蒙,隻覺得整個子有些輕飄飄,由於所站的臺階極其狹窄,整個人忽然後仰,他差點要出聲來!
幸得白餌手速極快,一把扯住了他的袖,才防止他跌了下去,暗暗抬眼看,他後是一段段陡峭的臺階......整個人嚇得話都說不出來了,隻是失魂落魄地盯著他,目有些呆滯,作有些僵。
將離完全就是金獨立的姿勢,他著眉眼,張得有些浮誇,表示很驚恐,不過,眼前的白餌貌似比他還要驚恐......他旋即輕輕鬆鬆地直起子,玉立住了。因為,若是再不立起來,以他的重量,準要將一同拖帶下去,接著便是二人護抱狂滾臺階......畫麵太刺激,幾乎不敢想象。
他佯裝著有驚無險的樣子,倒吸了一口氣,開始抱怨:“我說你上個臺階怎麽一快一慢的?不知道臺階上不能站人嗎?我差點就要被你撞飛了......”
白餌順了順氣,回過神想想還真有些後怕,若是真摔下去了,不死也要殘。不過見他剛才那副作態的神,瞬間就不開心了,擺擺眼,喃喃道:“是你自己沒站穩,怪我咯!”
聽的語氣,竟了他的錯了,將離有些不明所以,略帶無奈地勾了勾角,很是恭維地說:“那我真是謝謝您嘞!若不是白俠及時出手相救,小人今日恐怕就要葬絕地了!”
這話雖聽著有些諷刺,不過......他話中的一個稱謂深得心,索就不與他一般見識了。淺淺皂紗中,出淡淡一笑,很是配合道:“江湖人麵前,不必言謝。”
說罷,扭頭走了,皂紗緩緩飛起,著實有些九天聖的韻味。
將離低著頭,努力抑製住破涕為笑的,一步一步跟了上去。想起方才之事,疑著問:“對了,你剛才為什麽要停下來,你想說什麽?”
“沒什麽。”白餌滿不在乎地回道,可最後還是忍不住說:“就是想和你打個賭。”
打賭?將離饒有興致道:“說說看。”
“若是我在登頂前還未倒下,那你便將你最厲害的本事教給我。”白餌一字一句說清。
他一次一次地救下自己,對他最大的印象便是手了得,但自從得知他是神將司追雲令的一殺,相信了他是神將司最厲害的殺手之後,總覺得還不夠驚豔,既為一等殺手,若沒點殺手鐧的東西,那他又如何在神將司中立足?
“那若是倒下了呢?”將離輕蔑一笑,好奇地問。
白餌猶豫了片刻,角微抿,淡淡道:“可以幫你實現一個心願。”
“好啊!”將離興不已,想都沒想,迫不及待道:“那我要你做我將離的人!”
被他的話驟然一驚,白餌一時語塞,登時不知該如何接口,腳步不加快。
“怎麽樣?”將離挑挑眉,期待道。見不語,囔囔道:“說話說話,還敢不敢賭了?”
白餌了額頭上悄然冒出的大汗,隻覺得有些,被他聲聲,又沒臺階可下,索抬起聲音應付了一句:“賭!怎麽不賭?”
自己誇下的海口,豈能轉眼食言?雖然這個賭約在很大程度上有些不對等,甚至還可能賠上自己,但堅定自己可以贏,對的,可以贏......呃,以前上山去金明寺行的都是稍微寬敞的路,還是走走歇歇的那種,如今對來說,的確是一次不小的挑戰。
但想著能夠從他上學到殺手鐧,便格外得激和興,掌握殺手鐧後,便能手刃了那些猖狂的狼人,為死去的仇族百姓報仇雪恨,天南地北任穿行,再也沒有人阻得了,待那時,若要找到李愚和小桃桃他們,那就容易得多了。
想到這裏,頓時信心倍增。
過一層皂紗,可以發現,的臉漲得緋紅,額頭上還時不時冒著大汗,將離暗自一笑,引道:“你確定嗎?還沒到山腰呢!我怎麽覺得你已經有些吃不消了呢?”
白餌登時有些激:“你恐嚇我!我不吃你這一套!我輕如燕,無所負累,輕鬆得很!”
了臉頰,隻覺得有些發燙,這種燙是從臉頰一直連著耳的,此外,不知為何,耳朵邊一直響著一句話:“那我要你做我將離的人......”
反反複複,複複反反。
春風一路吹,送我上碧霄。
在將離各種“詛咒”與不斷打破“詛咒”下,白餌終於登頂了,事實證明,沒有倒下。
隻覺得得不行,嚨被火燒著了似地,口幹舌燥,全都散架了,白餌一手撐著腰,一手扶住了近的一棵歪脖子樹,想說什麽,卻已經無力說出口了。
將離抱著臂膀站在麵前,滿臉皆是悠然自得的樣子,不帶的那種。見白餌累得夠嗆,他傾下子去詢問狀況:“白俠,您還好嗎?”
著實有些不放心,便走過去攙著坐下,教如何打坐,如何坐禪,如何調理子。
清風一陣接著一陣吹來,令頓時神清氣爽,摘下鬥笠,對著天大喊:“我賭贏了將離——”
青天白雲仿佛近在眼前,隻需稍稍手,便能夠著。極目遠,一整個秦淮盡收眼底,平時那些再悉不過的地方變得格外渺小。秦淮河邊上的城牆竟是一條線,朱雀街就像一張地圖,被裁減一塊塊方方正正的圖形,井然有序地擺在那片土地上,當然,這張地圖的主調是白的,因為雪,隨可見。
白餌頓時有種俯仰眾生的覺,或許登上了頂峰,才能知道這個寰宇有多麽得渺小,上的責任有多大......
見笑得花枝,將離撇撇,悶聲道:“贏了我,你就那麽開心嗎?毅力那麽強,也不知道讓著我點兒,就不能故意輸給我嗎?”
“幹嘛要輸給你?”白餌著實有些莫名,朝他笑著問,語間頗是春風得意。“學最厲害的本領不好嗎?”
說著,繼續欣賞遠迤邐的風景。
得見滿臉陶醉的神,他的角也不由自主地微微揚起,好久沒有這般放鬆、愉悅過了,此刻的白餌,才是他最想見到的樣子,若是時能一直停在這一刻,該有多好......
他暗自垂下眸子,眼中是方才走過的漫漫長路。思緒融在風中,格外漫長。
其實,就算輸了賭約,亦或是沒有賭約,他也可以無條件地答應的要求,在麵前,他絕對是“不吝賜教”的。
他也知道,為了將自己變強,為了那些執著的守護,一定會傾盡全力贏下這個賭約的。
這是一場既定的賭約,可是他還是一步步引許下了。
這一刻,他多麽想問,如果沒有賭約,他說出口的那個賭注,可否為他二人之間,永恒不變的約定?
猜你喜歡
-
完結96 章

分手後我懷了大佬的崽
褚雲降和路闊最終以分手收場,所有人都嘲笑她是麻雀想飛上枝頭。幾年後,她帶著兒子歸來。見到路闊,隻是淡漠地喚他一聲:“路先生。”那一刻,風流數載的路闊沒忍住紅了眼圈,啞聲道:“誰要隻做路先生。”
24.9萬字8 25546 -
完結830 章

裴少寵妻成癮
“喜歡我,愛我,眼睛隻許看我!”男人咬著她的唇,霸道宣告。為了讓她留下,不惜逼她懷孕產子。“裴慕白,你就是個瘋子!”她嘔盡最後一滴血,硬生生割裂了和他所有的聯係,他崩潰嚎啕卻於事無補。多年後她於人海中出現,長發及腰笑得妖嬈。“好久不見,裴總,有沒有興趣一起生個孩子?”男人咬牙切齒:“我倒缺個女兒,你感興趣嗎?”
150.7萬字8 4190 -
連載824 章

二嫁頂級豪門,婁二爺悠著點腰啊
領證的路上,言茹茵遭遇車禍,昏迷了三年。再次醒來,丈夫因車禍失憶,怪她惡毒,說她棄他不顧,身邊已另有新歡。 言茹茵對這種眼盲心瞎的男人沒有挽回,離完婚扭頭會所偶遇一個寬肩窄腰、八塊腹肌身體好的小白臉。 小白臉又欲又野,卻不要錢要名分…… “寶貝,你快跑吧,我跟我老公還在冷靜期,這點錢你拿著,我怕他打你。” 言茹茵丟了支票就跑了,電話都沒留。 第二天,言茹茵跟冷靜期的丈夫參加婁家家宴,見到了那位傳說中神秘狠辣的婁二爺。 男人將她抵在墻角:“錢我要,人也要!都是我的。” 言茹茵驚:“二,二哥??”
144萬字8.18 95736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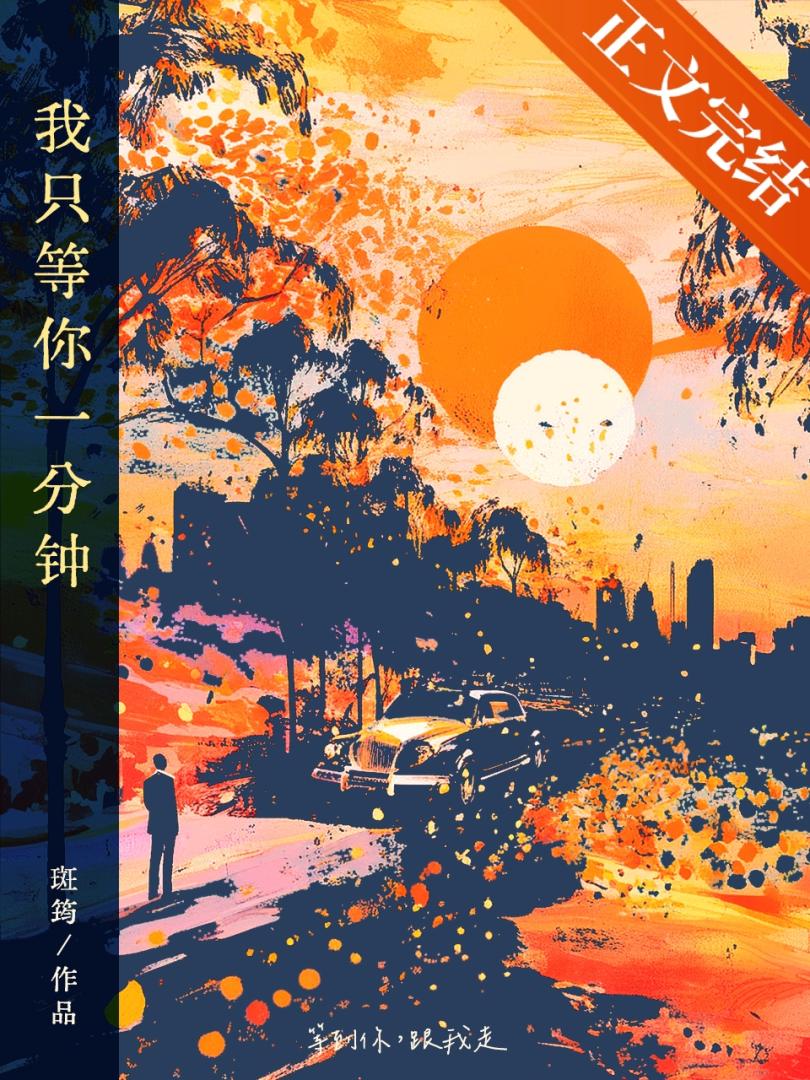
我只等你一分鐘
為躲避催婚,卿清也開始聽從母親的安排相親,意外與萬俟延相遇。此時的他已經成為新聞報道裏的科技新貴,中國最強游戲制作人,美國海歸,同年少時大為不同。卻是一樣的氣質冷峻,淡漠疏離,仿佛任何人都無法輕易靠近。決定領證時,二人已有6年未見,卿清也稍顯猶豫。她站在民政局門口思考,還未等捋清思路,便看到有人迎面走來,臉色冷冰冰的,足足盯了她5秒鐘,才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問她:“不進來,站在門口做什麽?”這目光帶有重量,卿清也忍不住後退,忽聽他開口:“你可以現在走,走了就沒有下次了。”卿清也的腳步倏地頓在原地。緊接著,她聽到身後人語調平靜地說:“我和你,只有做夫妻和陌生人這兩道選項。”*在外人看來,這兩人一點都不搭、一點都不合適,他們的婚姻就像是兒戲,遲早要完蛋。但卿清也并不覺得,他們約好了不告訴父母,也不互相幹涉,并且萬俟延領完證就飛往國外工作,一去就是許多天。卿清也也開始忙起泥塑事業,沉醉忘我,晝夜顛倒,全然忘了自己已婚的事情。然而某天她忽然收到一條消息——【夜不歸宿?】這條尚且還讀不出那人的情緒。可間隔半小時後的下一條,萬俟延又給他發來一則消息,是一個簡單的“?”。小劇場:①某天,卿清也接到她母親的電話,徐蕙蘭氣勢洶洶地問她:“檔案上顯示你已婚,是怎麽回事?”卿清也裝傻充愣:“你聽誰說的?”徐蕙蘭:“警察。”卿清也:“假的,別信。”徐蕙蘭:“......你最好給我一個解釋。”②兩家父母來找他們討要擅自結婚的說法。卿清也把萬俟延拉到一旁商量對策,她沒想到會遇到這麽棘手的場面。還沒商量好,就見萬俟延轉身走到父母面前,隨即,卿清也聽到他說:“爸爸媽媽們。”他的態度端正,讓對面的父母們也不自覺正了正身子。卿清也走過去,坐到他身旁,打算聽聽他的解釋,下一秒,就聽他說——“我希望你們不要破壞我的婚姻。”卿清也:“......”父母們:“......”一個沒良心VS一個死心眼—————————————————————預收文文案:文案1:家裏即將破産,為幫母親分擔債務,郁芣苢答應去相親,一路猶豫不決地在酒店盡是蓮科名的包廂門前打轉,最後在“芙蓉”和“芙蕖”當中任選一間,走了進去。哪知,繞過黃花梨木嵌雲石插屏,卻看到對面露出一張矜貴清冷的臉。他正在接電話,聽聞動靜,冷冷地朝這邊掃來一眼。郁芣苢慌忙道歉:“抱歉,我走錯包廂了。”轉身就跑。薄言初本在跟母親討價還價,他不理解為什麽這樁生意非得自己來談。待看到誤入包廂的人奪門而出,薄言初趕忙起身去追。正巧,對門也同時打開,他看到“芙蓉”裏頭出來一對挽手的璧人,再看身側郁芣苢臉上露出“大事不妙”的表情,當即明白了是怎麽一回事。想到郁芣苢當初同自己提過的分手理由,薄言初當即沉下臉來,質問她:“你來相親?”“你跟他就合適?”*搞砸相親的當晚,郁芣苢抓著手機思考該如何同母親交代,意外翻到了分手那天薄言初給她發來的消息:【你考慮清楚了嗎?】時間來自半年前。郁芣苢深思熟慮後,冷靜地給他回複:【我考慮清楚了,我答應跟你結婚。】薄言初不理解,并且很快地給她回來一個無語的“?”。*常年潛水、一言不發的薄言初,某天突然在家族群裏發了一張自己的結婚證照片。薄母先是鼓勵式地對他表示了真心的祝福和恭喜。過了三秒,意識到不對,又發來:【不是,兒子,配偶欄那裏的名字是不是不太對?】文案2:薄言初一側過臉,不看她,郁芣苢就知道他生氣了,不想搭理自己。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她就會把平日憋在心裏強忍著沒說的話沖他一頓瘋狂輸出。等到他終于忍不住皺起眉回看自己,想問她是怎麽回事之時,郁芣苢就會翻臉一樣,笑著對他說:“別生氣了嘛。”一個忘性大VS一個氣性大內容標簽:都市情有獨鐘青梅竹馬婚戀業界精英輕松卿清也萬俟延(mòqíyán)郁芣苢(fúyǐ)薄言初其它:@斑筠在流浪一句話簡介:等到你,跟我走立意:成為更好的自己
22.8萬字8 815 -
完結348 章

認錯白月光后,我慘死,他哭瘋
在向我求婚的游輪上,傅寒燚將兩億天價的鉆戒,戴在了養妹的手上。那時我才知道,這個對我謊稱得了絕癥,讓我拼死拼活為他攢錢買續命藥的男人: 竟然是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金融大佬。 可他偽裝成窮人,玩弄我的真心。 他把我賣血換來的天價藥,一顆顆扔在地上,讓我被他們的上流圈子嘲諷。 他們說,窮人的真心可笑又廉價。 在生命消逝前的幾分鐘,我不甘心的打電話向他求救,他卻讓我去死。 我終于歇斯底里:“傅寒燚,明明是你隱瞞身份對我戲弄,為什麼你卻像個批判者一樣堂而皇之的踐踏我?” 他輕蔑一笑:“溫媛,等你死了,我會在你墳前告訴你。” 如他所愿,我真的死了。 可當他發現我的尸體被迫害得慘不忍睹時,整個人卻咆哮了。 再醒來,我重生在她人的身體里。 傅寒燚跪在我的墳前懺悔:媛媛,欠你的,我很快就能還了……
57.7萬字8 78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