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為餌》 第034章 少年,大智若愚
的話好像提醒了他什麽。離開東宮之時,他並沒有代阿信他的行蹤,試想,一來,有太子令牌在手,若有意外發生也可從中轉圜,二來,他若沒有及時回轉,便按照之前的法子,掩人耳目一天,但若超過一天定會引起父皇的疑心,所以他最多隻有一天的時間。既囹圄,無論如何,都要試一試,他等了這麽多天,如今機會就擺在眼前,自然不能錯過。
“我打算試一試,看看明天能否找到線索,若無線索,我再想辦法。”漠滄無痕道。
“好,”白餌對上年堅定的眸子,繼續道,“我比你呆在這裏的時間久,這周邊的況多了解一些,你若信得過我,我可以掩護你。”
漠滄無痕愣了愣,他從未想過會幫他,即便自己沒有表明太子的份,仍舊毫無心機地想要幫他,幫一個才認識不到一天的陌生人。
漠滄無痕朝點點頭,眉宇間引來一陣清風。他知道,果然和別人不一樣。
“對了,聊了這麽久,還不知道你什麽名字呢?我白餌,食耳。你呢?”
食耳,這個名字倒是十分有趣,漠滄無痕頓了頓,笑著回道:“我李愚,愚蠢的愚,我的父親說我從小就特別笨,所以喚我李愚。”
聞言,看他說出這話時,臉上竟是一副傻傻的樣子,再聯想他之前那些搞笑的言行,白餌忍不住笑出聲來,然後又故作鎮定:“你這人真逗,這世上哪有自己的父親會嫌棄自己的孩子笨呢?我看呀,你父親分明是想表達,大—智—若—愚。”
漠滄無痕淡淡一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不再作聲了。他靜靜著那明月,眉宇間染上了淡淡的哀愁,其實,眼前的況比他料想的還要糟糕,偌大的囚奴囹圄他要找的人究竟會在那裏?那個人是否安好?那個人是否也正守著同一明月,靜靜等待著再次相聚的那一天?
Advertisement
月如水,流淌了一夜。
而太子令牌就像針落大海,遍尋無果。
天漸漸破曉,整個囚奴囹圄朦朦朧朧的,如同籠罩著銀灰的輕紗。這時,萬籟俱寂,突然有了一聲鳥,劃破了這寂靜。
臉上忽然一陣冰冷,好像被什麽輕輕點了一下,白餌微微睜開眼,長長的睫凝結著碎碎的冰晶,視線已然有些模糊,但能注意到頭頂的樹枝上立著一隻鳥,樹枝似乎太冰冷,沒站穩的鳥嚇得飛出了視線,同時帶下了些冰棱子,冰棱子悄無聲息地掉在雪上,發出了“沙沙”的響聲。
白餌收回迷離的視線,發現原來已經天亮了。坐了一晚上,一半冰冷一半暖和的子此時已經僵地不能彈。
被後若有似無的作驚醒,漠滄無痕也漸漸蘇醒了,休憩了許久,困頓的眼睛已然重新恢複了明亮的澤。漠滄無痕側著臉,輕輕問:“你醒了?”
聽到耳畔傳來的聲音,白餌意識到,與年竟不知不覺地背對背靠了一夜,冰涼的臉龐忽然生出了些許溫度。白餌點點頭,很自然地回了一個“嗯”字,許是剛睡醒,警惕心並不是很高,這聲音聽起來竟有些.....
白餌褦襶地搖了搖頭,飛快地丟了那些七八糟的思緒,單手支著石頭,幹脆利落地站了起來,轉走到年邊朝他出一隻手:“天快亮了,我們得先避避,不然待會你就會被風人發現的。”
漠滄無痕的視線輕輕定在白餌的手心,臉上出安然之,然後將手落於瘦小的掌心,小心翼翼地起,疑地問:“你可有什麽辦法?”
“這裏的囚奴腳上都會被鎖上一條鏈子,你若這樣貿然出現在風人的視線中,定會引起風人的懷疑,前天和我共一個牢房的朋友了鏈子伺機離開了,你和他的形差不多,你跟著我回牢房暫時頂替他,風人一時半會發現不了的。”白餌一邊打量著年,一邊慢條斯理地回道。
年的眼神落在臉上良久,半晌沒有回應,顯然,剛才說的話,他沒有完全注意。白餌好奇的眼睛朝年眨了眨,剛想試圖猜測他為什麽這樣看著自己,誰料,一隻手指猝不及防地落在自己的臉上,然後輕輕點了點,一抹溫暖瞬間代替了潛伏已久的冰涼。
白餌很不自然地後退了一步,年指尖沾著的那抹碎冰,頃刻間打消了眼裏的慌張和疑慮。場麵一度尷尬,白餌踱著僵的步子,側著子領著他走在前麵,裏出幾個字:“快走吧!”語氣顯得格外輕鬆。
漠滄無痕將手指從空中收回,朝白餌點點頭,然後毫不猶豫地跟了上去,一抹冰涼在他掌心安靜地暖化著。
此時,囚奴囹圄的牢門已經被負責早起開門的風人打開了,由於天還沒徹底地亮,那條本就不怎麽亮的通道黑沉沉的,像一隻的怪正張開著盆大口,想要把人吞噬。
不過眼前越暗,對白餌和漠滄無痕來說,卻是越有利。兩人踩著貓步一點點來到牢門,趁著開門的風人去方便的時間,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了那條通道。黑暗裏,生怕年走散,顧不上避諱,白餌已經拉上了年的手,憑著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索著進了牢房。
初牢房,一潑天的臭味從四麵八方突襲而來,一寸寸淩遲著漠滄無痕的口鼻,出於本能,一隻手已經鎖住了漠滄無痕的半張臉,隻留下一雙遲疑的雙眼,正不可思議地窺視著周遭的一切。
一堆枯黃的雜草,再加上幾塊簡單的板子,便搭了一個讓一群人睡得安然自得的床鋪。床鋪上躺著的那些人,有的鼾聲如雷,有的著眉不安地撓著,有的佝僂著子在一個角落像個活死人......一幕幕目驚心。
漠滄無痕蹙著眉,無意再看下去,而是把視線定在白餌的影上,支支吾吾地問:“你,你每天就睡在這?”
手裏已經拿到了將離掙時留下的鎖鏈,白餌跪在枯草上,準備將年的雙腳鎖上。
“是的。”白餌淡淡地回道,忙碌中不抬眸看了眼年,年這個反應並沒有給帶來太多吃驚,畢竟他是富貴人家出,這種地方估計這輩子他都沒待過更沒見過。
漠滄無痕乖乖地任由白餌擺布,看著下的白餌,眼裏寫滿的不可思議遲遲難以淡去,隻不過是一個子,卻要在這樣的困頓中存活,這是何等的不易!可偏偏他卻從未在眼裏捕捉到任何關於害怕的東西。
“待會你就躲在我後,無論發生什麽都不要出聲,以免引來風人的注意和懷疑,”白餌一邊囑咐,一邊將鎖鏈的斷口用一韌度很好的鐵暫時鎖住,“腳銬我暫時幫你虛鎖了,如此,就不會被風人發現了!”
被白餌眼裏的自信和樂觀容,漠滄無痕也收起了眼中的困和不安,朝白餌點點頭。
兩個人挨著牆,開始坐了下來。
不久,送早食的風人來了,那些沉睡的男囚也陸陸續續起床了,意外的是,最先起來的是王福。
王福睜開眼,隨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猛地起,往牢房裏掃了一眼,悉的影再一次跳了出來,王福心裏不免一驚,臉開始變得很難看,於是走下床鋪,厲著眼冷嘲:“幹了一天一夜的活,你竟然還沒累死在外麵,真是小瞧你了!”
自昨天從囚奴囹圄外進來,他就一直竊喜,白餌一朝為風人眼中釘,他也不用再對心生敬畏,這個牢房的主權也終於可以回到他的手裏了,可恨既沒累死,也沒凍死,還安然無恙的回來了。
自昨天的事後,白餌就已經認清了王福,從他剛才看第一眼起,就沒想過要理他,理一個小人。如今撕破臉說出這種話,也完全不當一回事,隻是自顧自地拿了兩個碗,一一往裏麵盛粥。有幾個男囚見到白餌,如見債主,默默躲在一旁。
牢房裏一時靜得可怕,每一個謹小慎微的作仿佛都能聽清楚,這無異於一刺,無形地紮在王福的臉上,王福睜著一雙怒目,靜靜看著白餌的一舉一,心裏的火氣一丈一丈燒了起來。
白餌蹲下子,淡漠的眼神注視著兩個手裏的粥碗,正要將一個碗往年邊送,忽然,一個手從天而降,碗還沒到年手邊就已經打翻在地。
其他人的眼睛齊刷刷地往同一個方向掃去,同時把手裏的碗攥地的。
白餌先是怔在原地,然後眸一寒,猛地抬眸,烈焰般的目直直向王福。
“怎麽了?心裏不舒服?”王福高高抬起頭,角勾起一冷笑。這一摔,就像給自己心裏澆了一盆水,是把那一丈丈怒火給澆滅了。然後瞥了一眼下的白餌,丟給一個警告:“以前是我給你麵子,任由你放肆。但我王福向來大度,過去的,我也不再追究。從今往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各各的苦,如今我要管的事,我勸你最好不要手!”
白餌忿忿地收回目,角慢慢浮出一笑意,繼續把另一隻碗送到年的手裏,若無其事地朝年笑道:“快喝吧!”
漠滄無痕掃了眼地上的碎片,好像明白了什麽,一切如他所想,一個子要在這男囚中生存確實不易。看著白餌一臉的鎮定之,漠滄無痕眼裏也浮現出一抹笑意,點點頭,然後接過粥碗,迅速地喝下半碗,再把粥遞回白餌手中,點頭示意喝完。
白餌接過碗,坐到年邊,在年的注視下,將頭埋下,輕輕喝了一口,那一刻,心裏竟有說不出的味道。
明明在弱勢,還那副怡然自得的樣子,而那個新來的人也並沒有被嚇到,見到這一幕,王福心裏剛熄滅的火焰,不可控似的,再次死灰複燃。
王福轉視了一眼那鍋粥,眼睛瞪得滾圓,意有所指地朝漠滄無痕命令:“你去把我的粥盛過來。”說話的聲音如寒冰刺骨,帶著咬牙切齒的聲音。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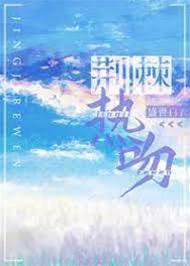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