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歸錦》 第262章 有備而來
府衙之,公堂之上,楚知南坐於高位,兩側點了許多火燭,將公堂照亮得猶如白晝。
楚知南曾坐過刑部公堂,這等府衙公堂,毫不覺有任何不妥。
公堂之下,伍元魁等人被於堂下,幾個商賈已冷汗連連,生生不敢哼半句聲。
伍元魁為朝廷命,倒可不必下跪。
遂州刺史汪慶洪則站在了楚知南左側,唐柳站於右側,衙門裏的衙役已換了兵。
楚知南拿起手中驚堂木無趣地把玩著,先是晾了他片刻,而後再笑著道,「你可知,本宮為何而來麼?」
伍元魁腳步有些虛晃,子險些站不穩,極力替自己爭辯道,「殿下,何文貴之事,下早已將宗卷給了刑部,所有證據一應俱全,明明是他趁著自己份為師不仁,如今那人證還在城,您若不信,大可將人證給喚上來對峙!」
「呵呵!」楚知南輕輕一笑,也不知有沒有聽進去他的話,只又問道,「何文貴之妻,白氏之事,伍大人可否將事宜說得更清楚些?」
伍元魁既能犯下這等大惡之事,便說明絕對不止會做下這一件。
已派人去查了這些年他所判下的案子,如今只需揪著白氏之事便可讓其輕易摘掉頭上烏紗帽。
何文貴所說是真是假,著實還存在了疑慮,但伍元魁瞧著也似個狗,這手裏定是不幹凈的。
Advertisement
「白氏~」提及這個稱呼,伍元魁瞳孔一,「回殿下的話,白氏主勾引下,又在下酒飯之中下了葯,事之後妄想企圖以此威脅下,下秉著公正執法的命令,不想因此妥協。那白氏見計不,便反咬下一口,將下推至了風口浪尖之上!」
他說完此話后,下意識去看楚知南表,見其仍舊只盯著而看,未有半點緒,心裏的慌張更甚,隨即再接著道。
「白氏乃是鄉野人家的子,大字不識的幾個,也未見過世面,、就是垂涎下份!」
楚知南將驚堂木放在了堂案上,點點頭,很是認同,「也是,那白氏不過是個村婦罷了,大字都不識得幾個,見得知府大人,怎會不產生些心思呢?」
聽楚知南順著自己的話說,伍元魁滿是認同點點頭,「殿下所言甚是!」
然而,楚知南在他話落下之後便又將話鋒一轉,「那本宮倒是好奇了,既然如此,這白氏又是如何會識得伍大人你呢?白氏不過是一個山村野婦,自未來過遂州,何文貴在城開了一家武館,雖說廣收門徒,卻也一直未與府有任何牽連!
伍大人,你說白氏嫁給何文貴不足半載,又是從何認識了你,甚至、有機會來加害於你呢?不如伍大人你好好將此事經過,來說與本宮聽個一二?」
伍元魁的確沒想到有朝一日此事會被重新拿出來說,也未料到問得問題竟是如此刁鑽。
幸好,幸好他之前有一手準備。
是以,他眨了眨眼睛,想了想先前早已準備好的說辭,而後道,「回殿下的話,下去酒樓用飯時,在大街上見有男子調戲於,便親自上前呵斥了那個浪子。白氏知曉下份后,便無論如何地也要謝下,下見得心思醇厚,便了幾分防備,哪料此人竟是有備而來……這才、這才……」
對朝廷命下藥,此事若是立,白氏還真是有九條命都不夠死。
伍元魁並未否認自己對行下了不軌之事,只是將此事推於被白氏下了葯罷了。
眼下白氏死無對證,活著的人又是他的人,若非在絕對的權利面前,此事還真真就難以翻案。
楚知南聞言無於衷,反而是瞇了眸子,「伍大人真是……好呢!」
話落,輕輕道,「既然伍大人不肯不實話實話,罷了,本宮也只好、上上刑了!」
此話說完,便見兩個將士抬著刑上了公堂。
南燕是個以仁治國的國家,並未有慘絕人寰的酷刑,那兩個將士所抬上來的無非是些各類刑,要不得命。
刑一上,伍元魁立時戰戰兢兢,面劇變,「你、你這是要屈打招麼?殿下,下好歹也是朝廷命,你若沒有證據,豈可用私刑?」
「誰說是給你上的?」楚知南似笑非笑,看向了那幾個跪著的商賈,「諸位都是遂州城得上名號的商人罷?唔,不知幾位對此事可知曉個一二呀?」
跪在地上的那幾人聞言瑟瑟發抖,只覺嚨干啞異常,「回、回殿下,草民不知!」
「你們怎麼會不知呢!」楚知南起,下至公堂,彎腰從刑上挑挑揀揀,看上了一條緶子,拿在手中試了試它的材質,而後走至了一個商賈跟前,緩緩蹲下,笑著與其平視。
「在那花樓里,閣下不言之鑿鑿的呢?既然你知曉個一二,那不如你說給本宮聽聽,可好?」
楚知南所挑的那人,便是喝得微醺,試圖要來教訓的人。
他此時酒意已全醒,就算跪在地上,仍舊雙打、渾哆嗦。
「草、草民不知!」
「怎麼?莫非本宮是母老虎不?閣下怕如此,是怕本宮將你給吃了?」楚知南溫一笑,吶鞭子手柄輕輕著他的肩膀,「本宮素來最喜講道理,也不會公報私仇,你們嘛,都是咱們南燕的老百姓,又沒犯什麼錯,本宮怎會傷害你們呢!」
那手柄在他肩上,明明沒有半點疼痛,卻又好似一把利劍刺皮一樣,異常驚心。
他著實不知如何應對,便只跟楚知南磕頭哭著求饒,「草民什麼也不知曉,殿下饒命,殿下饒命!」
「你是做了虧心事不?」楚知南無趣的搖搖頭,喚了一聲汪慶洪,「刺史大人,去查查這位的底子,若是不幹凈麼,直接抄家送大牢罷!」
汪慶洪聽得,於一側不卑不地應了一聲是。
而那商賈聞言,立時癱瘓在地,「殿下息怒,殿下息怒,草民什麼都說!什麼都說!」
楚知南嘖了一聲,「奉勸大家一句,還是識時務為俊傑的好,本宮此來乃是為何文貴一事,旁事不想參與,但若諸位不甚配合,那、本宮也只好一併都查辦了!」
。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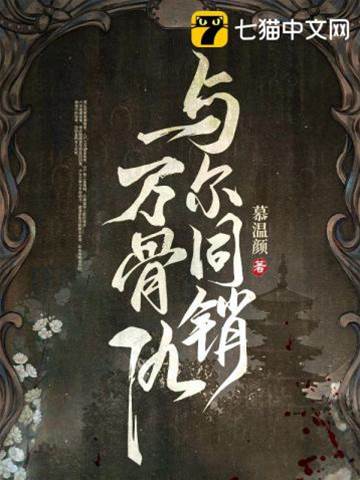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