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書後,對偏執大佬撒個嬌》 第805章 是他們給了她信任祁夜的勇氣
蘇糖離開的時候,下意識四看著,想看看能不能看到祁夜。
祁夜和孟悠悠前後腳出去,他們會去哪兒呢?
他的計劃到底怎麼樣了,會功嗎,孟悠悠會上當嗎?
要是他找不到那個對他而言很重要的人怎麼辦呢?
值得讓他這樣和孟悠悠周旋的人,到底會是什麼人呢?
有很多問題,也想發個消息問問,又怕會打擾到他,影響到他的計劃。
畢竟他這會兒可能是和孟悠悠在一起的,所以到底還是忍住了。
只是一路出去,也沒有看到祁夜和孟悠悠。
難免有些失落,當然,更多的是對他的擔心。
不過也不敢去找他,還是跟著晚上了車。
也不知道自己現在為什麼能這麼信任他,在孟悠悠跟說過那些話后,還是選擇相信他。
這在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可現在想的就是,不管真相是什麼,也要他親口告訴才可以。
Advertisement
只信他的話,其他的,謝子越也好,孟悠悠也好,都不信。
回去的路上,蘇恆開車,心菡坐副駕駛,母倆坐在後排。
先把心菡送回了家,這才轉道回蘇家。
車裏沒了旁人,晚才呵了聲,「沒想到還大方的,這是第二個億了吧。」
蘇糖裝作聽不懂,低著腦袋不說話。
蘇恆倒是皺眉,「什麼大方的?」
晚便笑了,「你未來婿大方的,那顆戒指的錢他已經給了。」
「什麼?」
蘇恆手一抖,方向盤一歪,車子朝右一偏,差點嚇死蘇糖。
蘇糖忙開口,「爸你好好開車。」
蘇恆磨牙,「回去給你老子好好代,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
蘇糖咬不敢說話了,晚翻了個白眼也沒再說什麼,怕影響他開車。
車裏變得很安靜。
過了兩分鐘,蘇糖轉頭看向車外。
忽然覺得天沉沉的,出酒店時還能看到星月,這會兒竟都被雲層遮蓋住了。
像是要下雨了。
本就不安的心更是加劇,就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一樣。
就這麼一路回到了蘇家,蘇恆一下車就沖得老快,一副老子很生氣的樣子。
蘇糖看著他的背影有些遲疑,晚倒是拉住的手,「你爸就這個樣子,別怕,老老實實代,不會有事。」
蘇糖有些遲疑,糾結道:「代什麼呀,我自己都不知道。」
晚,「……他和孟悠悠什麼況你不知道嗎,不知道你還拿人家一億的戒指?」
晚也有些無語了,蘇糖抿抿,「他只是跟我說,他要找個很重要的人,那個人只有孟悠悠知道在哪兒。」
說完,見晚臉不好,忙又道:「不過他說了,他不會和孟悠悠有什麼的,他現在只是在拖延時間而已,等他那個朋友到了,他們就能開始計劃了。」
晚恨鐵不鋼的額頭,「他說什麼你都信?」
蘇糖噘,「我信他總比相信敵的話好吧,難不,敵還能為了我好嗎?」
晚皺著眉想了想,「他倒是也跟我們說過,有很重要的事必須要做。我倒是不信他和孟悠悠能有什麼,畢竟之前那事兒……」
頓了頓,道:「正常男人都不可能,更何況祁夜那樣的人。」
很嚴肅的看著蘇糖,「我只是擔心,如果他把其他的事看得太重要,你會到傷害。我們希,你能找到的人,是把你看得比任何東西任何事都要重要的。」
說到這裏,又嘆了聲,「不過說到底,這也只是我們理想的狀態而已,這樣的人太難找了。人活在這世上,都有很多無可奈何。」
晚理了理蘇糖耳邊的頭髮,又嘆,「反正事也已經這樣了,那就看看他到底想做什麼吧。總歸你要記住,不管發生什麼,媽媽和爸爸永遠都在你邊。如果他真的讓你難過了,你也不需要為了一個男人委屈自己,明白嗎?」
蘇糖咬,片刻后,輕輕點頭,「我知道的。」
晚這才道:「這事兒我去跟你爸爸說,你先回自己房間去早些洗澡睡覺,別胡思想了,小心又頭疼。」
蘇糖「嗯」了聲,「謝謝媽媽。」
一直都知道,的父母是最大的底氣。
是他們給了信任祁夜的勇氣,因為不怕傷,因為有人可以依靠。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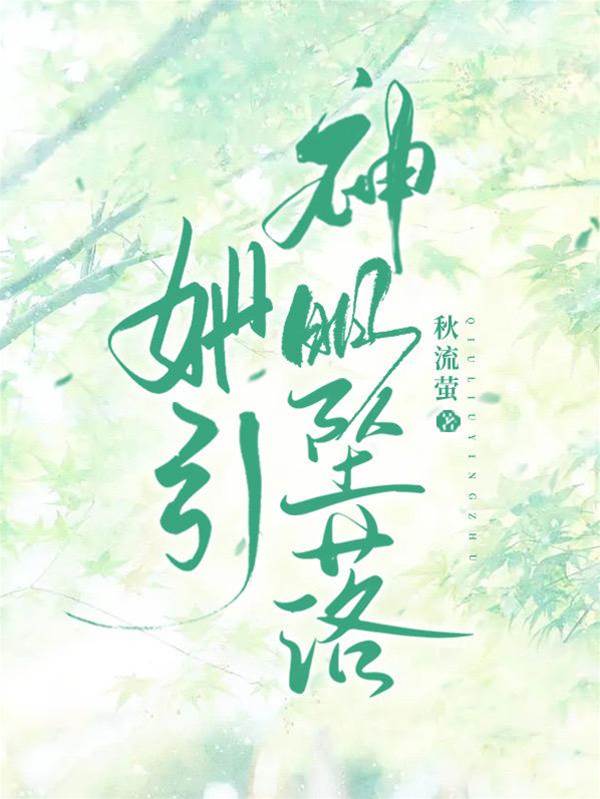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