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狀元》 第二五八三章 爲害一方
謝遷沒有直接在張懋面前表態讓沈溪回來,不過顯然已了這方面的念頭,且已準備付諸實施。
而此時朱厚照在徐州城毫也沒有離開的意思,躲在行在三天後便開始外出遊玩,只是子突然變得乖戾起來,跟惡一般帶着大批侍衛招搖過市,甚至帶人徑直士紳宅院,雖說沒有直接搶人或者搬東西,但所做作爲讓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苦不堪言。
Wшw ¤тт kǎn ¤C O
因爲皇帝份沒有暴,很多世家大族起反抗,但因家僕數量無法跟朱厚照所帶侍衛抗衡,數次衝突中均被朱厚照帶人闖家宅,便到府告狀,可惜員都知道乃是皇帝所爲,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管不問。
在這件事上,被皇帝拋到一邊的唐寅、蘇通和鄭謙三人毫無辦法,他們雖有心勸阻,卻不知該從何着手,因爲司禮監掌印張苑一直在旁推波助瀾。
張苑知道現在皇帝心不好,之前地方有關迎駕安排不合朱厚照心意,他便想出個主意,讓朱厚照扮演一回“惡”,過一把爲非作歹的癮,有意爲難地方紳。
本來早年朱厚照便在京城做過強搶民之事,雖時過境遷,但再做這種事居然駕輕就,毫也不覺得有什麼過分。
朱厚照嬉鬧兩天,沒做太出格之事,卻讓徐州紳跟防賊一樣,只要稍微有點資產的人家便會加強門,大白天也房門閉,想盡辦法加強護院人手,同時派出奴僕到街頭打探消息,一旦聽說有誰帶人招搖過市便早做準備,把家裡值錢的東西和人藏起來。
第三天早上,朱厚照出來一趟,便沒進到任何一家人房門,有些百無聊賴。
Advertisement
中午在一酒肆吃飯,張苑過來跟朱厚照報信,並非朝事,而是告訴朱厚照城裡哪些人家戒備不足。
朱厚照道:“你說這兩天經朕這麼一鬧騰,徐州應該人人自危了吧?”
張苑被朱厚照說得一怔,他沒想到朱厚照居然會有如此“自知之明”,趕道:“陛下察民,深百姓家中,與民同樂,他們爲何要人人自危?”
朱厚照眯着眼,面深沉:“你這不是明知故問?朕那是察民嗎?拍馬屁也不是你這樣拍的……朕本來就是想在城裡製造點事端,找點樂子罷了……朕實在是閒得無聊……”
張苑一時間不知該如何跟朱厚照對答,生怕說錯話被皇帝怪責。
原來皇帝知道自己所做並非善事,如此一來想要繼續忽悠下去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朱厚照再道:“下午不去那些人家,改去府逛逛……嗯,就到州府衙門擂鼓鳴冤,說這兩天城裡有賊人出沒。”
張苑瞪大眼道:“陛下,這算……哪一齣啊?”
朱厚照笑道:“就當是賊喊捉賊吧!朕不算是賊,純粹是爲了好玩……城裡這幫員不是喜歡替朕張羅嗎?朕就讓他們吃點苦頭,看以後朕所到之,那些地方誰還敢來……他們不讓朕過好日子,朕也不會讓他們消停。”
……
……
朱厚照果然說到做到,吃過午飯就到衙門報案,檢舉揭發的對象居然是自己,這種事讓徐州地方員聞所未聞。
徐州知州怕跟朱厚照照面,乾脆稱病不出,派出同知來接見,表面上還要裝作不認識,面對皇帝遞出的冤的狀紙,表現出一副重視的模樣,畢竟涉及員政績,一點都不敢疏忽大意。
朱厚照沒勉強說一定要見到知州,得意洋洋,先把自己當作苦主,又把自己前兩日所爲添油加醋抨擊一番,這才厲聲喝道:“你跟劉知州說,若不早些破案,將嫌犯一網擒,城裡始終不得安生,百姓日子不好過,就算是你們這些當的不作爲……看看,這麼短時間裡,市井便蕭索許多,民生不易啊!”
“是,是!”
這位徐州同知姓何,乃是弘治六年進士,沈溪要比他晚十二年中進士,但彼此職天差地別。此時何同知除了在那兒拱手行禮外,基本不敢做別的。
張苑見對方不迴應,便用怪氣的腔調道:“我家公子的話,你可有聽到?爲天子牧守一方,需諒民生不易,記得多派衙差上街巡邏,若遇到鬧事的一概抓起來,但別抓錯人了……我家公子帶人上街可不是惹是生非,而是維護市井秩序。”
“知道了!知道了!”何同知按部就班回話,頭垂得越來越低,眼看額頭都快挨着膝蓋了,這種狀況讓朱厚照意興闌珊,一擺手道:“卻不知這徐州地方做事是否妥當,回去看看況吧……走了!”
言罷,朱厚照帶着一羣人浩浩出了州衙,把裡面上上下下幾十號吏嚇得飛狗跳。
等朱厚照走後,何同知趕進去找自家知州,商議對策。
……
……
朱厚照瞎折騰,唐寅和蘇通等人看在眼裡,急在心裡。
對於朱厚照到底要達什麼目的,連一向自詡足智多謀的唐寅都沒看懂,無奈之下只能把這邊的況寫信告之沈溪。
原本唐寅想跟沈溪保持距離,但在張永和小擰子相繼跟他示好,且表達結盟之意後,唐寅終於意識到自己的份地位不在於得到君王多寵幸,而在於自己背後的靠山是沈溪。
若是皇帝有什麼特殊況自己卻不跟沈溪打招呼,等於是自絕門路。
唐寅這邊還在忙着寫信,蘇通已經派人把信函送往新城。
不過二人都知道,就算沈溪看到信並及時回覆,消息一來一回最快也要個五六天,中間發生什麼事實在不好說,必須要先做出應對。
蘇通沒有主意,只能登門求教唐寅。
唐寅儘管也沒看懂皇帝的用意,但在蘇通面前卻表現出一副一切盡在掌握的姿態。
唐寅道:“陛下此舉看似胡鬧,卻也暗藏深意,你還是別多問……陛下若有吩咐照做便可。”
蘇通聽得雲裡霧裡,道:“唐先生準備如何應付?陛下可是對你有所待?”
唐寅搖頭道:“陛下這幾日都自行出遊,未曾讓我等隨駕,不過這種狀況應該持續不了幾日,稍後便會有結果……你早些回去吧。”
蘇通見唐寅表現出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只能匆匆告辭。
唐寅則滿腹疑,本看不懂朱厚照出什麼招,而眼下徐州城的確鬧出不子,唐寅作爲皇帝跟前的“謀士”,對此無能爲力,實在是有些汗。
……
……
本來唐寅以爲消息至要兩三天後才能傳到沈溪耳中。
但其實朱厚照在徐州城帶人鬧事的次日沈溪便已知道事的前因後果……這得益於沈溪麾下報系的完善,用飛鴿傳書的話,一千里的距離,只需兩三次信鴿接力便可完信息傳遞。
雲柳把這件事告知沈溪時,非常着急,畢竟此前沈溪就表出對皇帝胡鬧的擔心,很害怕朱厚照回京途中出什麼意外……雲柳跟唐寅一樣也看不懂皇帝的用意。
沈溪剛開始還以爲發生什麼大事,弄明白朱厚照並不是跟歷史上那般突然對打漁發生興趣,獨自到大江大河泛舟撒網,便放下擔心,無所謂地擺擺手:“陛下這兩年多有些收心養,雖說他擅闖民宅,卻沒聽說他有擄劫民、奪人家財之舉,說明他行事還是有底線的。”
雲柳急道:“可是大人,陛下一天之出好幾戶人家,聽說還打人砸東西,惹得徐州民衆敢怒不敢言。”
沈溪道:“他要強進民戶,遇到阻攔自然會起衝突,加上他邊侍衛都是從江湖上招募的武林高手,肯定打得那些護院落花流水……其實他若表份,天下間哪裡去不得?所到之肯定是跪倒一片迎接。說到底,陛下不過是把這當做一件好玩的事,並不是真的作犯科……”
“那大人,此事當如何置爲妥?”雲柳平復心,好奇地問道。
沈溪微微搖頭:“陛下此舉暫時看不出有何目的,不過想來應該跟徐州地方準備的迎駕方式不妥有關,陛下前幾日閉門不出,眼下變爲‘淨街虎’,不過是陛下震懾地方員的一種方式。”
“雲柳,其實你不必把事看得太過嚴重,地方府不可能坐視不理,肯定會好好善後的……放心吧,出不了大事。”
雲柳道:“陛下如今尚未回京,朝中有太多不穩定因素,若陛下在徐州一直做擾民生之舉,就怕朝中非議聲加劇……”
沈溪皺眉道:“你去擔心這些作何?現在除了有人謀逆外,沒人能威脅陛下皇位穩固,就算太后娘娘也沒權力會這麼做……陛下最多是在爲他的名聲抹黑罷了。你讓我一個在外地的大臣如何作爲?”
雲柳想了想,馬上意識到沈溪對這種事實在鞭長莫及。
便在於就算沈溪能做什麼,也只能上奏勸諫,但皇帝本就不聽臣子的意見,叛逆心重,別人不勸或許他還不會胡鬧太甚。
沈溪再道:“過幾天看看事發展到何田地再說吧……此事應該會在一兩天傳到京城,京城那些大佬不可能坐視不理。這回就怕陛下有自己的想法,最後釀的結果,誰都不想看到。”
……
……
正如沈溪所言,事發生兩天後,京城閣首輔謝遷也得知況。
本來謝遷就在爲是否召沈溪回京之事而煩惱,在聽到朱厚照于徐州城胡鬧後,他可不像沈溪那樣有很好的忍耐力,也不會去想皇帝是否另有圖謀,只覺得小皇帝又開始胡作非爲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馬上寫了勸諫的上奏,還拉來朝中大臣聯名,準備直接送去徐州勸諫皇帝。
但關鍵時候,謝遷的行被張太后派人停。
張太后派出的人正是高。
雖然高名義上已卸任司禮監秉筆太監,但畢竟當前司禮監只有他一人留守,在張永、李興或者是小擰子這三人中一人回來接替他位置前,他暫時還要堅守崗位。
高心急火燎來到謝遷小院,見面第一句便是:“謝閣老,徐州無論有何事發生都要當沒聽說過……這是太后娘娘的吩咐。”
謝遷不明白張太后爲何會得知此事,更不理解張太后特別派高來勸說他不要上奏。
雖然謝遷覺問題不簡單,但他不敢當面詢問……高即將退出朝堂之際,謝遷對宮裡這些年老且資歷深厚的閹人越發防備。
高道:“太后娘娘待,讓壽寧侯和建昌侯兩位侯爺前去徐州迎接聖駕,儘可能不讓陛下在外逗留太長時間。謝閣老只管打理好朝政便可。”
謝遷聞言不由皺眉,心想:“張氏兄弟到現在都沒被恢復爵位……太后此舉到底是爲何?”
高沒有跟謝遷過多解釋,匆忙地道:“咱家還要去見兩位侯爺,便不打擾謝閣老了……謝閣老您先忙着。咱家告退。”
謝遷本來有很多話想問,但此時他顯得很謹慎,行禮後送高出門,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
高離開後,謝遷馬上對隨從道:“去戶部把楊應寧來……老夫出去辦點兒事,很快便會回來。”
……
……
楊一清本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來到謝遷的小院之後,他還在琢磨有關上奏勸諫皇帝之事。
過了大概一個時辰,謝遷才風塵僕僕回來,楊一清趕上前見禮。
猜你喜歡
-
完結4306 章
魔帝纏身:神醫九小姐
“夫人,為夫病了,相思病,病入膏肓,藥石無醫,求治!”“來人,你們帝尊犯病了,上銀針!”“銀針無用,唯有夫人可治,為夫躺好了。”“……”她是辣手神醫,一朝穿越成級廢材,咬牙下宏願︰“命里千缺萬缺,唯獨不能缺男色!”他是腹黑魔帝,面上淡然一笑置之,背地里心狠手辣,掐滅她桃花一朵又一朵,順帶寬衣解帶︰“正好,為夫一個頂十個,歡迎驗貨。
385.4萬字8 113543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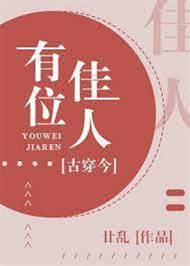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241 -
完結251 章

鳳馭天下:無情狂后
她是二十一世紀某組織的頭號殺手,因同伴背叛而中彈身亡,靈魂穿越到北越國,成為侯爺的女兒。而他則是深沉睿智的年輕帝王,運籌帷幄,步步為營,只想稱霸天下,當無情殺手遇上冷情帝王,當殺手與帝王共創霸業,結果會怎樣呢?…
70.2萬字8 17556 -
完結527 章

穿成五個反派的後孃
一朝穿越,竟然成了彆人的後孃,而且幾個孩子,個個都長成了大反派。究其原因,是因為這個後孃太壞太狠太不靠譜。喬連連汗顏,還好老天讓她穿過來,從此以後溫柔善良耐心矯正,幾個孩子從豆芽菜變成了胖多肉。可就在這時,孩子們的爹回來了。
91.5萬字8 302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