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蘭宮》 50、忘了
婉兮呆呆與語琴回到房間去收拾行李,等月娥等姑姑待會兒挨個送進各自宮裡去認主兒。
語琴明白婉兮一時還回不過神來,便也不擾,隻手腳麻利地幫將行李一併收拾了。
語琴還是開心的,雖說兩個人不在一個宮裡,可總歸都在這一片宮牆之,終究還有個照應。
卻聽外頭有人敲門:“魏姑娘可方便?”
婉兮一聽那嗓音,便登時回神,轉就朝門邊衝過去。
聽出來了,這嗓音是當日在花園裡,拜託過的那個老太監。
門外果然便是敬事房太監包喜。
婉兮一見包喜,便幾乎要跪下去:“諳達,您可來了!”
爲了等包喜的信兒,幾乎已是度日如年。就連在語琴面前,也不敢全都表出來。
——那是一個人兒藏在心裡的,不敢說,怕說出來了,就破了。
Advertisement
包喜也十分歉然:“魏姑娘啊,不是我不盡心,而實在是我人微言輕,而傅四爺又是侯爺,憑我的份怎麼都沒辦法直接見到傅四爺,這纔多用了些日子,費了幾番周折才見到的。”
幸虧傅四爺是皇后娘娘的嫡兄,宮裡太監有所接,中間的人就也都看著皇后的面子。
婉兮已是忍不住子輕:“有勞諳達了。諳達可見著傅四爺了?”
包喜點點頭,卻嘆了口氣:“見著了,總算不負姑娘所託。”
婉兮忽然覺得好冷,這八月天裡,竟忍不住連貝齒都磕撞在一起。
“您把葫蘆墜兒給他了吧?傅四爺他……他怎麼說?他可還,還,還記得我?”
手臂上的傷疤,又莫名地疼了起來。一陣兒如火燒,一會兒又如冰鎮;時而又像蠕起的蟲,麻得鑽心。
包喜半晌沒說話,只盯著婉兮的眼睛:“……不瞞姑娘,我是當面將那白玉的葫蘆給四爺的,又提到了‘九兒’的名。可是四爺說,這葫蘆墜兒他看著眼,可是九兒這個姑娘嘛,他卻沒有半點印象。”
婉兮一怔,連著倒退三步。
手扶一把牆,這才站住。
“四爺他……真這麼說?”
包喜也不忍,連連嘆氣:“我若說錯,天打五雷轟!”
婉兮一直忍著的淚,終於無聲地直直墜了下來。
原來如此,是想多了。也是,不過一面之識,說過幾句話而已,隔了這幾十天去,他又怎麼還會記得?
就算那個葫蘆墜兒是好東西,可是你瞧呀,人家是侯爺,府裡要多白玉的葫蘆墜兒沒有呢,也許滿坑滿谷,隨便就拿起一個賞人呢。
是傻,真的傻了。不是選秀的時候在順貞門上摔傻的,而是一個月前在花田裡邂逅他那天,就真的被蜂子蟄傻了。
蜂毒骨,無法拔除。
虧進宮來那一路上都還想著他,虧一腳使勁趟在順貞門的門檻上時還在想著他;
虧拼了命地想要撂牌子,心裡想的都是他;虧就連方纔想著二十五歲還能出宮時,還在忖著十一年後他是否還能記著……
就是個傻子,自從遇見他之後,便什麼事都傻傻想到他。
可是……人家是侯爺啊,不過是個包子,所以人家上路回家之後,便自然早就忘了了。
是想多了,本就是傻。
婉兮吸一口氣,舉袖狠狠抹一把眼睛。
夠了,婉兮。你現在再落淚,又給誰看?那個心疼你割傷手臂,那個用替你清理傷口的男子,他已看不見,他已不會再用那樣疼惜的目凝視著你……他已,杳遠夢。
紅著眼手:“諳達,那葫蘆墜兒呢?”
包喜一皺眉,爲難地直躬:“姑娘說那葫蘆是傅四爺的,我將葫蘆給傅四爺之後,傅四爺沒還回來,我也便不好再討要……姑娘,你看這可怎麼好?”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香妻如玉
凝香從冇想過自己會嫁給一個老男人。可她偏偏嫁了。嫁就嫁了吧,又偏偏遇上個俏郎君,凝香受不住俏郎君的引誘,於是甩了家裡的老男人,跟著俏郎君跑了。不料卻被老男人給抓了個現行!“你殺了我們吧!”凝香撲倒郎君身上,勇敢的望著老男人。老男人冇殺她,給了她一張和離書。然後,然後就悲劇了....俏郎君負心薄倖,主母欺辱,姨娘使壞,兜兜轉轉的一圈,凝香才發現,還是原來那個老男人好。突然有一天,凝香睜開眼睛,竟然回到了和老男人剛成親的時候。可這一切,還能重來嗎?--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42.4萬字8 11515 -
完結591 章

帶著千億物資穿成大奸臣的炮灰前妻
穿成大反派的作死前妻,應該刻薄親生兒女,孩子養成小反派,遭到大小反派的瘋狂報復,死后尸體都被扔去喂狼。 看到這劇情走向,俞妙云撂挑子不干了,她要自己獨美,和離! 手握千億物資空間,努力發家致富,只是看著這日益見大的肚子,俞妙云懵了,什麼時候懷上的? 不僅如此,大反派體貼化身寵妻狂魔,小反派乖巧懂事上進…… 這劇情人設怎麼不一樣?
103.7萬字8 99967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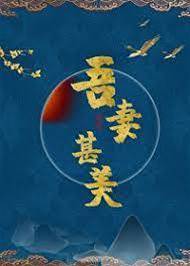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