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許侯夫人》 第2頁
北風穿堂撲來,院中空空如也,連方才還亮的那盞小燈,也搖晃著熄在了燈油里。
“夫人、夫人他們走了?”崇安難以置信。
夫人失蹤之后,他怎麼都查不到夫人的蹤跡,還是侯爺得消息趕了過來,幾下就算到了所謂“竇府”的人上,又沿著這線索找了過來。
他原想著侯爺反應如此迅速,必能找到夫人,誰想到,“怎麼撲空了?夫人就這麼決意要走?”
話音飄,大哥崇平急急瞥了他一眼,他趕閉了。
他看向侯爺,侯爺未言語,抬腳向里走去。他走到那熄了的小燈前,低頭看向燈旁,放著的一把鑰匙。
那是一把銅鑰匙,鑰匙頂端鑄了一座高聳而巧的書樓模樣。
歸林樓,京郊僅次于皇家文瀾閣的書樓,借了工部給宮里筑樓的工匠。
是侯爺給夫人準備的聘禮。
但此刻聘禮鑰匙被留了下來,還特特留在了這里。
夫人是在告訴侯爺,別再找了嗎?
油燈殘余的油煙飄在半空,又刺人的鼻腔。
崇安借著破曉的,看到侯爺垂頭淡淡笑了笑。但侯爺最終沒說什麼,只默然將歸林樓的鑰匙,收到了懷中。
日尚未大亮,就被降落淅瀝小雨的云層擋在天外,檐下昏暗,無人言語,崇安只看到自己大哥崇平在侯爺的沉默中,猶豫著上前問了一句。
“爺,還找嗎?”
*
天未亮就啟了程,這一路順風走得很快。只是順風的路只走了一小段,就到了頭。
不巧得很,他們下晌路過一小鎮,竟然遇上了此地的集會,堵得水泄不通,馬車走走停停,杜泠靜剛把秋霖下車,秋霖就撲到了路邊的樹上,一陣翻江倒海。
杜泠靜自己也不舒坦,往另一邊風大的地方走了幾步,夾在人群中獨自前行,
Advertisement
這兩日走的不快,更多時候在思量如何藏匿行蹤,未出京畿就還在那人眼皮底下。只要能順利潛出北直隸,進到山東地界,便是不回青州老家,也自有的去,可以暫時做停留。但要想離開北直隸,至還得三日。
杜泠靜暗自計算著,不想前面的路口忽然起了一陣狂風。那風裹著沙石飛走,吹得街上擁的行人一時都迷了眼睛。
本就挨挨的街道,立時一團。
有人驚起來,也有人抬手推搡,混之間杜泠靜不知被誰推了一把,可剛往后踉蹌了一步,就被人穩穩地扶住了手臂。
不由道了聲,“多謝。”
說完轉頭看去,只一眼,眼睛瞬間睜大。
男人悉的面龐近到臉前,遠遠近近的人群里,早已布滿他的人手。
杜泠靜知道自己走不了,但還是忍不住轉遠離他,卻被他握住了手腕。
“風太大了,你子不住,別往那邊去了。”
未回,“我并不覺得這條路風大,只要不與侯爺同行,這點風不算什麼。”
說到此,才回頭看了他一眼,“若侯爺肯讓我獨自離去,激不盡。”
男人聞言,嗓音低啞地笑了一聲,“那還回來嗎?”
“既走了,自是不會回。”
“但若是,你已有我們的孩子了呢?”
他目落在的小腹上,頓了頓,才又重新返回到臉上,看住的眼睛。
像是他生了薄繭的手,于昏暗帳中挲在肩頭、腰間……杜泠靜微怔,旋即別開了目。
“無甚可能。”
冷言冷語,冷眉冷眼。
待他,自來連對待前未婚夫婿蔣竹修、蔣三郎,五分之一的溫都沒有,如今更是半分也無。
可同他,才是結發相守的夫妻。
男人越發笑了,低啞的嗓音輕輕笑出了聲。
“娘子對我這樣不滿,真是我之過。”
他搖著頭,自嘲著自責。
擁的人群不知何時被疏散開來,風卷得他額前一縷碎發翻飛。
但他卻在此時更上前一步,近到與咫尺之間。
杜泠靜下意識要退,他卻扣了的手腕。
“我有過,我知曉,可越是如此,我越不能讓娘子離開。佛經有云,若人懺悔,罪即消滅。還請娘子給我機會,允我以此生來懺悔滅過,如此可好?”
每一個字,都隨著他的目,抵至前。
杜泠靜不開他掌心,更不知世上怎會這種人,將懺悔當借口,還說得如此順口。
男人卻只當沒看到妻子眼中的鄙夷,向下握住的手,帶著從遠往回走。
但忽的笑了。
“陸侯會否欺人太甚?從一開始設局得圣旨賜婚,到后來哄騙欺瞞,再到如今特特追來,只為囚我于京。”
哼笑一聲,“敢問陸侯,到底所思何為?”
他陸侯。
男人沒立時回答的話,從懷中取出一方帕子,將帕中包裹的東西,輕放進了腰間的佩囊里。
是歸林樓的鑰匙。
“別再弄丟了。”
抿不言,盯著他的眼眸,讓他回答的問題。
男人微頓,跟妻子緩緩笑了笑,他一字一句說得很慢。
“我所思,惟夫人爾。”
……
車窗外群山起起伏伏,遠觀仿若九天景,但對上山下山的碌碌凡人而言,跌宕難捱,不知盡頭。
杜泠靜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六個月前,只是因為收書路過京城,這短暫的路過,竟將自己陷進了這個最是不喜的,權勢漩渦、是非之地。
第2章
六個月前。
連三日的暴雨,將京畿最后的暑熱消解完畢,日子剛轉進八月,山間的秋意便順著渠,汩汩溢到了田間地頭里。
田莊門外的老榆樹下,金黃的榆錢子厚厚地蓋了一地,順著這陣疾風暴雨,老樹將枝條抖了個干凈,滿輕快地在秋風里搖曳沐浴,神清氣爽。
杜泠靜站在門前,的境況,可比不得這顆父親中狀元那年手植的老榆樹——
被這場大雨留在京畿五日,眼下雨雖然不下了,但算算日子,趕在中秋之前返回山東老家,卻來不及。
阮管事跟提議,“姑娘收書一路北上,既然風雨要留姑娘,何不就在此過中秋。恰二老爺一家都在京城老宅,姑娘過去倒是闔家團圓。”
杜泠靜認真思量了一下。
母親在五歲那年過世后,父親沒再續弦,一直跟著父親到做,后來到了京城,住進祖父留下的老宅里,父親途步步走高。先帝重父親,晚年重病時,時時招他至側,后來更是將他提為文淵閣大學士。
三十六歲的閣臣,即便是狀元也是首例。
只是先帝過世、今上繼位之后,祖父也過世了。隨著父親離京回鄉守孝,回了山東青州老家。
原本父親守孝三年便可回京復原職,誰料就在回京的路上,突遇山洪……
父親意外過世時,十七歲。
父親生前,給與蔣家三郎定了親。與三郎一起長大,當然無意嫁給旁人。可三郎子不好,終是與尚未婚便病逝了。
那年,才剛二十。
嬸娘顧氏從前便在意過無父無母,后連未婚夫婿都沒了,說實在算不上吉祥之人。
杜泠靜并不在意。不過此番若是平日里也就算了,偏偏是中秋佳節,突然上門叨擾,在旁人眼里,未必是團圓喜事。
杜泠靜說罷了,只讓阮管事去準備中秋節禮,屆時給叔父嬸娘送過去,自也給二妹和小弟都備一份。
“……只是多年沒見弟弟妹妹,不曉得他們喜好些什麼。還有嬸娘,近來不知如何了。”
杜泠靜的嬸娘顧夫人,去歲出門時出了意外。堪堪撿回一條命,卻了重傷,多半時候神志模糊,連人都識不清,只能臥床休養,再無昔日風姿。
管事阮恭這就遣人,先往顧夫人京郊的陪嫁小莊子上打聽。小廝一個時辰便跑了個來回,回來的時候臉有點古怪。
“是有什麼事?”杜泠靜讓阮恭把人進了廳里來。
小廝名喚菖,支吾了兩聲不知從什麼地方說。
阮恭上前踢了他一腳,“就把你聽的見的,從頭到尾說。”
菖捂了屁,這才道。
“小的過去,二夫人陪房見是小的來了,都嚇了一跳,我就把咱們被雨困在這兒的事說了,又照著姑娘吩咐問了話。”
“他們說京城澄清坊府邸那邊,二老爺居家候缺,一時沒有合宜的,多等了幾個月。二夫人還是舊樣子,只是月余前生了場小病,更虛弱了,每日貴重藥材養著。二姑娘接手了家中中饋,平日還要往顧家進學,甚是忙碌。小爺年初去了保定的書院讀書,等閑不還家。”
秋霖挑眉,“這不都好?你怎麼一副被棗核卡了嗓子的樣子?咽不下也吐不出的。”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yanqing/21_b/bjZ5Q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2088 章

廢柴王妃又在虐渣了
蕭涼兒,相府大小姐,命格克親,容貌被毀,從小被送到鄉下,是出了名的廢柴土包子。偏偏權傾朝野的那位夜王對她寵之入骨,愛之如命,人們都道王爺瞎了眼。直到人們發現,這位不受相府寵愛冇嫁妝的王妃富可敵國,名下商會遍天下,天天數錢數到手抽筋!這位不能修煉的廢材王妃天賦逆天,煉器煉丹秘紋馴獸樣樣精通,無數大佬哭著喊著要收她為徒!這位醜陋無鹽的王妃實際上容貌絕美,顛倒眾生!第一神醫是她,第一符師也是她,第一丹師還是她!眾人跪了:大佬你還有什麼不會的!天才們的臉都快被你打腫了!夜王嘴角噙著一抹妖孽的笑:“我家王妃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是個柔弱小女子,本王隻能寵著寵著再寵著!”
400.4萬字8.08 204045 -
完結18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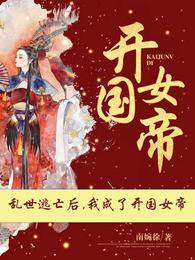
亂世逃亡后,我成了開國女帝
◣女強+權謀+亂世+爭霸◥有CP!開局即逃亡,亂世女諸侯。女主與眾梟雄們掰手腕,群雄逐鹿天下。女主不會嫁人,只會‘娶’!拒絕戀愛腦!看女主能否平定亂世,開創不世霸業!女企業家林知皇穿越大濟朝,發現此處正值亂世,禮樂崩壞,世家當道,天子政權不穩,就連文字也未統一,四處叛亂,諸王征戰,百姓民不聊生。女主剛穿越到此處,還未適應此處的落后,亂民便沖擊城池了!不想死的她被迫逃亡,開
238萬字8.18 16115 -
完結129 章

盛寵
【全文完結】又名《嫁給前童養夫的小叔叔》衛窈窈父親去世前給她買了個童養夫,童養夫宋鶴元讀書好,長得好,對衛窈窈好。衛窈窈滿心感動,送了大半個身家給他做上京趕考的盤纏,歡歡喜喜地等他金榜題名回鄉與自己成親。結果宋鶴元一去不歸,并傳來了他與貴女定親的消息,原來他是鎮國公府十六年前走丟了的小公子,他與貴女門當戶對,郎才女貌,十分相配。衛窈窈心中大恨,眼淚汪汪地收拾了包袱進京討債。誰知進京途中,落難遭災,失了憶,被人送給鎮國公世子做了外室。鎮國公世子孟紓丞十五歲中舉,十九歲狀元及第,官運亨通,政績卓然,是為本朝最年輕的閣臣。談起孟紓丞,都道他清貴自持,克己復禮,連他府上之人是如此認為。直到有人撞見,那位清正端方的孟大人散了發冠,亂了衣衫,失了儀態,抱著他那外室喊嬌嬌。后來世人只道他一生榮耀,唯一出格的事就是娶了他的外室為正妻。
31.9萬字7.92 62628 -
完結99 章

和死對頭成婚后
六公主容今瑤生得仙姿玉貌、甜美嬌憨,人人都說她性子乖順。可她卻自幼被母拋棄,亦不得父皇寵愛,甚至即將被送去和親。 得知自己成爲棄子,容今瑤不甘坐以待斃,於是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死對頭身上——少年將軍,楚懿。 他鮮衣怒馬,意氣風發,一雙深情眼俊美得不可思議,只可惜看向她時,銳利如鷹隼,恨不得將她扒乾淨纔好。 容今瑤心想,若不是父皇恰好要給楚懿賜婚,她纔不會謀劃這樁婚事! 以防楚懿退婚,容今瑤忍去他陰魂不散的試探,假裝傾慕於他,使盡渾身解數勾引。 撒嬌、親吻、摟抱……肆無忌憚地挑戰楚懿底線。 某日,在楚懿又一次試探時。容今瑤咬了咬牙,心一橫,“啵”地親上了他的脣角。 少女杏眼含春:“這回相信我對你的真心了嗎?” 楚懿一哂,將她毫不留情地推開,淡淡拋下三個字—— “很一般。” * 起初,在查到賜婚背後也有容今瑤的推波助瀾時,楚懿便想要一層一層撕開她的僞裝,深窺這隻小白兔的真面目。 只是不知爲何容今瑤對他的態度陡然逆轉,不僅主動親他,還故意喊他哥哥,婚後更是柔情軟意。 久而久之,楚懿覺得和死對頭成婚也沒有想象中差。 直到那日泛舟湖上,容今瑤醉眼朦朧地告知楚懿,這門親事實際是她躲避和親的蓄謀已久。 靜默之下,雙目相對。 一向心機腹黑、凡事穩操勝券的小將軍霎時冷了臉。 河邊的風吹皺了水面,船艙內浪暖桃香。 第二日醒來,容今瑤意外發現脖頸上……多了一道鮮紅的牙印。
25.2萬字8 140 -
完結123 章

不是聯姻嗎?裴大人怎麼這麼愛
姜時愿追逐沈律初十年,卻在十八歲生辰那日,得到四個字:‘令人作嘔’。于是,令沈律初作嘔的姜時愿轉頭答應了家里的聯姻安排,準備嫁入裴家。 …… 裴家是京中第一世家,權勢滔天,本不是姜時愿高攀得起的。 可誰叫她運氣好,裴家英才輩出,偏偏有個混不吝的孫子裴子野,天天走雞斗狗游手好閑,不管年歲,還是性格,跟她倒也相稱。 相看那日—— 姜時愿正幻想著婚后要如何與裴子野和諧相處,房門輕響,秋風瑟瑟,進來的卻是裴家那位位極人臣,矜貴冷肅的小叔——裴徹。 …… 裴太傅愛妻語錄: 【就像御花園里那枝芙蓉花,不用你踮腳,我自會下來,落在你手邊。】 【愛她,是托舉,是陪伴,是讓她做自己,發著光。】 【不像某人。】
23.8萬字8.09 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